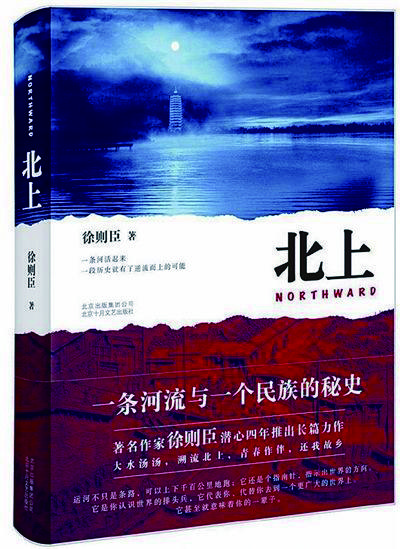记 者:在您看来,徐则臣的小说《北上》最突出的特征与意义是什么?
杨庆祥:《北上》以一条河流的变迁写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并投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同。
张 莉:去年在杂志上第一次读完《北上》,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我想,是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以回报,将之写在纸上,使无数人想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很显然,《北上》做到了。在我看来,《北上》中,运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神采,它使我们尘封于历史中的运河“活”起来。读《北上》使我们认识到,运河是源远流长的时间之河、生命之河,它既是抵御外族入侵的、同时也是开放、包容的文明之河。它是实在的,也是象征的,它实在地穿越我们的土地,滋养我们的成长,同时也象征了我们的民族文脉。《北上》引领我们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运河内部的文化能量,让我们重新理解运河以及运河文明,认识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记 者:《北上》以一条河流的变迁串联起跨越百年的中外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徐则臣是如何将宏大的历史投射到一部具体的小说中的?
杨庆祥:宏大历史叙述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对徐则臣这一代作家来说,很显然不会使用那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北上》实际上是用“私人史”的方式,从内部来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想象和建构,所以主体意识很强。
张 莉:《北上》纵横交错,广阔辽远,一扫我们对以前运河文明的肤浅理解,我想,这与小说的叙述方式有重要关系:一是叙述时间的使用,二是世界视野的引入。在叙述时间上,小说家选择了双线并行,上下交汇。一条线是1901年,从时间的上游顺流而下;而另一时间线则是2014年,由2014年溯游而上。时间是这部作品的枢纽,历史与当下交汇在运河之上。小说选择中国人与西方人两种视角交织的方式。意大利青年小波罗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兄弟马福德,由此,读者跟随西方人来看1901年的中国,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恨情仇。这是非常新鲜的视角。当然,另一个视角则是中国的本土视角,两种视角交织碰撞,最终都凝聚在运河之上,这是有意味的选择,也是极为陌生化的文学处理,由此,小说家将一段宏大历史具象在浩荡大河之上。
记 者:有批评家提出,“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北上》的写作”,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与东西方文化视野?
杨庆祥:比较视角是《北上》的一个基本设置,也是基本的结构。正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才避免了某种单边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东方中心都是一种单边主义。事实是,只有在“世界”之中,中国和中国人可能完成其现代性蜕变。
张 莉:我想用“世界视野”来形容这部小说。《北上》中,小说家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单边的、不是狭隘的。小说中,通晓外语的知识分子谢平遥渴望效法先进,去“世界”寻找改变中国的药方,而意大利的小波罗则渴望来到中国。欧美对于谢平遥来说意味着“世界”,中国对于小波罗而言也意味着“世界”。这就是小说家的卓越理解力,小说不仅要写我们如何理解运河,也写“他们”,即西方人如何理解我们的运河。相信诸多读者对小波罗离世的场景记忆深刻。他的遗言是,“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细节,但它具有隐喻色彩。《北上》里,固然有作为中国人的强大主体性,同时也有一种并不封闭的世界视野,换言之,世界视野使徐则臣写出了运河的中国气象,也写出了运河文明的世界意义。
记 者:小说中涉及关于历史、地理、考古、绘画、摄影等许多细节和知识,徐则臣在写作中体现出一种学术研究般的热情与严谨,这样的写作方式在当下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您怎么看这种写作及其意义?
杨庆祥:我觉得徐则臣作品中的这种知识性东西不是太多了,而可能恰恰相反。现代小说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综合性”。仅仅有故事和人物是不够的,而要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场域。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机体”。
张 莉:细节是小说的生命,是作家的基本功。我认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毕生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准确。当然,细节的生动与否也是我自己考察一位小说家是否有才华的重要标志。对过去的生活不了解、对过去的知识不了解,怎么办?写作者只能老老实实去查资料,做案头工作,别无他途。当然,我并不认同那种知识的铺陈、细节的堆砌,那样的细节是没有神采和生命力的,也看不到创作者的能动性。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常识性细节不能出问题,否则会导致整个文本的不成立。我非常欣赏徐则臣写作《北上》时的态度。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做案头准备工作是深有意义的,我认为应该受到鼓励。
记 者:作为一位“70后”作家,小说《北上》以及徐则臣之前的写作,是否代表了青年一代写作的某种特征与新变?
杨庆祥:最近这些年,青年作家的写作整体上都呈现一种求新求变的趋势。这里其实有一大堆名字和作品为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概而言之,文学的代际更迭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当然这也是未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所在。
张 莉:作为生活背景的运河在徐则臣作品里已经有近20年历史了。那么,将生命之河融入自己的笔端、在纸上为大运河立传也就成为徐则臣的命中之作。其实,写眼前的运河,以个人成长记忆为蓝本是条捷径,也可以写得好看,但是,作家没有这样做,他知难而上。《北上》超越了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而进入更为广大和广泛的视域。小说家写的不是个人记忆之河而是民族之河,他以艺术手段使它活起来,使它栩栩如生地长在我们民族文学的记忆链条里。
这样的特征和变化,除了《北上》,《北鸢》中也有体现,葛亮跳出个人记忆而进入家国书写,这部写作了7年的作品写得笃定扎实,有静水深流之美。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能说这两部作品是青春写作了。作为长篇小说,《北上》和《北鸢》的完成度和成熟度都很好,并不逊于年长作家。《陌上》也是如此,付秀莹的写作之所以受到诸多评委的肯定,在于她真切书写了变革中的新的农村图景,因此,《陌上》被视作当代乡村书写的代表作品。当然,新一代作家的新变不仅仅体现在从青春、个人史写作的跳出,还在于丰沛的创作能量和探索精神。李宏伟《国王和抒情诗》的魅力在于表现形式的先锋性,其中包含了属于新一代作家的探索和无畏,非常令人赞赏。无论是《借命而生》还是《心灵外史》,石一枫对人的精神疑难的深度书写也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