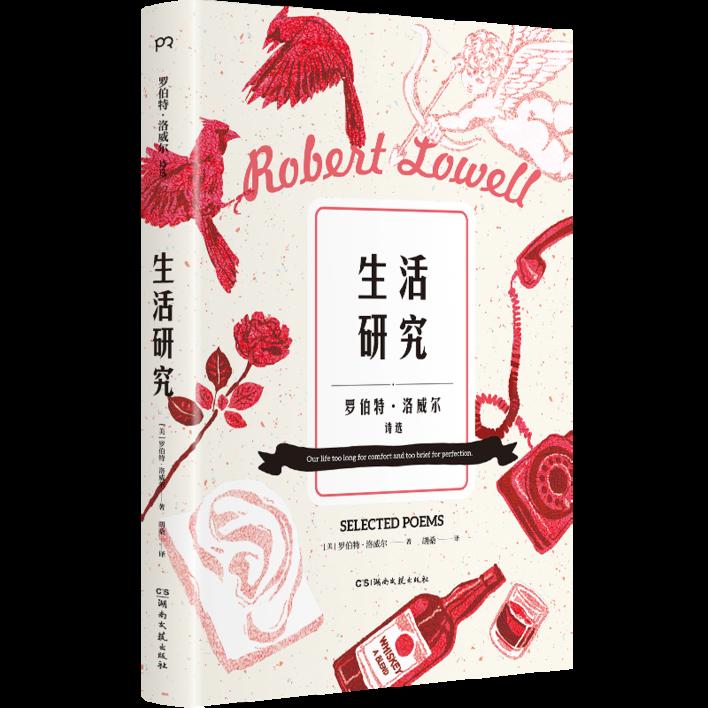美国诗人、著名译者丹尼尔·韦斯博特(Daniel Weissbort)在与罗伯特·洛威尔的对话中曾提到,直到1969年后者的《生活研究》出版之后,美国诗歌才真正醒过来。这样的论断乍听之下不免让人怀疑。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诗歌在洛威尔的《生活研究》面世之前,垮掉一代的金斯堡已经在诗坛“嚎叫”了3年,洛威尔在此之前也出版过两部诗集,其中《威利老爷的城堡》还在1947年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由此来看,丹尼尔·韦斯博特的话更像是一种隐喻,苏醒意味着着陆,意味着回归,也意味着洛威尔本人和美国人阅读、接受诗歌态度的转变。
在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眼中,罗伯特·洛威尔本可以凭借家族影响力成为外交官等政府要员,但洛威尔却选择了成就自己。洛威尔的父亲从海军退役后,结束了其一生惟一带有色彩的生活。在罗伯特·洛威尔眼中,父亲的余生过得毫无特色,比如,这位退役军人从不在周日去教堂,而喜欢在家中的垃圾桶上描摹自己的名字,并一次次给名字后面“美国海军”这几个字补漆,以至于他在诗歌中宁愿认祖父为生父。相比之下,母亲在日常生活中要积极很多,她崇拜英雄式的人物,性情高扬。在洛威尔的家庭中,经常会发生一幕幕家庭情景喜剧式的场景:母亲高声放话,父亲结结巴巴。即便如此,洛威尔还是在两股相反的力量之中汲取了力量。在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中,类似父亲在凡俗之物上刻写名字的举动一次次被赋予了全新的诗意。母亲的热情激发了洛威尔对英雄气概的向往。他在童年时期酷爱玩“玩具兵”,也为这些玩具编撰过富有传奇色彩的罗曼司故事。这一股男子气的激情与创造,在他13岁加入寄宿制学校之后,直接转换为想要加入美式足球队的冲动,但校方只是将他列入队里,从未让他获得过出场的机会。于是,洛威尔从运动转向诗歌创作,或许在年轻的洛威尔心中,诗歌是另一片需要绞杀的场地。他野心勃勃,精力旺盛,所要面对的对手至此变成了词语。
在进入哈佛读书后的第二年,洛威尔拜访了诗人弗罗斯特,他给洛威尔指出了进入诗歌的“终南捷径”(the easiest sort of path)。这条捷径上站着济慈、柯林斯等前辈诗人。其入门之道,归根结蒂来说,是要让初学诗歌的人找到进入诗歌的声音——怎样压缩词语。于是,洛威尔开始了自己的试炼期,他仿照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意象派诗歌,创作了一系列最初的习作。在与父亲因为一名女子而争吵之后,洛威尔来到了波士顿,经人指引认识了诗人约翰·克罗·兰瑟姆,随后又与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起,去南方拜见了阿伦·泰特。由于泰特家已经住满了人,洛威尔只能在泰特家的草坪上搭起帐篷,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屋外帐篷岁月,满足了洛威尔作为逃离家庭者的内在需求。同样,这一顶帐篷也是兰瑟姆和泰特等人“新批评”主张的象征,它隔绝了传统意义上诗歌与生活的脐带,也隔绝了意图与诗歌之间的桥接,对洛威尔的诗歌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影响。如果说弗罗斯特只是指南者,那么泰特等人则是洛威尔真正的试炼师,他们让年轻的洛威尔接触到了诗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序列中,洛威尔作为后来者,学到了诗歌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感和系统性。这一场试炼一直持续到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教书时期,他在那里遇到了柯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新批评对他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按照这一系列“试炼”的步骤,罗伯特·洛威尔本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带有新批评色彩或南方派风格的诗人。但是,随后爆发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他的轨迹。与许多当时有志于报效祖国、加入复仇的太平洋战场的美国青年不同,洛威尔决定拒绝加入海军。此举固然有以母亲遗传的勇气对抗父亲的影响的因素,但洛威尔在随后的岁月里将这段日子称为“种子时刻”(seed time),亦即,他更倾向于认为在这一段孕育的时刻里,他因为拒绝,而赋予了自身作为诗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与世间重大时刻的隔绝,成了洛威尔加冕自身的诗歌勋章。
在1944年仅发行250册的处女作诗集《无相似性的地方》(Land of Unlikeness)中,洛威尔展现的是早期试炼的成果,其中,诗歌的形式感和内容中所探讨的宗教性是这部诗集最大的特点,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T.S.艾略特。尽管与当下生活隔了一层晦涩的薄膜,但是泰特却认为这部诗集展现的是一个“造雨人”的品质,他将召唤一场暴雨,席卷并淹没整个美国诗歌界的读者。
在摒弃了第一部诗集的形式感和对宗教题材的探讨之后,罗伯特·洛威尔的第二部诗集《威利老爷的城堡》面世了。在这部诗集中,洛威尔早期诗歌中晦涩的象征体系,以及较为注重形式的系统性不见了,他找到了联接宗教性和实在物的新方式——赋予实在物以活力。凭借着这种活力,凡俗的物体获得了跳出自身并点触宗教题材的活动空间。比如,在《醉酒的渔夫》中,《圣经》的典故融合在日常生活的可见事物之中,洛威尔在细微之物中,勾连起庞然大物:“我鞋子里的一粒沙/也模仿着可能毁灭/人类与造物的岁月。”
虽然这部诗集获得了普列策奖,但若非对《圣经》传统和母题有充分的认识,读者恐怕难以捕捉到诗句的精妙之处。这一点在1951年出版的《卡瓦诺的磨坊》(The Mills of the Kavanaughs)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部诗集中,洛威尔企图用神话叙事的方式来结构他的诗歌,他所效仿的典范是弗罗斯特,想要用极为小心的方式来言说现实的经验。但此举被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过于小心的洛威尔将诗歌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加上了韵脚和节奏,以至于没人相信在现代生活中,普通人的心思是带韵脚的。在这部当时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中,洛威尔迎来了真正蜕变的时机。神话、格律、诗歌本体论,这些因素被证明除了晦涩之外,未能帮助他书写出心中真正有关“经验”和“生活”的内容。
直到《生活研究》的面世,罗伯特·洛威尔才“醒来”。这不是“苏醒”,更多地是激活和“清醒”过来。他曾在采访中说起,他对两种方式的写作有着持久的兴趣:其一,直接处理经验本身,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没有争执,托尔斯泰是这方面的典型;其二,高度压缩的语言,其诗歌的韵律与韵脚彰显在方寸之地。这两种类型对读者阅读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有着直接的帮助。而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美国诗歌的发展,在洛威尔眼中则是一段“亚历山大时代”:大多数诗人在诗歌中呈现的是形式和技巧,其内容多少与当时的文化相脱节。即便是金斯堡这样的“嚎叫派”诗人,其诗歌也或多或少呈现出一种古怪的结合方式:取材和改编自威廉·布莱克的神话体系的框架,外加恣意放纵的惠特曼式的混响。这一类诗歌所激起的情绪和神秘体验,包裹在爵士乐的氛围中,让人有极强的飞翔感,却往往忘了起飞点和起飞的过程。换言之,即便这其中有对现实的触及,但未能真正变现实为诗歌经验。
变现实为诗歌经验,恰恰是《生活研究》提供给美国诗坛的苏醒剂。洛威尔在这部诗集中有意识地放弃了前三部诗集中的神话形式和晦涩表达,转而直接用描述性的语言,企图集中展现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对比《威利老爷的城堡》,读者可以较为直观地发现,那些《圣经》典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世俗的细致描写。《生活研究》写家庭生活,写世俗生活,写经验本身。其中,母亲和父亲的骨头,不再是典故中亚当和夏娃的骨中骨,而成了石头。先前诗歌中诗人投射在韵脚、韵律上的精力被收回,并以取自神话的关怀现实的耐心,专注于人物经验的瞬间。在这种笔调之下,母亲清理完过世的父亲的遗物,留下的是一个出神的瞬间,这种瞬间不再具有复杂的结构,而仅仅是生活中另一种经验的类比:
准备完了,担心
会独居到八十岁,
母亲倚在窗口出神,
就好像在火车上
坐过了一站。
更为重要的是,洛威尔“研究生活”的方法,在这部诗集背后慢慢成形,并在随后的诗歌中以“针”的意象被反复提及。比如,在《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中,纪念碑如鱼刺,上校如一枚指南针;又比如,在《中央公园》中,飘荡的纸风筝悬挂在方尖碑的尖端,另外还包括蜜蜂的蜂针等,这些尖锐的意象或许可以看做是洛威尔转变诗歌风格、嵌入生活的方式。如果说金斯堡等人的诗歌是大声疾呼的棒喝,那么洛威尔的诗歌更像是崩断的琴弦,扎入人们最为纤细的皮肤之内。这种声弦过后的寂静,改变了美国诗坛的诗风,它被后人称为“自白派”。值得指出的是,自白不是喃喃自语,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一场从生活到经验、再从经验到语言的双重压缩。在这双重压缩和转换中,新批评的技巧,弗罗斯特和毕肖普等人对平常事物的关注,给予了洛威尔巨大的能量。
针、尖锐、浓缩,其背后是狭长而密闭的黑暗。洛威尔企图用这种内心晦暗的尖端刺破生活的薄膜,呈现出诗歌秩序下密封的思想。他在《近视:一个夜晚》这首诗歌中写道,在糊在一起的五种感官背后,激起的是“思想缝合了思想/在通过针眼之时……”关键在于,这枚穿过揉捻成股的思想的针,缝合了时代,也缝合了自我的经历。在《生活研究》这部诗集中,洛威尔最终呈现的是一位具有卓绝勇气和强烈野心的形象,它召唤每一个企图研究生活的读者。而只有将生活当作个人历史进行研究,不放过任何崩溃、悬停、绝望的瞬间,并将它放在与词语搏斗的搏斗场上进行展示的个体,才具备成为生活中的英雄的品质。
长 夏
黎明时,朋友们简短干脆的告别;夜晚,
敌人重新集结,脚步杂沓,殊难移动,
像马戏团贵宾犬在圆球上跳舞——
某种非人之物总在我们身上升起,
以拥抱击打你,伸出
一只犹豫不决的手,挺直如扫帚;
把明亮的原木堆得更亮,直到我们大汗淋漓
闪闪发光,像涂了热油:
纯酒精、明亮的液滴、十分钱硬币大小、银色……
每天,更沉痛地决定留下,
每天,更残酷,神秘莫测且根深蒂固,
脱水,在火中微笑,
解去他那柔嫩的、结着血痂的脚上的绷带,
踢开最后一只废弃的瓶子时受的伤。
渔 网
任一惊奇得令我们目眩的清晰事物,
你漫游的寂静和明亮的意外收获,
海豚被释放,去捕捉闪光的鱼……
说得太少,随后又太多。
诗人们年纪轻轻就死去,其节拍令他们不朽,
原本的声音唱着,走了调;
那老演员不能读懂他的朋友们,
然而,他大声读着自己,
天才嗡嗡聒噪让观众席沉寂。
那诗行必有终止。
而我的心升起,我知晓我已一生欣喜
于打结、解开一面沥青绳的渔网;
鱼被吃掉,网就会挂在墙上,
就像难以辨认的青铜被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之上。
——摘自罗伯特·洛威尔《生活研究》,胡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