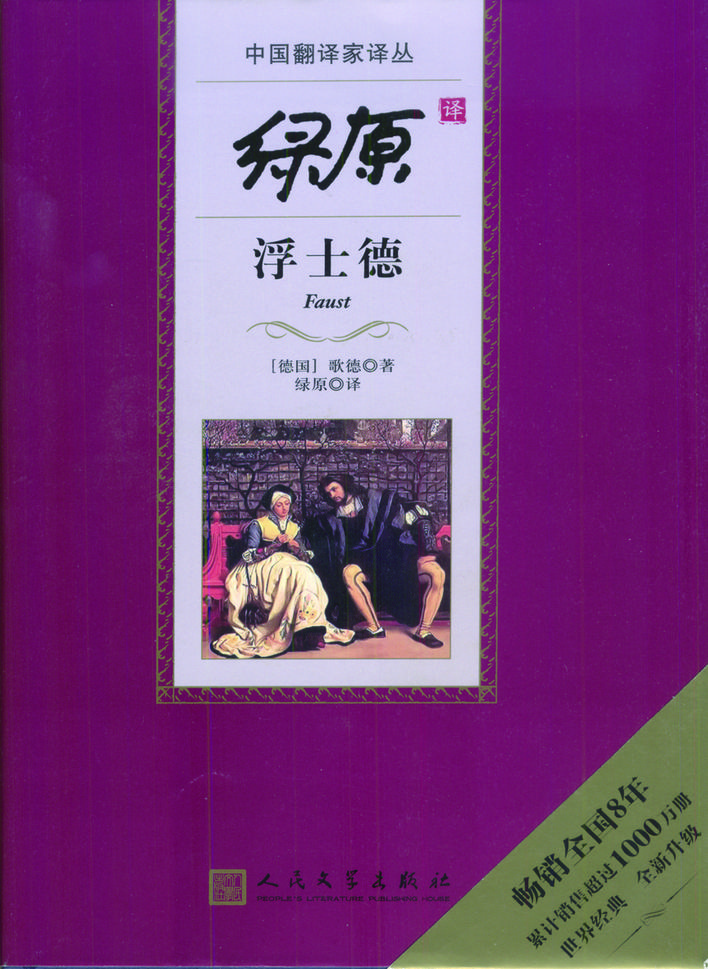对于绿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很多人以生命诗学、生命哲学的视角进行解读,如此说法显得空泛,尤其是读者对他一些长诗的忽略,这些长诗驳杂交错的主题和反复向生命本身挺进的“炼狱”式进程是丰富而深刻的。比如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即景三幅》《现代中国,仲夏夜之梦》中的现代性反思,同期的《我们走向海》《高速夜行车》中对于生命的诘问、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生命与死亡的辩证等等,由此肇始的零碎而分散的诗学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长诗《人淡如菊》(1996)等作品中的生命沉潜和哲学追问,终于在新世纪的长诗《……他走着》(2001)、《在旷野的那边》(2003)等作品中得以集中、系统地呈现。生命诗学、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与死亡的互证,一直是古老但却历久弥新的话题,绿原在现代语境中对这些主题的关注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注意到中国文学在新时期的特殊性(甚至可以置于整个20世纪的特殊性中去观照),以及绿原对歌德、里尔克等德语诗人的翻译,就会发现以“生命诗学”“人与自然”这样的总结去定位绿原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只能是游走于词语的表面,甚至以热爱动物、环保这样概括前文提到的那些长诗,就更显得挂一漏万了。
一
值得注意的是,绿原的诗学思想在新时期以来有一次大的蜕变,与同期其他诗人尤其是经历相近的诗人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甚至在诗学意义上来说,他成为时代风气中卓尔不群的独行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夜行车》中,“高速”一词表面看来与时代精神密切对应,“你和你的车在空荡荡的全天候公路上飞速前进/公路像传送带在你的车轮下而飞速抽动/把你和你的车当作仿佛待加工的制品/投入了无尽长的空间流水线”。虽然诗中夹杂着对于现代性的陌生与质疑,但诗的基调是高昂明快的,根据作者后记中所说,“人决不甘心做尼采所谓的‘末人’虽然他又毕竟不是超人;他总以为看见了自己的前途虽然有时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直在迈步向前虽然有时不得不踌躇停顿;他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幸运虽然有时难免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他永远希望着虽然又几乎同时陷入绝望之中。”这些观念显然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高速夜行车也成为“超人”生命没有终点只有永恒进程的象征。
从1986年写作又经1988年修改的《高速夜行车》开始,诗人对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逐步深入,进入了学界所说的生命诗学时期。在表面高亢实则迷茫的高速夜行中,诗人渐渐冷静了下来,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终于走向了“人淡如菊”的境界。“我如一个盲人/凝视空洞而坚实的黑暗/达二十年……”“于是我们饥饿/我们恐怖/并在饥饿与恐怖的/交迫中玩着/诗人的游戏:/要从/火坑里栽出/一盆水仙来!”这样的诗句让人很自然就想到里尔克那句著名的诗,“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80年代开始绿原大量翻译了里尔克的诗歌,包括最经典的《杜伊诺哀歌》。对比他的翻译和创作,可以说,经由里尔克,诗人发现了诗歌新的领域,也重新发现了自己。在《人淡如菊》中,有几句很突兀的诗句,“抛弃!/抛弃就是遗忘:/只有遗忘才回得了/故乡”,联系绿原诗学中的生命意识,以及90年代的整体创作,这里的“故乡”很自然就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还乡”,或者诗人在岁月沉淀中对生命归宿的思考和追寻。
其实,生命本体之思、哲学意义上的故乡之思,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隐性甚至是比较缺乏的,绿原的诗学思想的来源及转变往往是被读者忽视的。绿原在1984年写下名为《秋水篇》的组诗,以读后感的方式介绍了五位诗人,桑戈尔、聂鲁达、里尔克、惠特曼、波特莱尔,其中里尔克对绿原影响巨大。组诗中的《读里尔克》是这样表达的:“他写不出诗来/便向大师诉苦/大师罗丹指点他/放下笔吧,到/植物园去,去/独自凝视/笼子里的动物/凝视下去,凝视下去,直到/它显出了/它的粗暴和窈窕,直到/狭小的囚笼又变成了/险峻的山坳,直到/你自己通过/它的喉咙/发出了自己/绝望的吼叫。/他照办了,于是/写出了/名篇《豹》/并且以为懂得了/诗的诀窍。/从此便到处寻找/心的空间,倾听/雕像的呼吸,涂抹/听得见的风景,并为/迷失在死胡同里的语言/找出路——/可惜再也/写不出一首/活的或者曾经活过的/野兽。于是他又成为/一名初学者……”恰如罗丹对里尔克的启示,绿原在里尔克的启示下也成为了一名初学者,从《高速夜行车》中出现的“无人地带”,到后来以动物为主体的诗歌,绿原似乎在逐渐突破“人的视角”而开始倾听“无人地带”的鼓声。
二
这种转型在写于2001年的长诗《……他走着》中得到彻底的完成,“……他走着/……早自/一天的黎明,从黑暗里迎着朝霞,/走在自己浓影的前面;走着走进了/一天的黄昏,沐着夕晖,走在/自己淡影的后面,跟着没入了/黑暗;不知怎么在哪里过了一夜又/重新走着,走过眼前身旁一切,决然/向不可知的地平线走去——”这首《……他走着》有着《豹》中所呈现的雕塑感。同时,“初学者”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由《高速夜行车》中的“我”向无人地带走去,到《……他走着》中的“他”向不可知的地平线走去,主体变成了“无人”或者说非人——动物。诗中的“他”指的是大象,他一生都在“走着”,成为生命过程的象征,他走过一切艰险和未知,“……走过/不知从哪儿伸进来让/居民们见着相顾失色的/一片陌生的白巾,或者/不知从哪儿传过来让/居民们听着无不打寒噤的/阵阵咒语似的鼓声……”他穿过这些白巾和鼓声走向尊严的死亡。根据绿原在原文中所注:“原始森林里什么颜色都有,唯独没有白色。猎人遇危险,常挥动白巾以自卫。击鼓是当地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居民们’指林中动物,它们见到白巾或听到鼓声,无不惊避。”人类向无人地带的不断挺进,以及用类似鼓声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可控范围”,表面看来,确实指向了人与动物的关系,指向了生态,但绿原所要表现的,显然远非如此。
当以生命的视角来看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包含的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绿原在《……他走着》一诗中反复阐明的诗学思想。“是的,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光,熄了就/熄了,决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于是,他终于/交出了、交出了/他如光的生命;他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没有任何痕迹的永恒。/(永恒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痕迹才是永恒。)/他在永恒中仍然/等待着,等待奇迹;等待/复活:等待死与生的交替:等待/另一个生命,另一个世界/降临在自己已经化解了的/尸体之上,彻底解构/永恒长夜的黑暗与/虚无!”这种表达与里尔克死亡是另一种存在的想法异曲同工。当然,绿原是深受德语文学滋养的诗人,不仅仅是里尔克,他也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歌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浮士德》那种“永不停歇”的精神所驱动的文本结构,在《高速夜行车》《……他走着》这些长诗文本中也是隐性存在的。至于《……他走着》中大象“如光的生命”,更是让人想起里尔克笔下的天使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由此来看的话,绿原笔下的大象,“……恰如/古代一位落难/人间的诗神把自己/最后一部心血结晶/吐了出来,埋在地下,坚信/将在遥远的后代身上/复活一样。尽管/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光,熄了就/熄了,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除了远远/枉然对他追踪的/那一阵近乎/临终关怀的/神秘的鼓声。”这里又出现了“神秘的鼓声”,如果说一开始出现的“鼓声”类似于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那不断响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咚咚声的话,那么这里的“神秘的鼓声”就类似奥尔弗斯令万物动容的琴声了。
在绿原翻译的里尔克的作品中,有一首诗歌中提到了死亡的“伟大”及其对人的意义,“每人身上所含有的伟大的死,/这才是人人围着转的果实”。(《关于贫穷与死亡》)其实这种死亡观贯穿了里尔克后期的全部作品,也是其重要的诗学思想,在其公认的代表作品《杜伊诺哀歌》的第四首中也得到集中的体现,“但是这一点:死亡,/整个死亡,即使在生命开始之前/就那么温柔地被包含着,而且并非不吉,/却是无可描述的啊。”由里尔克对死亡的思考与表达,去审视绿原的《……他走着》《在旷野的那边》等长诗,就会发现里尔克对绿原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生命与死亡的哲学思考,使绿原从人类出发而开始关注“无人地带”,或者说由人转向动物再延伸到万物最后又回归到人自身。如果再从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作品出发(绿原的选译无疑有自己的喜好和认同),就会发现绿原笔下“无人地带”的深刻含义,以及动物的隐喻,而不仅仅是多数读者认为的生态意识。比如他翻译的里尔克的《是时候了……》,这种万物包含神性的源头,很明显是奥尔弗斯神话,而且,这种通过诗歌与万物感应的思想,与绿原笔下的歌德形成了诗学上的呼应,诗人“宛然悲悯下界一切的/欲望、苦难、追求和斗争/膝前是一座黄金的竖琴/让微风拨动它的和弦/飘向了遥远的古希腊/飘向了沉寂的东方/连同他倦怠的灵魂”(《歌德二三事》)。
三
从生命视角审视人与动物,或者人与万物的关系,是很多诗人所触及的主题,尤其经由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赋予诗人神圣天职以后。绿原从《高速夜行车》的“迷茫”到《人淡如菊》的“沉静”,再到《……他走着》的反思终于抵达了《在旷野的那边》的诘问。在这首写于2003年的长诗中,绿原通过“动物园”“马戏团”“博物馆”三个视角审视了人类对于其他生物的奴役,实际上是人扮演上帝角色之后的疯狂与不可扼制的自大:“这就是动物园,人类为了/帮助可怜的动物界脱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经由/捕捉、安置、隔离等必要措施,为/猛兽们和弱小族类分别建立了/另一个陌生的家园”,绿原对动物园的表述,让人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类荒谬的历史事件,甚至更为深刻地讲,让人想到一个个类似现代化工厂的人类生活场域;“这就是马戏团……/所有节目圆满到、醇化到理想/境界,不论观赏还是参演,均无异亲历/一场神宴……/分不清自己是看客还是演员”,其对马戏团的描述中已见深刻的哲学思考,这马戏团写尽了人类的一幕幕可悲的生活场景;“这就是博物馆,原来人类在/马戏团的意外成功之后而/动物园的梦想远未成功之际又/以魔幻的科技之手为/新人类和新新人类制造了/一道时间的长桥,让他们/从旷野的那边通向/旷野的这边”,在博物馆的描述中,又回到了现代性反思中去,“时间长桥”与之前他笔下的“时间流水线”形成了内在联系,在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维一体的诗学语境中,以时间为圭臬的“现代人”无异遭受了降维打击,而博物馆又指向了已死和将死。
在长诗《在旷野的那边》后记中,绿原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人与动物之关系、动物作为生命主体的思考,“一切动物都离不开旷野,家畜在被驯化之前也不例外。旷野这边才是动物的天堂,天堂的子民都是自由的……在旷野的那边,即人间,动物们虽无匮乏之忧,处处感到‘温馨’‘仁慈’和‘安全’,却不得不被迫丧失了自由,即动物之为动物的这个先决条件。对于这个缺陷的可能性,任何动物不论如何被驯化,都是十分警觉的,随时提防着的;可叹人类对它始终丝毫不以为意,即使设身处于动物的境地,也根本未必理解它。”如果不对绿原稍早一些的《……他走着》等长诗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在旷野的那边》确实很容易让读者简单地理解为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或者说保护动物的主题。但从生命本身的视角来看,所谓的“保护”本身就是“被保护者”自由的丧失。从人为动物立言到人为上帝立言,诸多论者停留于这一过程,但是,更深入来看,则是极少数人为整个人类立言,这种立言并不是先知般的思想者,而往往是权力主导下的“专制”,并通常打着“自由”的旗号。在这首长诗中,绿原提醒读者,“看哪,在‘万物之灵’的主宰下/旷野的那边在扩大,这边在缩小/那边向这边伸延而成零距离/正如诗人所谓‘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狱的天花板’。”甚至在动物园中,在马戏团中,人的天堂就是动物的地狱,这是绿原诗学思想中更深刻的地方,更多的人应该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法则中看到自己的人生处境。
绿原接续着20世纪现代性反思的传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撞“上帝之死”的世界语境,并在《在旷野的那边》一诗中做出了回应,“原来‘上帝’就是人——/正是人,即‘上帝’”。这种从生命意识出发,由人而思考到动物(生命主体的尊严),再由动物回到人的生命状态的过程,在绿原后期的创作中形成了类似歌德《浮士德》中的螺旋式探索,其实如前文所说,他于80年代开始直到新世纪的长诗创作,在结构上大多有浮士德的影子,但在思想上,却深受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影响,即生命与死亡、人与万物、人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在旷野的那边》的后记中,绿原认为:“归根到底,如果按照任何宗教观点,还有一个更高级的‘万物之灵’的话,人类岂不是同样属于动物范畴,而应怜悯自己吗?人类赖以生存的狭小的生活圈子,不就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园’吗?人类赖以显示才干的各种职业,不就类似‘马戏团’么?人类借重于文化、历史而孜孜以求的身后名,不就类似‘博物馆’吗?在旷野的这边,可以从动物想到人;在旷野的那边,可以从人想到动物。”由此可以看出,绿原对动物的关注,实际上借由生命这一通道仍然回到了人本身,“动物园”“马戏团”“博物馆”在他笔下成为人类生存的隐喻或者说缩影,这首绿原生前的最后一首长诗,也成为他诗学思想的归结点——“在人身上看得见动物性被装饰,在动物身上看得见人生被摧残”。
综上,再去看绿原翻译的里尔克,尤其是里尔克笔下的动物或生物、万物,就会发现绿原笔下的动物远非许多读者认为的生态属性的动物,而是具有永恒与诗性特质的,人类所不具备(也可能是丢失)的灵性存在。在《杜伊诺哀歌》第8首中,里尔克这样描述动物:“生物睁大眼睛注视着/空旷。只有我们的眼睛/仿佛倒过来,将它团团围困住/有如陷阱,围住它自由的出口。/外面所有的一切,我们只有从动物的/脸上才知道……自由的动物/身后总是死亡而/身前则是上帝,当它行走时它走/进了永恒,有如奔流的泉水。”里尔克对于生命与死亡、瞬间与永恒的探索所达到的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许恰恰是我们辨认绿原的一把钥匙,尤其是绿原后期的创作,不难发现他翻译与创作之间互相的滋养。无论是他笔下的动物还是旷野,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系列“无人地带”的丰富性,以及那不断传来的一阵阵“神秘的鼓声”。回想起艾略特那绝望的“判词”——“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啜泣”,我们可以在绿原的诗歌中欣慰地听到成串的“砰砰声”,借以审视一个个被摧残的人生,一个个追求尊严的生命,以及死亡的必然价值和尊严。那穿过“无人地带”的神秘的“鼓声”,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