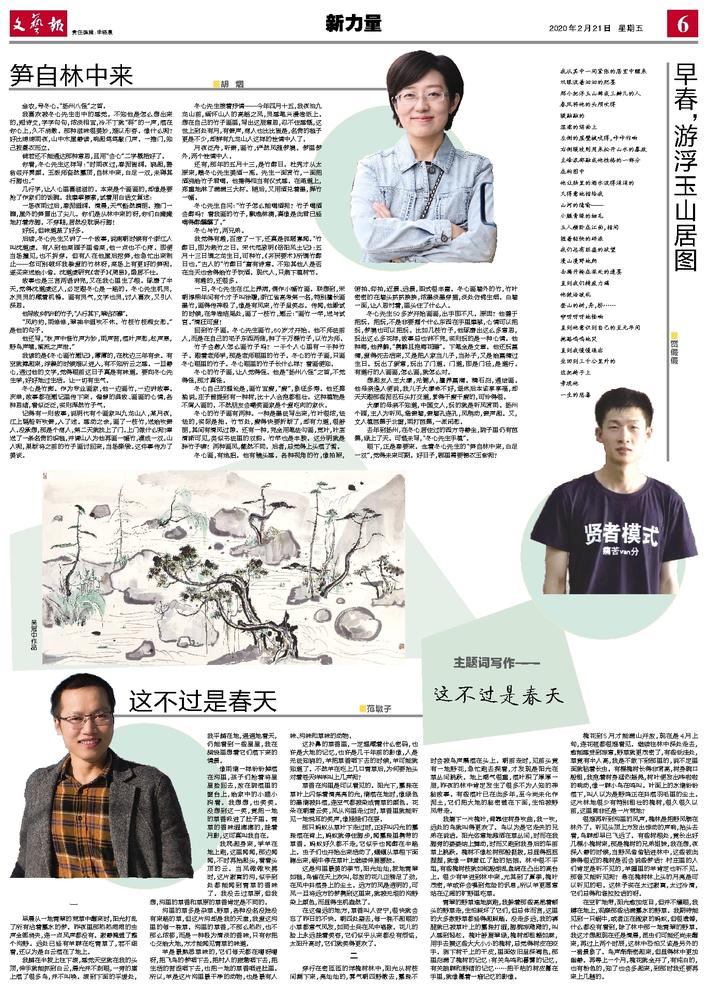金农,号冬心。“扬州八怪”之首。
我喜欢被冬心先生击中的感觉。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短诗文,字字句句,浓淡相宜,冷不丁就“砰”的一声,落在你心上,久不消散。那种滋味很美妙,难以形容。像什么呢?好比绵绵雨夜,山中木屋静读,响起笃笃敲门声。一推门,知己披蓑衣而立。
倘若还不能通达那种意思,且用“会心”二字概括好了。
你看,冬心先生这样写:“时雨夜过,春泥皆润。晓起,碧翁忽开霁颜。玉版师奋然露顶,自林中来,白足一双,未碍其行脚也。”
几行字,让人心里喜滋滋的。本来是个画画的,却像是要抢了作家们的饭碗。我摩拳擦掌,试着用白话文复述:
一场夜雨过后,春泥湿润。清晨,天气豁然晴朗。推门一瞧,屋外的笋冒出了尖儿。你们是从林中来的呀,你们白嫩嫩地打着赤脚。不穿鞋,居然没耽误行脚!
好玩,但味道差了好多。
后续,冬心先生又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朝时候有个浙江人叫沈道虔。有人到他菜园子里偷菜,他一点也不心疼。即便当场撞见,也不拆穿。但有人在他屋后挖笋,他急忙出来制止——您可别破坏我挚爱的竹林呀,菜场上有更好的笋呢。遂买来送给小偷。沈道虔研究《老子》《周易》,隐居不仕。
故事也是三言两语讲完,又在我心里生了根。琢磨了半天,觉得沈道虔这人,必定跟冬心是一路的。冬心先生机灵,水灵灵的藏着机锋。画有灵气,文字也灵,讨人喜欢,又引人深思。
他写故乡杭州的竹子,“人行其下,翠沾衣襟”。
“风约约,雨修修,翠袖半湿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是他的句子。
他还写,“秋声中惟竹声为妙,雨声苦,落叶声愁,松声寒,野鸟声喧,溪流之声泄。”
我读的是《冬心画竹题记》,薄薄的,在枕边三年有余。有空就捧起来,浮躁的时候难以进入,有不知所云之感。一旦静心,透过他的文字,觉得眼前这日子真是有味道。要向冬心先生学,好好地过生活。让一切有生气。
冬心是竹痴。作为专业画家,他一边画竹,一边讲故事。庆幸,故事都在题记里传下来。偏僻的典故、画画的心情,各种思绪,看似泛泛,实则浑然竹子气。
记得有一则故事,说明代有个画家叫九龙山人,某月夜,江上隔船听吹箫,入了迷。感动之余,画了一枝竹,送给吹箫人。没承想,那是个商人,第二天就找上了门。上门做什么呢?奉送了一条名贵的织毯,并请山人为他再画一幅竹,凑成一双。山人呢,果断将之前的竹子画讨回来,当场撕毁。这件事传为了美谈。
冬心先生接着抒情——今年四月十五,我夜泊九龙山前,缅怀山人的高蹈之风,灵感笔兴漫卷纸上。想在自己的竹子画里,写出这层意思,忍不住感慨,这世上到处有月,有箫声,商人也比比皆是,名贵的毯子更是不少,却鲜有九龙山人这样的性情中人了。
月夜泛舟,听箫,画竹,俨然风雅梦境。梦里梦外,两个性情中人。
还有,那年的五月十三,是竹醉日。杜秀才从太原来,赠冬心先生美酒一瓶。先生一面赏竹,一面把酒浇给竹子君喝。他搞得相当有仪式感。在甬道上,郑重地淋了满满三大杯。随后,又用酒兑着墨,挥竹一幅。
冬心先生自问:“竹子怎么能喝酒呢?竹子喝酒会醉吗?看我画的竹子,飘逸淋漓,真像是此君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冬心与竹,两兄弟。
我觉得有趣,百度了一下,还真是孤陋寡闻。“竹醉日,即为栽竹之日。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古人的“竹醉日”富有诗意。不知其他人是否在当天也舍得给竹子饮酒。现代人,只剩下植树节。
有趣的,还很多。
一日,冬心先生在江上养病,偶作小幅竹画。联想到,宋朝淳熙年间有个才子叫徐履,浙江省高考第一名,特别擅长画墨竹,画得传神极了,像是有风来,竹子呈笑态。传闻,他殿试的时候,在考卷结尾处,画了一枝竹,题云:“画竹一竿,送与试官。”清狂可爱!
回到竹子画。冬心先生画竹,60岁才开始。他不师法前人,而是在自己的宅子东西两侧,种了千万棵竹子,以竹为师。
竹子会教人怎么画竹子吗?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种竹子。跟着老师学,那是老师眼里的竹子。冬心的竹子画,只画冬心眼里的竹子。冬心眼里的竹子长什么样?看画便知。
冬心的竹子画,让人觉得怪。他是“扬州八怪”之首,不觉得怪,那才真怪。
冬心自己的理论是,画竹宜瘦,“瘦”,象征多寿。他还揶揄说,庄子曾提到有一种树,比十人合抱都粗壮。这种植物是不屑入画的。不然朋友会嘲笑画家是个爱吃肉的家伙。
冬心的竹子画有两种。一种是墨法写出来,竹叶很浓,怯怯的,实际是拙。竹节处,瘦得快要折断了,却有力道,很舒朗,其间有清风过隙。还有一种,完全用笔法勾画,宽叶,叶茎清晰可见,类似书法里的双钩。竹竿也是丰腴。这分明就是胖竹子嘛!两种画风,截然不同。后者,总觉得上头落了雪。
冬心画,有绝招。他有镜头感。各种视角的竹,像拍照,俯拍、仰拍,近景、远景,图式很丰富。冬心画墙外的竹,竹叶密密的在墙头挤挤挨挨,浓墨淡墨穿插,淡处仿佛生烟。白墙一面,让人思忖着,里头住了什么人。
冬心先生50多岁开始画画,出手即不凡。原因?他善于把玩。把玩,不是非要握个什么东西在手里摩挲,心情可以把玩,梦境也可以把玩。比如几枝竹子,他琢磨出这么多意思,玩出这么多花样,故事总也讲不完,实则玩的是一种心情。他种梅,他养鹤,“携鹤且抱梅花睡”。下笔全是文章。他还玩菖蒲,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把人家当儿子,当孙子,又是给菖蒲过生日。玩出了新意,玩出了门道。门道,即是门径,是道行。有道行的人画画,怎么画,就怎么对。
想起友人王大濛,无锡人,擅养菖蒲。精石刻,通绘画。他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大濛命不好,退休后本该享享福,却天天跟那些泥巴石头打交道,累得干瘦干瘦的,可怜得很。
大濛的母亲不知道,中国文人,玩的就是听风赏雨。扬州个园,主人为听风,造箫墙,箫墙孔连孔,风稍动,箫声起。又,文人植芭蕉于北窗,雨打芭蕉,一派闲愁。
去年到扬州,在冬心居住过的西方寺静坐,院子里仍有芭蕉,绿上了天。可惜未写,“冬心先生手植”。
眼下,正是春要来。念着冬心先生的“笋自林中来,白足一双”,觉得未来可期。好日子,哪里需要锦衣玉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