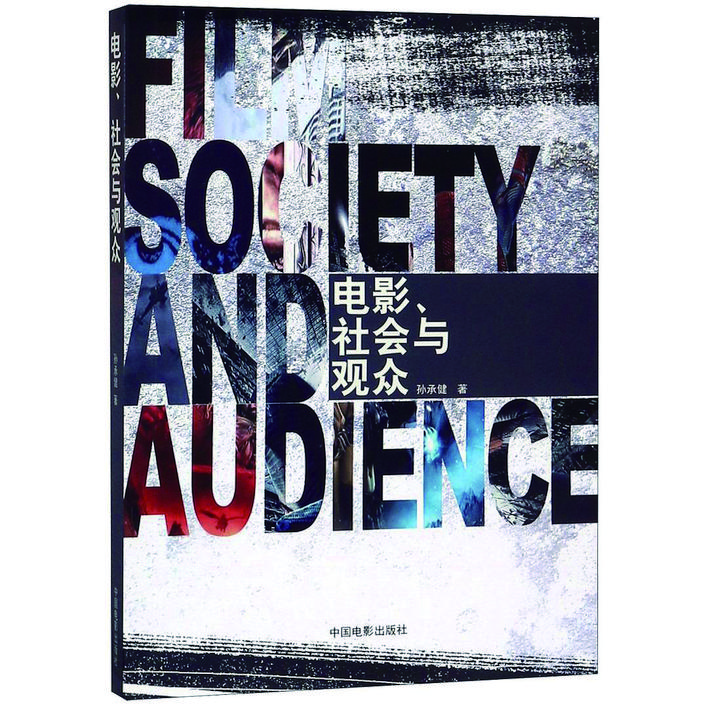虽然,中国电影并没有像美国电影那样,经历早期明星制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早在1949年之前,电影明星在中国电影之中就已然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阮玲玉、周璇、胡蝶、王丹凤、李丽华、陈云尚等等,一大批早期电影中的明星,不仅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更在电影之外,对包括时装服饰、流行歌曲等流行文化样式及其审美价值导向,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推动性效应。周璇在《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时至今日,甚至依然受到众多电影观众的喜爱。与此同时,在包括《良友》等一些早期时尚与综合画报之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早期电影明星中西杂糅的时尚造型,对那一时期以老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在流行文化层面所具有的引领性效应。
在改革开放之后,电影、电影明星与时尚流行文化等相关概念,在市场经济观念的推动下,彼此之间迅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既互为联系又互为建构的发展格局,由此也很快在社会大众之中产生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部国产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1984)在国内院线上映,这也是国产影片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主要题材元素,将时尚流行概念融入到电影叙事表达之中。影片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纺织厂的一群青年女工的生活变化为主线,借助“红裙子”这一服饰符号,聚焦时代变革过程中,社会群体基于个体价值与精神信仰层面的一系列转变,建构起整体叙事脉络。或许在今天的观众看来,无论是影片的叙事手段,还是流行文化的关照视点,已不再具有任何的吸引魅力,但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而言,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对于80年代之后,才刚刚恢复拥有诸如口红之类化妆品的年轻的中国女性而言,这部影片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显然已超越了影片本身。并且,影片中扮演女主人公的,那些穿着漂亮红裙子的赵静和姜黎黎等女演员,都是80年代出现在《大众电影》封面的“电影明星”,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正是基于此,据说影片上映之后,那条具有代表性的“红裙子”立刻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成为许多年轻女性“欲望”的对象,而这一现象背后所隐含着的,恰恰是对全民“灰黄蓝”时代的一种集体文化的反思。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电影明星及其商业价值的观念认知,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也经历了观念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一方面,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大众电影》为主要代表的,一些在当时大众文化领域较为流行的电影杂志,每一期都是以一位当时有一定知名度的,诸如陈冲、李秀明、张金玲、洪学敏、姜黎黎、赵娜、刘晓庆、斯琴高娃等等电影明星的时尚照片作为封面和封底,对于形塑电影明星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传播效应。而在另一方面,与电影杂志相比,这一时期大多影片开场的字幕列表,则显得更为“保守”,甚至缺少基于电影明星的商业意识。与之相对的,当下几乎每一部中国电影的开场字幕列表之中,都会在显赫的位置标明某某明星领衔主演等等字样,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从中也显现出明星的商业品牌价值之所在,并且,这种商业品牌意识早已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时间之中,电影字幕中的大多演员表,都是按姓氏笔画,或者是按照演员的出场顺序进行排列的。虽然也注明有哪些演员参加演出,但极少有某某演员领衔主演的列表形式。这种忽略明星商业品牌价值的观念和做法,甚至延续至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之中。比如,在1981年上映的,由赵焕章执导的影片《喜迎门》之中,演员列表是以出场先后进行排列的,主要演员在列表之中并未具有任何的优先地位。而1982年,在由谢晋执导的影片《牧马人》之中,演员列表则更是被放置在影片结尾之后,虽然在列表之中,两位主要演员丛珊和朱时茂,都被有意识地标注在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之前,但是,并未有“领衔主演”的标注字样。
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的电影运作机制,导致电影机构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同时,影片的票房收益也并不会对制片机构的生存造成任何影响;而在另一方面,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价值导向不可分割。
曾经有许多电影研究者,试图对电影明星在一部影片的市场收益层面的受众影响,进行一种精确化的研究,“像华莱士等论者(Wallace)就用相当复杂的计算方法分析各种影响电影利润的因素……他们的计算结果是:影星为热门电影带来的收入约占电影总收入的22%。”虽然,华莱士等人的这一研究结果,是以具体的量化数据得以显现,但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不得而知,并且,对于不同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电影观众而言,显而易见,其中所蕴含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这一结果本身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种参照数据,这一研究结果依然具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电影明星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力是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的。这其中,各种媒介机构所具有的主导性作用不容忽视,正如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所指出的,“一个明星形象在文化中的塑造,包含了无数媒体和环境对他或她的呈现:影迷杂志与主流新闻媒体、电视报道和人物传记、许多电影里的表演、访谈、传闻以及各种场合的出席。”
然而,格雷姆·特纳指出,“如果我们要讨论一部影片的意义,就要避免把角色看做是明星隐没自我的容器这种源自文学的观念。”也即是说,电影明星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层面的意义蕴含,以及这种意义对角色诠释的作用,实际上是创作者必须要慎重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选择演员有时可能是电影制作者塑造角色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选择一个正确的演员能够发挥特定明星的所有意义,并投射到银幕上呈现的角色身上。”这其中所关涉的重要问题,即是电影观众对明星的认同关系及其所饰演角色类型的心理期待。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谈到的,明星作为电影机构的一种基于商业化的产业运作机制,一种电影机构、媒介与观众共同建构的产物,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仅仅作用于电影机构本身,而是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更多不可预见的社会效应,甚或是经济收益。这其中,电影、电影明星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值得思考和分析。正如电影研究者所指出的,“流行文化特有的快感,它们都(潜在地)影响着观众观看一部影片的决策以及在观看时他们需要影片中的什么因素。这些都是社会与文化的快感,被个体获取,为他们自己所用,但并不会每个个体都如此。它们也是与流行文化中的其他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快感,因而揭示出电影的社会实践是如何包含在其他的实践以及其他意义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