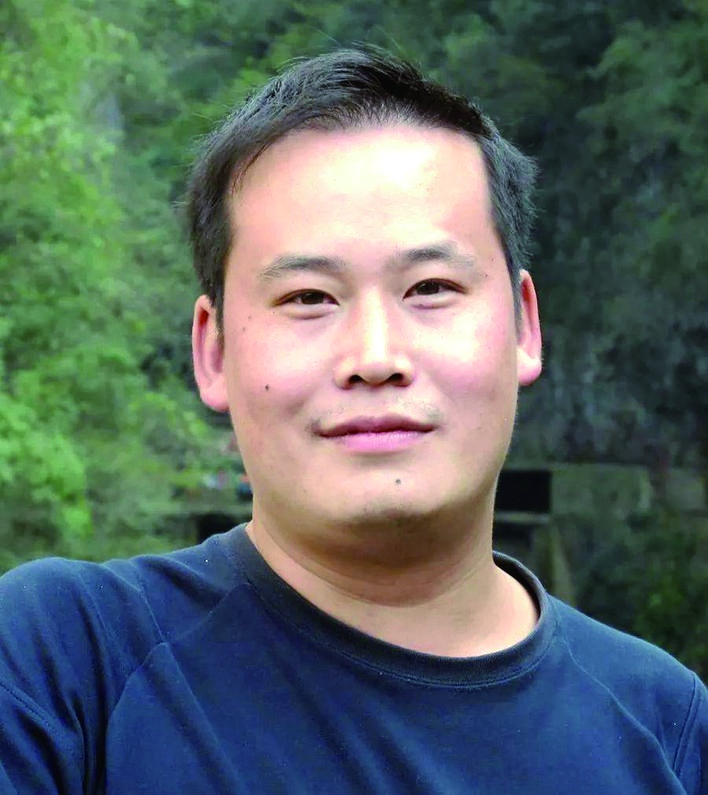贵州著名文学评论家杜国景这样判断贵州新时代的文学现状: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贵州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作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是何士光,第四代的领军人物是欧阳黔森。回顾40年贵州文学的历程,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贵州作家也逐渐完成了从第二代、第三代到第四代的过渡,这支队伍比之前不仅更为壮观,而且也更加成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比如何士光、叶辛、伍略、龙志毅、余未人、李宽定、赵剑平等,《乡场上》《蹉跎岁月》《孽债》《麻栗沟》等小说作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涌现了一批较有实力的中青年小说家,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肖勤、唐玉林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纵观贵州文学的发展历程,乡土叙事一直是优良传统,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延续至更年轻一拨的肖江虹、肖勤、曹永等,贵州作家长期扎根于乡土叙事,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世纪贵州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乡土叙事传统,在人性、历史、文化与形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并张扬了探索精神、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贵州历史上曾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闻名。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始以来,贵州成了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眼下,以城镇化带动、大数据产业支撑、高铁与高速公路建设、能源开发等为标志的一系列发展战略,正在深刻改变贵州的山川地理、经济社会与多彩文化面貌。
另一个事实是:随着扶贫搬迁、退耕还林等举措的实施,乡村人口大量迁徙,许多历史悠久、文化浓郁的古老村寨正在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聚居型村镇。这种物理空间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书写的变化。古老的乡村地理符号的消逝,意味着已经被美学化、文学化的具体指向不复存在,贵州作家如何面对这种猝然而至的空间轮转,是眼下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和所有乡村叙事面临的痼疾一样,有两个倾向需要警惕。
一是田园牧歌式的滥情。
真正深入乡村,依稀还能见着田园牧歌的痕迹,但这绝不能成为当前乡土文学描写的全部内容。在新农村的抒写中,各种异质文化已经深刻融入甚至影响着传统文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纠缠,此消彼长,呈现出百年难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恰恰是新乡土文学生长的可能性。城市人和乡下人,一直都是中国人之间文化身份最广大的差异及相互确认的标志,现在,这种认知正在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复杂的确认和区分方式。剧烈的突变,文化的融合、各种因素纠缠和影响带来迷惘和阵痛,我们还很少有作品从容全面表现过。
二是纵情于暗黑的书写。
正如评论家施战军所言:“这类作品特别着迷对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封建性、非人性的描绘,先把批判意识置顶,成了习惯性的主题先行。不仅和现状有一定距离,不少是胡写的,把乡村生活写成宫斗模式。……只要回去就会发现现在乡村权力结构并非如此。”
生活的匮乏,意识的滞后,端坐书斋寻章摘句,如何能洞悉生活现场的丰富和斑驳?加上对暗黑部分的过分关注,让我们操作黑暗和垮塌的部分特别得心应手,构建崇高和恪守庄严的能力却严重不足。
文学的核心是人,乡土书写的核心是农民。城乡的快速融合,城市的各种服务行业、手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及一些合资、外资企业中的蓝领工人,身份还是农民,写出他们的复杂情感、幽深精神,仍旧是乡土书写的转场和延续。如果还把眼光局限在村落小镇这样封闭的领域,文学目光的探照自然就显得逼仄。
新世纪以来,贵州的变化日新月异。传统乡村在时代的脚步中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古老的、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那些遗迹正逐渐消失。但这不代表乡土文学书写的消亡,物理空间的挤压,让作为文学核心的人开始转入更大的场域,这恰恰让文学的空间感和丰富性成为可能。所以,以贵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域的新时代乡土书写,正成为作家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只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时代,对生活,对人心有更深的体察和关照,才能更好地延续这一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