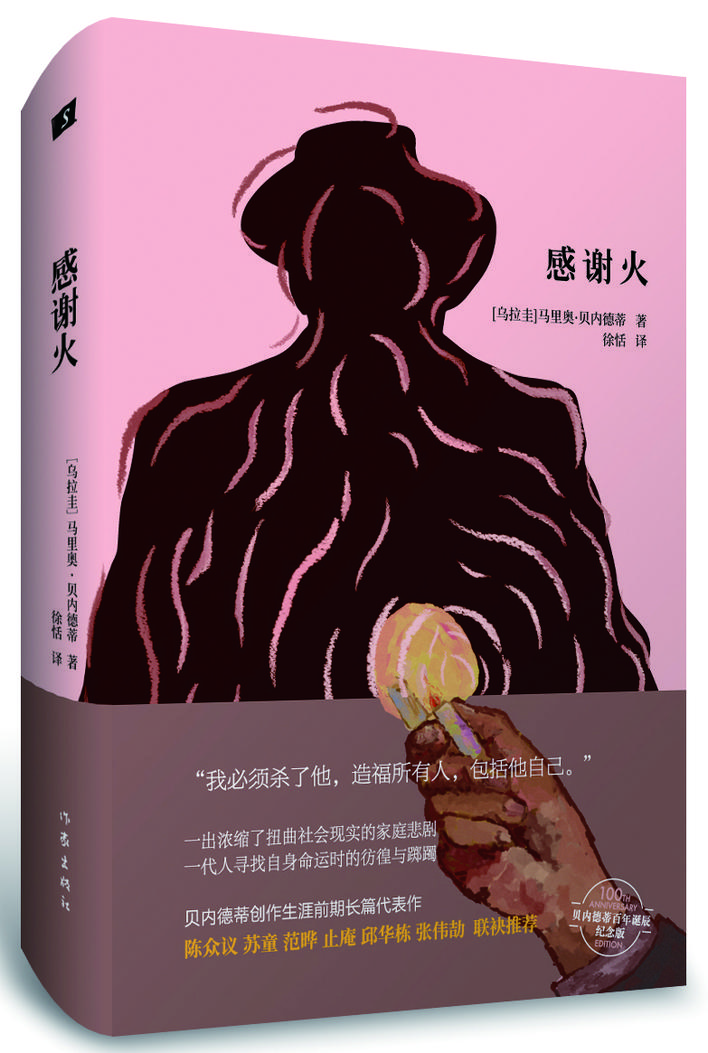马里奥·贝内德蒂是乌拉圭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有八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有无乡愁》,诗集《办公室的诗》以及长篇小说《休战》《感谢火》《破角的春天》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大量拉丁美洲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内,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如今,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科塔萨尔、波拉尼奥、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已成为无数人钟爱的作家,但是,贝内德蒂的作品却一直没有受到应得的关注。1969年,奠定贝内德蒂在乌拉圭文坛地位的《休战》在国内出版,之后,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但是,即将迎来退休生活的桑多梅与年轻的阿贝雅内达悲惨的爱情故事似乎并未在读者间引发共鸣,蒙得维的亚人办公室——家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唤起读者的兴趣。或许个中原因在于贝内德蒂的叙述都太为“平常”,他笔下的蒙得维的亚常年被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灰色笼罩着,与色彩斑斓的马孔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乌拉圭国内一些批评家诟病贝内德蒂的原因,在贝内德蒂成为乌拉圭最受欢迎的作家后,他们仍指责贝内德蒂只会写些鸡毛蒜皮。然而,考虑到乌拉圭特殊的国情,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贝内德蒂的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是由乌拉圭的社会现状决定的。
1904年至1929年,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和他的继任者发起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使乌拉圭成为当时拉丁美洲为数不多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政府职员和雇员成了乌拉圭社会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美国《时代周刊》甚至把乌拉圭称为“拉丁美洲的瑞士”,乌拉圭人也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喊出了“没有国家能和乌拉圭媲美”的口号。但是,50年代的繁荣只不过是经不起推敲的表象,是巴特列时代的改革残留的余热。事实上,由于政府没有推出适当的后续政策,乌拉圭的经济、政治、文化早已陷入因循守旧、几近停滞的状态。1955年,经济危机爆发了,为了遏制危机蔓延,政府引入数额巨大的外国贷款,并向国民征收高额税款,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日益强大,开始向南边的邻居施加压力。这种内患外忧的境地使得一大批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以《前进》周报为主阵地,发表评论文章、小说、诗歌、戏剧等文艺作品,抒发对社会的不满。贝内德蒂就是应运而生的批判一代的主力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因缺乏沟通和交流导致的冷漠、对舒适生活的留恋、对存在意义的探寻等会成为贝内德蒂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元素。通过对日常琐事精准的观察和生动的描写,贝内德蒂试图在作品中重现彼时乌拉圭社会的真实状况,唤醒耽于当下舒适生活的乌拉圭人民,进而探索实现彻底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感谢火》正是贝内德蒂在这方面的又一次尝试。
贝内德蒂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感谢火》出版于1965年,此时距《休战》出版已有五年,离《破角的春天》出版还有十七年。贝内德蒂的这三部作品常被置于同一个序列中,评论家指出,这三部作品清晰地体现了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贝内德蒂的观念。《休战》通过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乌拉圭的社会状况,《感谢火》和《破角的春天》则分别关注了个人和集体改变社会的尝试。在从观察者视角向行动者视角过渡的过程中,《感谢火》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小说主要聚焦在拉蒙·布迪纽——一个脱离社会、脱离自我的人——注定失败的弑父行为上,通过阐述拉蒙为何弑父又为何注定失败的关键问题,贝内德蒂批判了扮演停滞社会同谋的大众,与此同时,他还在作品中寄托了自己的美好愿望:希望《感谢火》引燃的些许火星能引发一场大火,彻底烧掉乌拉圭的“稻草尾巴”。
那么,拉蒙为何弑父?他弑父的行为又为何注定失败呢?
我们可以看到,《感谢火》的主体叙述是由主人公拉蒙·布迪纽完成的。他的叙述,尤其是在涉及自身时,是破碎、片段式和充满偶然性的。将零散的叙述拼凑起来,我们得知:拉蒙·布迪纽是乌拉圭大人物埃德蒙多·布迪纽的儿子,经营着一家旅行社。乍一看,这样的生活似乎无可挑剔,事实上,拉蒙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安逸的生活,如果三年级时他没有在屏风后见证慈爱的爸爸厉声斥责并殴打一直保护着他的妈妈。屏风后的那幕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从那刻起,拉蒙无比依赖的父亲,那个“完美无瑕、优雅、胡茬总刮得干干净净、自信审慎地对待一切、毫不犹疑地理解一切”的男人被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卑鄙无耻的老头。父亲的形象在转瞬间轰然崩塌,而拉蒙通过父亲建立起来的世界也被颠覆了,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年岁的增长没有改善这种状况,步入中年的拉蒙对妻子苏珊娜的爱和激情早已不再,和儿子古斯塔沃之间又横亘着彻底的不理解,同时,扭曲的社会观念和道德价值让他无所适从。就这样,他脱离自身、脱离家庭、脱离社会,深陷存在主义危机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拉蒙不停地在回忆中追溯,试图找到那个出错的时刻、改变它并将自己的人生重新纳入正轨。于是,弑父成了他惟一的出路。
弑父是拉蒙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惟一结论,而弑父行为的失败也是早就注定了的。首先,拉蒙杀死老头只是为了找回爸爸,从而找回自我。自始至终,拉蒙的决定都是从主观意识出发,因而是脱离现实、不可行、不坚定的。他无法说服自己打消所有疑虑,因为他清楚,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老头给的,杀死老头意味着毁灭一切,不仅是自己的一切,还有苏珊娜、古斯塔沃、乌戈和多莉的一切,而这并不是他期望看到的。在他看来,弑父是惟一一条通往救赎——包括自我救赎和对爸爸形象的救赎——而非毁灭的道路。他也清楚,尽管自己痛恨老头,却仍深爱着亲爱的爸爸,如今,这两个大相径庭的形象在同一具躯体中共存,杀死前者就意味着抹杀后者,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抹杀爸爸的形象等同于抹杀自身。
其次,日复一日单调且安逸的生活麻痹了拉蒙所属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丧失了作出改变的能力。拉蒙不认同所属阶级的价值观,但他仍然是停滞不前的社会的受害者,被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禁锢。因此,尽管他试图打破种种限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屏风后目睹的那一幕中断了他童年时期的发展,之后,一成不变的安逸生活又阻隔了他的自我救赎之路,乃至每每到了“需要做些什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时,一种 “类似童年恐惧的东西”就会排山倒海地向他袭来,使他无法行动。最终,拉蒙悲哀地意识到,“一切都强于我:老头、陈词滥调、阶级禁忌、偏见”,惟一的救赎之路不复存在,出于对自身处境的绝望,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终结自身。
有趣的是,在《休战》中,贝内德蒂也曾就弑父和自杀进行探讨。可以说,拉蒙的自杀和《休战》中哈伊梅的“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拉蒙自杀或许是出于逃避心理,但比起《休战》中想自杀却缺乏勇气的阿贝雅内达先生,拉蒙已经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自杀是应对荒谬世界的一种方式,但荒谬必然导致自杀吗?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给出的答案是:存在另一种方式,即希望,但希望只能通过信仰或反抗实现。贝内德蒂在《感谢火》的最后两章也给出了和加缪类似的答案:拉蒙自杀的行为可被视作一种牺牲,他的死让周围的人认清现实并试图作出改变。如果《休战》中阿贝雅内达的意外死亡在桑多梅和阿贝雅内达先生心中掀起了波澜,使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生活;《感谢火》中拉蒙的牺牲则证明了弑父的不可行和无意义,敦促下一代人继续探寻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下一代人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吗?经历了流亡的贝内德蒂将在十七年后出版的《破角的春天》里给出答案。
(摘自《感谢火》,【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