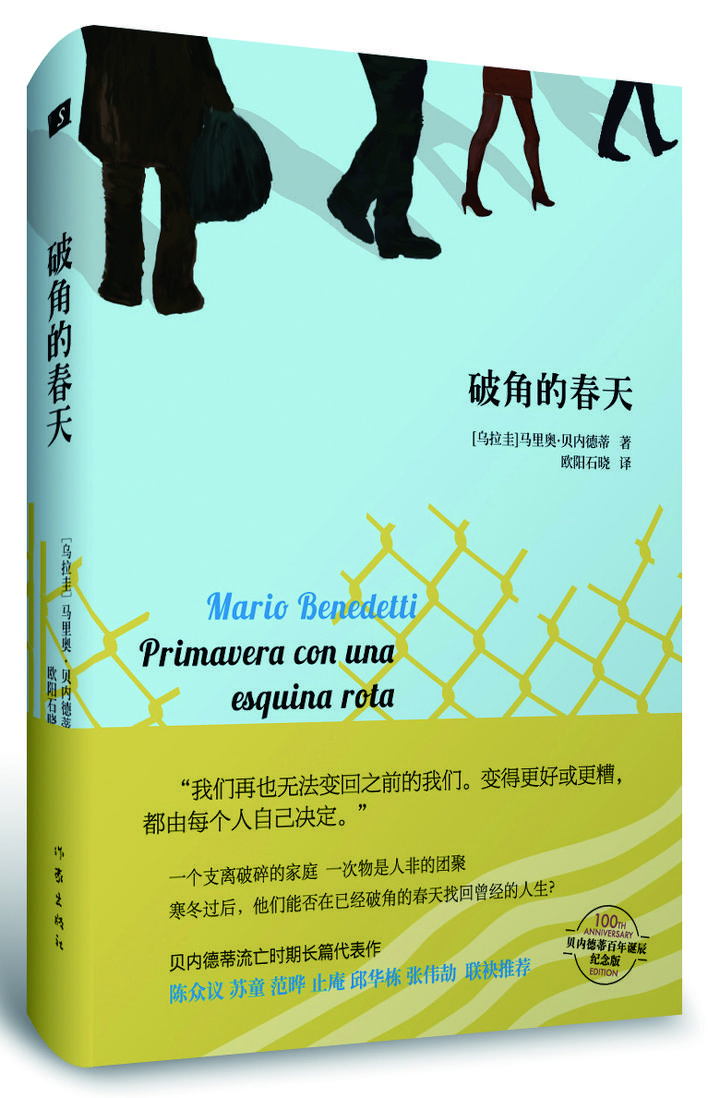我是在刚搬来马德里生活不到两年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贝内德蒂这个名字的。
当时我与朋友合租一套公寓,朋友的一位朋友因居无定所也搬来暂住。他看起来五六十岁,皮肤黝黑,听说他曾经出过两三本书,写过诗和歌词,还当过战地摄影师。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过着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生活。
白天家里常常就我们俩,我学西语、看书,他有时候拿个大本子,写写画画,抽很多很多的烟。有时候累了就一起聊天,他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同时也荐书给刚学西语不久的我。某天他提到一位他非常喜爱的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并把带在身边的惟一一本贝内德蒂的书借给我读——《破角的春天》。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贝内德蒂的文字,又自己找来他许多别的书来读。
马里奥·贝内德蒂于1920年出生于乌拉圭塔夸伦博省的帕索德罗斯托罗斯(Paso de los Toros),父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贝内德蒂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省会塔夸伦博,后来又搬去了蒙得维的亚。由于家境贫寒,贝内德蒂只念过几年书,自十四岁起,他就靠打工谋生:售货员、收银员、速记员、会计……他在十九岁时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以各种杂工为生,但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发现了自己对诗歌的热爱。在返回蒙得维的亚后,他加入了当时极具权威的《前进》周刊(Marcha),那本反思和分析拉普拉塔河流域文化的杂志造就了乌拉圭三代知识分子,比如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等人。贝内德蒂在1945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并随后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短篇集和诗集,声名鹊起。
对贝内德蒂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而言,1960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他在美国住了五个月,公开加入了一个支持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并由此写作了第一部让他陷入危险的文本——《麦草尾巴的国家》,该书描写了乌拉圭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没落。从那之后,贝内德蒂更加踊跃地参与政治,甚至是军事活动。由他领导的左翼政党“三月二十六日运动”(Movimiento 26 de Marzo)在后来融入了“广泛阵线”的政党联盟。1973年7月27日,军人发动政变,开始黑暗的独裁统治,使乌拉圭成为全世界政治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贝内德蒂辞去在大学的工作,离开乌拉圭,开始长达十二年的流亡生活,辗转于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并因此创造了那个由他命名的概念:去流亡化——无论是在他的生活中还是在他的文学中,这一概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整个流亡生涯中,贝内德蒂写成了《破角的春天》,以及其他两部短篇集和四部诗集。所有作品都关乎同一个主题:流亡。
《破角的春天》的创作始于乌拉圭公投前一个月,那时候的贝内德蒂已经接受并且内化了流亡的经历,也正因如此,他能够以一种更坚定且持久的方式来探讨这一主题。在这本书里,他以流亡者的身份,也就是他的“真实身份”,站在一个新的空间,对过去的回忆与遗忘进行辩证,以及重建。它既关乎故乡的过去——继续履行对过去的承诺和义务,同时也涉及与新地方展开对话,完成文化的移植与渗透。
故事的主角分为两类:真实的和虚构的。斜体的“流亡”章节由作者及其他人的真实流亡经历组成;其他章节的叙述者则是圣地亚哥、格蕾西拉、拉斐尔、贝阿特丽丝和罗朗多这些虚构的人物。全书采用了多种写作形式:叙事、书信、内心独白、诗歌和对话,字里行间透露出小说中不曾描绘的事实:监狱里的拷打刑罚,家庭成员的内疚感,以及将乌拉圭拖入暴力与沉默的历史事件。
圣地亚哥以第一人称描述自己内心的流亡,而父亲拉斐尔的自白则与从狱中(经过审查后)寄来的圣地亚哥的信件相映成趣,他们的交流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既内省,又被联系了起来。惟一不同的是,拉斐尔在同样经历着内心的流亡的同时,也经历着现实生活中外部的流亡。他除了对在狱中的儿子感到内疚,要照顾一起流亡国外的儿媳和孙女之外,同时还需要面对在异国他乡的新生活、新感情以及新语言的挑战。正如他以积极的心态“深入探索那个叫莉迪亚的国家”但同时又坦承“有太多的话题只能与同胞才能开诚布公地聊得尽兴”,他对于流亡国的语言同样持保留的态度——“我已经开始欣赏(当然,我不会真正使用)当地的习惯用语了”。在拉斐尔身上,可以看到贝内德蒂的影子。拉斐尔跟贝内德蒂一样,在长时间没有进行创作后又“感到了”,或者说“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和需求。他们俩都认为,写作是面对流亡、建造个人与国家的认同的媒介,而小说中连接虚构与证据的桥梁也是重建一个新的祖国所必需的。
贝内德蒂睿智又机灵的语言在这本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行文中跳跃着双重语调:有时严肃,有时幽默。作者在沉重悲哀的主题叙事中用文字游戏和嘲讽的语气让人不禁莞尔。尤其是贝阿特丽丝的章节,小女孩以文字游戏学习“政治犯”“自由”“祖国”“赦免”等本不应属于她所处的世界的词语,用天真的方式逐渐认知这个破碎且混淆的世界。由于西班牙语与汉语所属体系的不同,很多巧妙的文字游戏无法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常常为作者出神入化的表达而惊叹,又为自己无法将那一表达的精髓完整重现而沮丧。只能以注释的方式做出解释,希望读者可以借此体会到原文的巧夺天工。
说回那个最初介绍我阅读贝内德蒂的朋友。
印象中后来某天他接到一通电话,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他的某个中篇刚刚获得了阿根廷某文学奖。我们都很高兴,开了香槟一起庆祝。再后来,他说他要去乌拉圭生活了。他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想要去乌拉圭,那里天气好,适合他。于是他买了机票,据说准备去蒙得维的亚的一间书店工作。再后来渐渐就没了他的消息。时光流逝,过了大半年,听朋友说他回到了马德里。又过了几个月,听说他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再后来,就是他去世的消息。
我和他不过是在同一个屋檐下萍水相逢了几个月,但得知他去世时依然十分难受。也许有人会质疑他的生活——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失败的生活”,但我仍以为,能像他那样纯粹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活在文字、文学和影像里,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他在年过半百时准备彻底离开故乡前往另一个国家生活,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流亡。当他向我描述蒙得维的亚明媚和煦的生活时,我在他天真勇敢的表情中看见过一束光亮。
因此,去年,当编辑说打算引进贝内德蒂的书,想请我翻译《破角的春天》时,我感到了某种宿命的回归。
正如贝内德蒂试图通过这本书说服读者,也说服他自己那样:即使经历了一切,即使春天已经变异了,破角了,但它依然会在看似无止境的冬天过后来临。
(摘自《破角的春天》,【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