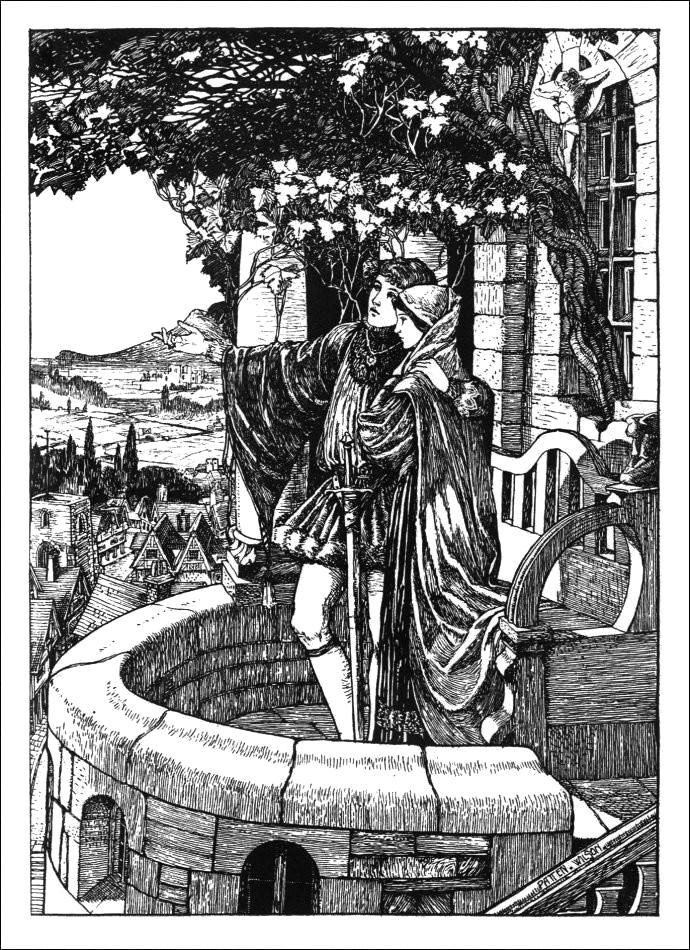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科学界一个显著特征是“启蒙科学”向“浪漫科学”的转变,而浪漫派诗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法国著名科学家乔治·居维叶的论断,英国探险家约瑟夫·班克斯开启的《奋进号》之旅,是“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之举,集博物学研究,天文学测量和科学考察于一体,并将范围和规模延伸向不断扩展的全世界。从各个方面衡量,这都是一次堪称与史诗《奥德赛》相比肩的浪漫求索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进号》之旅亦带有柯尔律治名诗《忽必烈汗》(1797)的神秘意味,旨在向世人讲述某个曾经神圣而后“失陷”、并且再也没有回复往昔荣光的人间天堂。这一类比,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1817)中的名言:“科学知识对于史诗创作来说必不可少。”
浪漫派诗人与自然科学渊源颇深:济慈早年为药剂师学徒,后考入牛津大学国王学院并在学院附属盖伊医院研习医学;骚塞在湖区亲自参与化学家托马斯·贝多斯的气体实验;雪莱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林德的关门弟子,对各种理化实验更是兴趣盎然。在《致玛利亚·吉斯伯恩书信》一诗中,雪莱认为,“理智与情感,知识和美德/所有的合力,使得平庸的世界熠熠生辉”,并为即将到来的“科学世纪”而欢呼呐喊。然而,如果论及自然知识的深广渊博,则上述诸人谁也无法与柯尔律治相颉颃(1824年,柯氏荣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诗人极大的荣耀)。据说,柯尔律治曾计划用20年时间创作一部史诗,而其中一半时间将用于收集素材,尝试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武装思想”。在写给出版商科特尔(Cottle)的信中,诗人列出了该计划的详细科目:“我将粗略了解一点数理学知识,广泛涉猎力学、流体静力学、光学、天文学、植物学、冶金学、化石学、化学、地质学、解剖学、医药学等科学门类,在旅行、游历、历史中获取有关人类心灵的科学知识。余下的10年,我将一半时间用于创作,一半时间用来修改润色。”
其实早在1790年代赴德国留学之前,柯尔律治(1772-1834)对康德哲学及以洪堡为代表的启蒙科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笔记中称即将到来的19世纪为科学的“千禧年”(Millennium)。游学德国期间,以施莱格尔和歌德为首的德国浪漫派对启蒙科学的质疑令他眼界大开:施莱格尔对科学逻辑分析方法大加鞭挞,痛斥启蒙运动的科学世界图景割裂了人与宇宙的隐秘联系。歌德则提倡一种体验式的、整体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以对抗并修正牛顿、笛卡尔理性主义和机械论所造成的冷冰冰的科学主义(scientism)。返回英国后,柯尔律治著文抨击启蒙哲人滥用科学手段,“冷酷地试图从自然中汲取知识”,而他则坚决主张“科学不应该导致自然与人之间的任何分裂”。在柯尔律治看来,科学主义者将理性狭隘地理解为具有逻辑性和分析性的工具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想象力所代表的创造性和整合性的认知功能——而这一点,恰好是启蒙与浪漫派科学观大异其趣之处。
与华兹华斯兄妹隐居湖区期间,经骚塞(好友兼姻亲)介绍,柯尔律治结识了在学界崭露头角的科学家戴维,二人相见恨晚。诗人自称在旅居德国的时候,确曾“在布卢门巴哈(德国人类学家)门下学习生理学和自然科学”,并且出版过一本科学著作《生命的理论》——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自然哲学学者(他一向反对科学家这一称谓,以为类乎“俗气的工匠”)。戴维亦自承在乃师贝多斯博士研究基础上,已成功发明出氧化亚氮气(俗称笑气,laughing gas)。随后,柯尔律治在戴维实验室多次进行了亲身体验。“我从未感受过的纯净的愉悦……一种暖洋洋的气息包裹全身,仿佛从冰天雪地回到温暖的家中。”这与他当年吸食鸦片的感觉极为相似。正是在此状态下,他创作出不朽诗章《忽必烈汗》。此时,“想象力散发,消解,融合,目的是为了创造。任何物体一旦凝固,便意味着死亡”。像一个世纪后的弗洛伊德一样,柯尔律治发现,相对于理性和有意识,非理性或无意识的力量显然更为强大,于是他益发坚信:知觉的起源和诗歌一样无从探究。他把鸦片称为“甜美的毒药”,将笑气称为“甜蜜的牛奶”,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像大海一样深广的思维的悸动”。而依照他的诗学理论,“惟有深邃的哲学头脑才能谱写伟大的诗歌”。
在此期间,柯尔律治热切地拜读戴维发表的著述,并多次赶赴伦敦聆听他的讲座。当别人问他为何对化学讲座情有独钟时,诗人回答说,“为扩充我的隐喻库存量”。在致戴维书信中说,他坦承每当看到《晨报》上刊出戴维电流研究取得新进展的消息,自己都会感到兴奋:“我的房间、你的小花园、你的冷却槽,还有那月光下的岩石……我有多少美妙的梦,都是与你戴维联结在一起的呀!”与此同时,在他本人的诗作中,也展示出之前不曾有过的与科学标准相符的精确性。柯尔律治相信,新的诗文和新的科学密切相联,因此也应当通过某种方式结合为一体。为此他敦请戴维搬到北部地区居住,在湖区建立一座化学实验室,并表示:“我将猛攻化学知识,强劲之势会有如鲨鱼。”
在柯尔律治看来,化学实验和研究不但将对立的非物质性思维的优点结合到一起,而且不会损害其观念的明确性,甚至还使得它们更为明晰。他坚持认为,科学作为人的行为之一,“是必须怀着希望的激情进行的、带有诗意的努力”,也是人类建设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世界这一意愿的高尚体现。此外,作为对欧洲神秘主义学说(雅各布·波墨、斯维登堡)素来推崇的学者,柯尔律治对戴维的“体粒子”假说大加赞赏。戴维设想人的所有知觉,都直接取决于人体内一种所谓“体粒子”的变化:“知觉、观念、欢愉、痛苦,都是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这样说来,有关思维的定律可能并不会与有关粒子运动的定律有所不同。”
关于这一假说,柯尔律治还与另一位好友、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约瑟夫·亨利·格林进行了深入讨论。诗人认为,“生命能量”或“生命原则”无疑是客观存在,但与生理学没有任何关联。这一“生命原则”中包含一个固有功能,即所谓“个性化”,其具体表现是低级生命向创造链条(或称宇宙巨链)的高端移动,并最终导致具有独特的“自我意识”的人的出现,而“自我意识”中又包括了道德观念和精神的自我感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魂魄”。
柯尔律治在戴维假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个性化”学说,日后成为他的“有机(体)”诗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究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西方科学史上自古希腊以来“生机论”或“活力论”的翻版。诗人与自己的医生兼朋友詹姆斯·吉尔曼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关一个生命新理论的札记》,目的在于将生命这个神圣的概念与科学融为一体。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魂魄”是的确存在的,但并不能用“光”“电”与之类比。换言之,诗人不相信生命为纯物质性的表现,但同时也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神秘的“生命力”(这是他对传统生机论的超越之处)。对此他曾不无幽默地说:“对于所有的流体和以太的概念,无论是磁的、电的、万有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经过九蒸九晒而成的超级缥缈的设想,我都绝对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与法国著名医学家比夏(1771-1802)在《生命与死亡的生理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生命定义颇为契合——根据这位欧洲名医的看法,生命无非是“抵抗死亡的所有功能的共同表现”,因此即便存在“魂魄”,其功能亦只在于“抵抗死亡”,并无神秘可言。(据传当时科学界有一句名言:“金刚石是有感觉的碳”,而另一位科学家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水晶一定是发了疯的金刚石!”)
通过上述科学研讨,柯尔律治深知无论是研究物理化学还是人体化学,最终都可以极大地造福于人类自身。“人们的情感和观念的每一点变化,是不是都必然与人体内的某种相应改变有关呢?我们应当通过实验确定这一点。一旦发现此种关系,便可认知与人类存在有关的规律……化学会以其与生命规律的关联而成为所有科学中居于顶点的重要成员”——这也是当时湖畔派诗人的共识。也正是这样的共识,将柯尔律治和戴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1801年后者应邀赴伦敦担任皇家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1809年,柯尔律治完成一首赞颂戴维的长诗“天才与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自称此乃“这些年来我惟一的诗作”。诗人讴歌英国有了戴维,化学遂由炼金术的别称一变而为得以与天文学比肩的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由此戴维本人也成为了一种象征:代表“启蒙科学”向“浪漫科学”的过渡,同时也预示着这一转变必将引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戴维发明的“安全矿灯”拯救了成千上万矿工的生命)。
除了化学和生理学,柯尔律治对物理、天文等学科也颇有研究。他曾用棱镜进行过光学折射实验,由此明白了彩虹的原理——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说:“天上的冰雾过往匆匆,而彩虹稳稳不变。这是狂风急雨的瞬息万变与神妙永恒的何等结合,又是图像与感觉的何等结合!它真是暴风雨的女儿——产生自狂暴的安详啊。”可见,在这里,柯尔律治既接受了科学观念,承认彩虹产生于“冰雾”的折射,但同时也指出,这一在急剧的动荡中给观察者造成的“狂暴的安详”,具有强大的象征作用,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唤起人们的诗情。而后者在他看来更是“上天神明”给出的一个强有力的标示(他并不认为科学与诗意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有何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他与17世纪著名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1605-1682)在《医生的宗教》《瓮葬》等著作中表达的立场颇为相似。作为联想心理学的先驱,布朗的名言是,“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存在。”
此外,据考证,柯尔律治创作笔记中大量出现关于日月星辰(尤其是月色、云彩)等自然景物的描绘极有可能受到当时流行的“天文学热”的影响——天文学家威廉·赫舍耳的天文观测台乃成为众人的朝圣之所。华兹华斯、济慈、雪莱等人诗作中对天文星象的描写皆不乏精妙文笔,如华兹华斯曾将牛顿作为在知识的海洋中破浪远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写进他的长诗《序曲》;济慈将自己初读荷马诗歌的感觉,比喻成探险家发现新世界时的无比激动心情:“我已经遨游过不少黄金的领域……我自觉仿佛守望着苍天,见一颗新星向我的视野奔涌而来”——诗句将上下求索的诗思与天体明亮的光芒联系到一起,堪称神来之笔;雪莱名篇《西风颂》(1819)传诵一时,其中不乏“欲来雷雨的卷发”等佳句,而他的另一首名诗《云》(1820)更在字里行间反映出诗人对云的形成和对流运动了解非常深入,达到“相当专业”的水准。
与之相似,柯尔律治据说早在16岁去伦敦求学之时,便创作过一首题为《致秋月》的十四行诗(诗中提及流星运动轨迹)。移居湖区之后,在他的许多出色诗文中,更有大量对月色的吟咏。《霜夜》(杨德豫先生译为《午夜寒霜》,1798)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时诗人在坎布里亚郡凯西克小住,寓居格雷塔厅,此处原来是一处观象台。诗人在此将观测到的意象与诗歌融为一炉,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效果。他的名诗《失意吟》(1802)也在开篇处描绘出“澄澈冬夜”的一弯新月“将旧月揽在自己怀中”的瑰奇景象(这一天文景象俗称“新月抱旧月”,而新月弯中隐约可见的、与新月合为一体的暗灰色圆形,实际上是地球反射的太阳光映照到月面上又被反射的结果)。后来,当诗人孑然一身寓居马耳他之时(1805年),也曾用航海望远镜观测月亮和星体,并记录下若干崇拜月亮的文字。即便在他晚年所作的《云乡幻想》(1817)等作品中,也时常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在园中凝望月光的老人,或“伫立在开俄斯海滨的盲诗人(荷马)”。尽管这位老人已双目失明,“目光呆滞有如雕像”,但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神秘力量,让他能够感受到洒到他身上的月光,并从月光中感受到幸福——“他一动不动,双目失明的凝视无比集中,/仿佛整个面庞上都是眼睛。”根据蒂姆·富尔福德(Tim Fulford)在《浪漫主义与科学》(Romanticism and Science,2002)一书中的考证,柯尔律治在此处极有可能化用了晚年盲目的前辈诗人弥尔顿的典故:弥尔顿在长诗《失乐园》里,描写反叛天使所持巨大无比的发光盾牌时,提及伽利略的折射式望远镜,以及伽利略运用“我那个眼睛”(指代望远镜)做出的发现(据弥尔顿自述,出于对科学巨匠的崇敬,他曾于1638年去意大利游历时拜望过伽利略,并与之探讨新的宇宙观——其时科学家已双目失明)。当然,诗人最为传神的描摹出现在代表作《古舟子咏》中:“月亮正移步登临天宇,/一路上不肯停留;/她姗姗上升,一两颗星星/伴随她一道巡游/月光像四月白霜,傲然/睨视灼热的海面;/而在船身的大片阴影中,/着魔的海水滚烫猩红,/像炎炎不熄的烈焰。”
苏格兰启蒙哲人亚当·斯密在《天文学史》(1795)一书中曾指出:“好奇……而非从发现中谋利之期望,乃是促进人类研究哲学(自诩能揭示所有自然现象中隐含的联系的科学)的第一原则。”柯尔律治晚年评论华兹华斯、班克斯、赫舍耳、戴维等科学人文巨匠时宣称:成年人终其一生保有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天才的特权和标志”。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荣誉院士理查德·霍姆斯在《好奇年代》(2009)一书中所言:浪漫科学时代的特征——是包括柯尔律治本人在内的天才人物“纯粹出于好奇”而追求科学发现。在那样一个时代,科学家是热情洋溢的诗人,诗人也是充满想象力的科学家——大自然是他们共同的神秘女神缪斯。同时,也正是在上述主张诗歌与科学融合的天才人物的合力作用下,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启蒙科学”才逐步让位于19世纪兴盛一时的“浪漫科学”——以电磁学、矿物学、地质学(甚至催眠术、颅相学)等为标志——直到19世纪中期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实证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