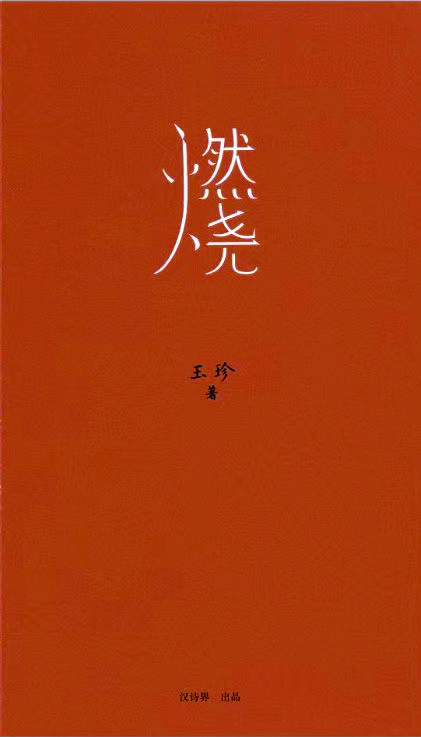关键是去写,去呈现,去创造有魅力的语言
师 飞:今年比较特殊,一些人直呼“凶年”,也有一些人申张“新变”;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追逐时代风尚的人,但还是好奇已经发生的一切对你是否有影响?
玉 珍:有,“没人是一座孤岛”,人人都处在蝴蝶风暴中,在这种外部的推力下,我好像已经完成了之前从没有过的改变,这不是完全靠自觉而达到的,发生的一切构成了现在。人在面对环境变化后的反应决定了他的一生。疫情的发生使我思考了很多平时忽略的东西,那时候创作成为巨大的慰藉,我要思考要解决要写的太多了。要珍惜时间。今年看了很多黑白电影,重看了一些经典,相当好。给我的震撼非常大,与我的创作一起成为晦暗岁月的光明。
师 飞:谈谈写作吧,这一年有没有什么调整?
玉 珍:我觉得今年是我写诗以来惟一没将时间和大脑留给诗歌的一年,也是思考人生与巨变、死亡与厄运最多的一年。我们过去聊到过人生的意义和创作过程中虚无感之类的问题经过今年,对待困境我还是保持过去的想法;我得穿过困境。
师 飞:我知道你写了许多散文随笔,有写小说的计划吗?
玉 珍:我小时候其实想当小说家,但后来写了诗,我跟很多朋友说过我写不好小说,跟你也说过,你说你也差不多,其实写什么文体不重要,关键是去写,去呈现,去创造有魅力的语言。譬如我们现在的对话,严肃的,雄辩的,自白式的,随意的,友人唠嗑式的,各种口吻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一种简约隽永的辩证法
师 飞:我尝试过那种一个人自我辩驳的对话,但有个问题,就是很难分清那是自说自话还是真正的对话;稍严肃一点就会发现,一个人无法借助语言彻底隐身或是变换身份。相比美,我更乐于见真,并且我还坚信真理很大程度上与真诚有关。谈谈你前段时间刚出版的那本新诗集吧,叫《燃烧》是吧?
玉 珍:这本诗集设计得很有质感,必须谢谢朵渔老师对我的信任,他让我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反省,做出来相当漂亮。但我喜欢给自己挑刺,对自己非常苛刻,面对这本诗集我陷入自我怀疑,觉得它离我对自己的期待还差一截,我在挑选作品的时候感到了一种麻木,认定这两年的诗歌发生了停滞和退步,今年几乎就没怎么写诗了,我挑选的那些作品是否太相似,是否有生命力,我写了那么多,哪些是好的,什么是好的,我总是不满!对自己问来问去,我跟朵渔老师也谈到了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说这很正常,说我在思考反省,说明我会进步,我也希望是这样,希望经过一年的疏离和放空,能有突破。
师 飞:《我的梦——》这首诗只有两行——“我的梦如此浓烈以致溢出现实/我的死过于缓慢以致生生不息”;还记得当时怎么写出来的吗?
玉 珍:我不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几年前,某个晚上,它突然就冒出来了;但我思考过这类问题,瞬间的结晶来源于长期的聚精会神。
师 飞:从阅读体验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精心提取的结果,你似乎想表达很多,但最终只借助梦和死亡展示了一种简约而隽永的辩证法,这几乎可作为你所有写作的一个触点;你是否自觉掌握了某种可靠的方法论呢?
玉 珍:不知道,那可能是不自知的,你讲的简约隽永的辩证法特别好,这两句原本确实被我安在某首诗里面,但后来又被拎出来了。我常常思考悖论的东西,越思考越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它是灰的,悖论就是这样,自相矛盾但相互成立,当你理解了悖论和复杂性,很多问题就从绝望转向了释然,死亡和活着是这样,梦与醒也是,那天我们讲到瞬移,你谈到一个词……
师 飞:跃迁。
玉 珍:对!也是这个意思,都是辩证。我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没有什么目标,我脑袋里有个模糊的宇宙,不清晰,因为内容太多了,我没力气给他们整明白,我对自己看得不够清楚,对别人也一样;我只有一个模糊的远景和某种确定的信念,但这信念也没法很快显现为语言,那是我将来要走的漫长路。我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只能在黑暗中坐着,将生活和思想从那种混沌中解救出来,大多时候我是糊涂的,一部分时候我又极其清醒明白。
死亡是一个想象的深渊,
巨大的容纳器
师 飞:整体来看,在你的写作中,标题似乎并不处于一个显赫或者是必要的位置。
玉 珍:我不擅长取标题,我很多年前就想给自己取个笔名,快10年过去了,也没能取出来。
师 飞:你这么说我还挺意外的;我一直以为,无论你怎么运用笔触,总是有一个内在而强大的“我”在节制这一切,也许是因为某种自觉,也许出于某种野心;总之,不是你说的“不擅长”,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某种写作上的任意性,或是无计划无目的。
玉 珍:不全是无计划无目的,就比如那两句或别的某些我觉得好的诗,是我非常想要想明白一个问题而蹦出来的,我只有那个过程的野心,我对自己非常苛刻,理性是必然的,苛刻就是理性。不存在完全随便挥手就来的好东西,它一定有过先验,我的野心在我写之前,但有时候太倚重自己的心情,凭借感觉,贪玩,无所谓,不确定任务或目标,这是不怎么有野心的地方。
师 飞:当然,要相信感觉,但也要意识到感觉需要经受理智的无尽锤炼。我发现你所有的写作都可被理解为一种系列主题式的表达,所有的写作都倾向于集束为某些主题,无论它是梦还是死亡。关于梦和死亡,能再谈谈吗?
玉 珍:我有主题吗?谢谢你的发现,我自己总是不了解自己,可能下意识造成了这个局面。我常常做梦,如果醒来和睡着是躯体与意识在生命中的交班,我觉得两者从没有一起休息的时刻。我的有些梦弥补了我血肉之躯的局限,它甚至在部分梦境中替我面对和思考了现实中的问题;梦是野性的,野心勃勃、充满意外。
至于死亡,跟梦差不多;它们对于我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神秘。死亡是个压轴节目,在这个看似晦暗的词语上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我想我们所有的创作不过是在它发生之前的记录总和,谈论死亡似乎意味着谈论一切。
师 飞:你关于死亡的这个论述太精辟了。史蒂文斯曾说,“死亡是美的母亲”;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死亡都像一件终极的容器,一件绝对悲伤的容器,等待着被填充;像一种悲凉的风格等待被欢乐的主题填充。对于很多直接处理死亡经验的诗人而言,死亡作为一种素材被使用,但你并不直接处理死亡,你似乎是受惑于死亡并信赖它,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必要的背景。对于你而言,死亡是构成美的必要前提吗?
玉 珍:可能没有特别必要,它就是习惯,死亡是一种压轴,我对它充满好奇,它是个想象的深渊,一个巨大的容纳器。它总会冷不丁出现;它不是个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氛围,一顶黑色帐篷;或丛林深处层叠幽绿的茂密树林,人在其中容易感受到隐秘力量的存在,有些来自外界,有些来自自己。
我相信轻盈,
轻盈是一种很好的力量
师 飞: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诗中总是潜伏着一种雄辩的主体性力量;譬如,当你写“马是善良的/它谦逊到完全不需要赞美”“只有伟大的美可以改变浪费”这样极具论断意味的句子时,你一定对它们所散发的命名威力了然于心;这能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上帝视角,而在此一视角之下遣词造句确实具备一种从本体上赋义的力量,而事物也会因为被书写而重新存在,你对此有过省察或者迟疑吗?
玉 珍:有,诗意其实与论断之类的东西是不太相融的,就像有人认为过于雄辩有削其美,但其实我热爱雄辩的力量,虽然任何诗人都可以随意命名任何事物,这是语言天生具有的魅力和弹性;但其实也是有度的,诗意的决断最终要尊重的还是“诗”和“意”。我惟一迟疑的是,我的决断除了让事物与美更具有威力之外能否更有意义,而不只是无知地挥霍词语。
师 飞:你的表达策略中偶尔也有一些口语性,但整体依然保持了某种内敛与节制,似乎是在维护一种书面语式的典雅。一般而言,书面语似乎不像口语那般,在表达上容易摊开、轻纵。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一语言特点,或者,你有没有对自身语感的不满足呢?
玉 珍:有,不满与不足都会有,还有更高的要求,但没考虑过我的语言特点,我只管写,我的众多诗里面好像有几种口吻,很杂,这个感觉会变的,我反对任何一种盲目自信,但信念必须有。在某首诗的某个瞬间,我觉得它是完美的,恰当的,但我很快又会对自己产生新的要求。麻木,视觉疲劳,突破,新意,改变,这意味着我不会有完全的语感上的满足。
师 飞:你的语言处处显露出受惠于西方精神养料的痕迹,在观念上始终追逐着一种重而不是轻,一种拯救而不是逍遥,甚至连俏皮的余地都不容留;你似乎不信任轻盈的力量?
玉 珍:哈哈,有吗?你这么说我得审视自己了,你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我呈现给你的就是这样,然后你诚实地告诉了我,我看我自己的作品是一张完全东方式的脸,其实我写了很多非常清新轻盈日常的诗歌,但没拿出来,这一年多我都在写散文随笔,那里面容得下更多的轻盈与日常;我必须从中找到某种不同,否则就没成就感。但我更要找到新的突破和稳健的质感。我相信轻盈,轻盈是一种很好的力量,另外,我觉得我的生活会非常简单、轻盈、平静,我能较大程度地把握这个,我不会失去它,而思考不一样,它需要记录、坚持,否则会生锈、迟钝、忘记、愚昧。
关于你所说的重和轻、还有拯救和逍遥的问题,非常神秘,早上我看着这个问题觉得特别熟悉,好像这情形曾经发生过,事实上没有人这样问过我,但完全就像经历过,仿佛过去的时间重新来到我身边。如果现在你遭遇苦难和困境,有三个神站在你面前,他们分别要你反抗、适当妥协、放下,你选择什么?我经常听到什么“平常心”“放下”“忘记”“不争不斗”,诸如此类的话,仿佛地狱是没必要去的,忘记就是天堂;它对应斗士和隐士,对抗和奴役,拯救和逍遥;这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性格态度,但核心又朝着同一个方向,即走向某种解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个人认为自我拯救大于逍遥,反抗永远要放在放下之前,因为没有一种绝对从天而降的造化为你提供逍遥的生存,逍遥是一种境界,现在整个时代的信仰宗教都被破坏了,人仍然要去尝试,你所说的拯救也许是基于我创作中的苦味;从表达方式和语言完成度来讲,我通过表达拯救而追求逍遥,别人可能借助逍遥抵达拯救。
师 飞:说到拯救与逍遥,我们从小受到的规训就是恐惧、逃避——甚至否认——灵性生活(无论它是何种意义上的);从宗教的意义上而言,我们的生活都是枯瘪滞涩的、黯然失色的。本雅明曾在论艺术作品的时候提出过“Aura”(中文译作“灵晕”)这个概念,我在想,不只艺术,人也是这样;有些人生动有趣,有些人僵硬刻板;你会时常自省自己是否有生气、有灵性吗?
玉 珍:问得好,人人都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常常自省这个问题,我不会允许自己脱离必要的生气灵气而存在,我在前面某个问题后说了没有天生逍遥的环境也没有绝对的拯救,神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一切靠自己。诗与“灵”都是理想,我们得怎么生存?我们的“人性”和“灵性”是否在溃散?有些人身上只有性没有人或灵,是只有欲望的行尸走肉,甚至将欲望等同于“人”与灵。生气灵气不在于是否轻趣和灵动,沉重有力痛苦庄严也是一种气,它未必用轻盈来展现,关键在于“灵”的表达,魂与灵是否正常,心灵是否健康,内在的东西是否坚守住了。
写人类就是写人,写人就是人类
师 飞:似乎,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宗教信仰都得承受一种生活,被我们领承的这个世界(时代)本来就是祛魅了的、被理性分割宰制的、受制于因果序列的。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终极解脱这回事儿。也许有,但它只可能是一条个人化的道路,一个人要想获得自身的意义认可就必须进入那道属于自己的“窄门”。你相信“诗”就是你的“窄门”吗?
玉 珍:嗯,不穿过窄门哪儿也去不了。
师 飞:你的诗中几乎完美地回避了对性别、身份这类时尚标签的攀附,尽管如此,依然包含着一个女性的独特经验和由它载负的人类性。我还想追问一句,就具体写作中的想象和期待而言,个体的人和人类,哪一个能对你形成持续的诱惑?
玉 珍:这可能又是我某种写作习惯而造成的局面与局限,我没有刻意回避,我不避开什么,什么都能写,但我的习惯性就那样,我像个中性人,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做母亲,但一切都会改变,我的创作还很漫长。后面那个,你问的是人和人类哪个更具有创作诱惑吗?哈哈,人类吧。我先大后小,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都一样,写人类就是写人,写人就是人类。
师 飞:其实,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人类。类似地,也可以申言:一首伟大的诗中孕育着所有的诗,一个诗人就是能从一首诗中发现并赞同所有诗的人。你遇见那首“伟大的诗”了吗?
玉 珍:不知道。未来可能会知道,有些东西和感觉不会立马显现。有过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不是语言。
师 飞:说到未来,有生之年,你对艺术或科技方面有什么期待或者想象?
玉 珍:我希望能有记录梦境的东西,哪怕展现部分图画,声音,我都很向往;我有很多对未来的好奇,至于艺术,内心的东西,这大概是我能用自己的力量和信念去做到的事情,艺术不是非要去做艺术家,就是追求和去做喜欢的事情吧,我希望在精神上更富足,自由。你呢?
师 飞:我大概从心里还是不太信任技术;我并非一个保守派,但就事实而言,技术能保证的只是效率,而不是意义,在技术面前,生命倒像个赝品。话说回来,与其期待艺术或者科技,还不如期待一种更好的生活;你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吗?
玉 珍:我想无灾无祸过一生。我把精神与人的意志看得很高,他们是科技的对手,也是科技的灵魂。艺术与科技都曾使我惊叹,也使我感到善变无常,科技的疯狂突然将人挤压到充满噪与快的孤独角落,而艺术也总是孤独的,惟有朴素的生活真切有情,人必须用内心去战胜与适应,这是恒常的力量,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愿望非常简单,希望健康,平安,自己安排人生,希望爱我的人也一样。然后再去谈理想,我很感激某些伟大艺术给我的营养,那些了不起的电影,文本,它们让我醍醐灌顶。我希望自己创作出那样的作品,这是个梦,我喜欢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