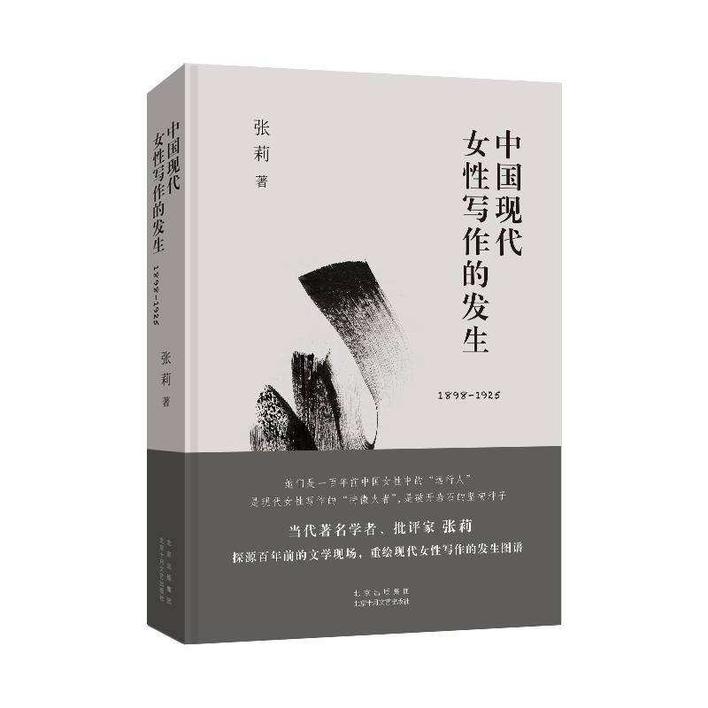张莉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全面梳理和考察“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之本事。对起源的探讨总是以“发生学”的美名,以无穷的魅力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要是没有西方文化的‘压迫’,中国的文人才不会提什么女性问题”,但张莉在绪言中开宗明义,本研究“不是时下女性文学研究中通用的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作者立意于关注“中国环境”,梳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以及写作史。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基础上提出“女学生文学”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关注到“女学生”这一之前并未引起多少注意的群体,捕捉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一群体起源的考察,作者成功抵达了现代女性写作的起点。尽管王富仁认为张莉观察的女学生群体所在的学校教育空间中,“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男女两性的关系不是在家庭经济关系和国家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显然这一空间并没有王富仁所勾画的那样成为理想的飞地,张莉依然在多重维度上论述了历史、国族、家庭、社会等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甚至可以说,“女学生”所在的教育空间只是这些维度交错运行生发作用的原因与结果,当然,也是这一空间直接孕育了现代女性写作。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支撑自己的叙述逻辑,并纠正了以往现代历史上对女性解放的诸多误解。如以往认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也都是以民族问题为前提,张莉认为要区分1898—1918和1918—1925等不同时期妇女解放的不同内涵,即晚清民初的“强国强种,贤妻良母”式妇女解放与进入“五四”时间之后作为“人”的妇女解放。正是在这种不同时期解放性质的重大区别中第一代女性作家成长起来。也正如“妇女解放:一个问题的两种看法”一节所梳理的金一与何震的巨大观念差异,也是在“主流”与“偏离主流”的观念博弈中,真正意义上的、男性话语之外的、功利性能之外的、作为单独个体存在的女性及女性话语受到了文坛与社会的注意,陈衡哲、冰心、凌淑华、庐隐、冯沅君等作家才走出家门,走进校门,进而走上文坛。张莉在这样的意义上建构起个人的学术框架与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了这一代女作家的风格特征与时代意义,填补了理论之外的材料空白,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寻找到了真实而具体的起点,开启了更为宏大艰难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学术讨论。
这部著作直面了性别研究永恒的难题,即“女作家”何以成为问题?更普遍地讲,“女性”何以成为问题?作者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有对当时批评家观念的总结,“因为女子的内心生活和社会生活究竟和男子不同;她们所描写的对象,每为男子所难想象到。所以,她们的生活实在可以代表另一种为男子十分隔阂的生活”,也给出了自己对女性写作价值的评价,“她们对于语言形式的探索”,“对‘问题小说’写作的开拓性工作”,“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但显然,前者依然是“男子”话语权之下的表态,而后者则停留在单纯的文学技术层面,甚至是男性作家也可以做得到的贡献。这里当然不是质疑张莉对女性写作发生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是要进一步追问,当起源与发生的难题都得以梳理和解决的时候,该如何为问题本身寻找到正义性?张莉在书中也给出了“社会性别”的视角,试图进入历史情境,采取“共时”的讲述,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以此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显然有利于性别关系研究的深入和性别平等的推进,但“女性”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意义依然没有凸显。
即便是有意回避西方的性别研究理论,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和性别问题的世界背景。如果说是西方文化的压迫促使我们“发现女性”,那么也必须承认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对中国现代的“入侵”,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学”也正是“现代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女性”乃至“女性写作”的关注是西方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主动选择,没有“妇女”的发现,就没有现代社会要求的基本的平等、文明、和谐。换句话说,“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本身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完整”“发生”。“发生”由此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能指,“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成为这一能指立足落脚的具体所在。
张莉所研究的“冰心女士”的接受史恰好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另一种现实解释。冰心和同时期的作家们相比,在读者和批评家那里更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冰心的创作理念中既有传统的对女性身份的认知和审美,如对贤妻良母的颂扬,也具有现代的反抗和进步因素,如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这使得冰心的创作历程更像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的结合,这种并不极端激烈的立场似乎更适合一切悬而未决的现代中国时代的读者们。冰心有着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人文关怀,却也始终携带着性别偏颇的传统阴影,这可能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时期的典型问题,或者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典型问题。女性写作本身正如冰心的创作立场,有可以完整“现代”的素质,却也沾染某种暧昧,这种暧昧包括自身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也包括其在不同时间受到的阐释与质疑,更包括其本身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损。然而,这种暧昧恰恰也是“现代”“发生”的标志与产物。“女性写作的发生”正是荒烟蔓草的时代里挣扎求存的人们对石头和木头的使用,文学参与者们由此“完整”了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而中国文学也“完整”了自身的“现代”属性。规避了西方时髦理论,立足本土本事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