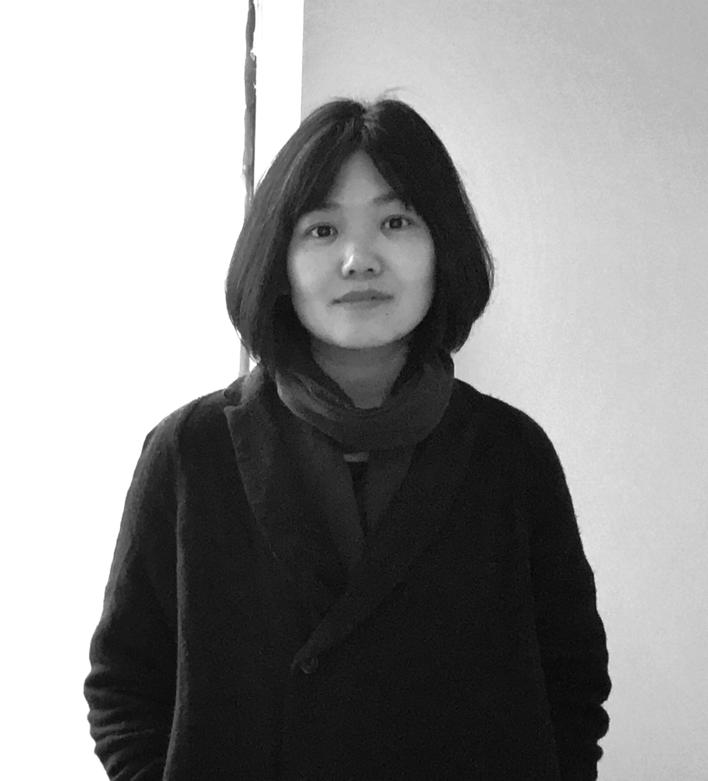很多个冬天的黄昏,她坐在房间里等待雪的来临,等待那个关闭已久的世界重新开启。仙乐飘飘,大雪纷飞。雪落在道路、树木和屋顶上,将山林染白,将田野变成白茫茫的雪地,让人欢喜、震惊。
通常在第一朵雪花羞羞答答地飘落之前,她的回忆便开始了,并纷纷扬扬地铺展开,不可收束。
那是一个雪后的早晨,阳光透过树枝照射在积雪的路面上,被许多脚印所踩踏的黑色柏油路显得泥泞而湿滑。九岁的她终于穿上那双觊觎已久的红靴子,细腻、光滑的猪皮,里面附有稀疏的毛绒物及虫蛀的痕迹——它们来自她时髦的舅妈,在母亲的鞋柜里一躺就是好多年。相比她的脚,它们实在太大了。在父亲的搀扶下,她晃晃悠悠地行走在雪地上,像醉酒的人踩着高跷。她感到莫名的快乐,又有些许担忧。积雪的路面上随处可见四仰八叉的人,蹦跳的孩童走着走着便摔倒了,颤颤巍巍的老人自己将自己绊倒在雪地里。但父亲在她不会摔跤,父亲的手温暖而干燥,紧紧抓住她的手。那天早晨,他们走过一些高耸而湿滑的台阶才来到雪地里。——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他们为何要走出温暖的屋子,母亲怎么会同意他们出门。她只记得雪后的世界变得无比亮堂,房屋的顶上全是白鳞鳞的积雪,树枝上挂着串串雪,道路两侧是硬而发黑的脏的雪,被冻成冰渣子的雪。路的那头,男人们站在雪地里大声说笑着,眼前浮现出一小团一小团的哈气。或许,父亲就是被这些人的笑声所吸引。平日里,他们都是父亲的牌友。下雪了,天寒地冻,与世隔绝,更有理由组织一场昏天黑地的牌局。
关于那个遥远的雪后早晨,除了布满灰黑色冰渣的路面,红色高跟靴带来的蹒跚感以及父亲宽厚温暖的手掌……更多细节,她已经无法回想。但雪带来的兴奋感一直埋藏在她体内。它们太强烈了。雪对事物的侵占是彻底的,全方位的,毫无商量的余地。视域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面对如此场景,她总是忍不住想要大喊大叫,对着漆黑的夜晚,对着茫茫雪原、朗朗晴空。
很多年后,她还能回想起冬天里第一朵雪花从浩瀚无垠的苍穹飘落,心底涌现的感觉。好像期盼了许久的事物终于到来了。雪后屋檐下滴滴答答的化雪声,刺亮的雪光反射到屋里墙壁上,留下不规则形状的跳跃的光斑。清冽而彻骨的冷。她搓着手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听雪从树枝上簌簌抖落的声响,冰块在沟渠里一点点融化,感到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个雪后的清晨,她的屋子里来了一群人,他们将她带到邻村的墓园里。一个早逝的朋友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雪让死亡变得遥远,好像那是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他们在墓园里谈论各种计划,计划之一便是未来某天要把死者置身的地方装扮一新,把荒凉的坟地改造成豪华墓园,要有石狮、石凳、汉白玉碑石,还要松柏常青,花开不败。他们想让人记住死者,记住一个年轻而过早凋谢的生命。他们还蹲在雪地里拍照,相片洗出后,曝光过度的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雪光映照下的身体也显得臃肿不堪。那时候的少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衣物,他们的衬衫、外套、鞋子、围巾都是他人替换下来的。它们式样老旧、面目模糊,不是过分宽大,就是窄小而局促,把人箍得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找到独属于自己的状态,一切行为不过是模仿,连雪地墓园里的踏访也可归为此类。
很多年过去,墓园里的一幕被渐渐淡忘,她经常想起的只是那些人如何在雪地里艰难跋涉,一路问询,最终找到她的家。幸运的是雪把破败的屋舍完美地掩盖住了,所有丑陋的、污水横溢的地方都被完好地遮掩起来。他们来到她的屋子外面看到的只是雪,洁白的、遮挡一切的雪。这也是她这么多年热爱雪的原因。她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平常的气候里来到那里,向她招手,喊她的名字。她不能让人看见自己住在一个破旧的地方。她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住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后来,一些离家出走的人成了她的朋友。他们不仅有相似的遭遇,似乎还存在着某种共同语言。下雪了,他们来到异乡的雪地里,想着在那上面留下痕迹,就像许多年前在自己家乡所做的。无论在哪里雪都是不一样的,它们是崭新的寒冷,留给寒冷一个完美的理由。
飘逸的雪花既无法被瞬时融化,便一点点堆积起来。视野所及处都是雪,不断积压的雪,各种形态的雪,层叠不化的雪。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消失了。过去和未来的界线也不复存在。在雪地里,只有今天、现在和此刻。人们走出屋子,找到那些雪,又看着它们在眼皮子底下慢慢融化,彻底消失。
她的几个舅舅都是在下雪天结的婚,好像这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让雪花飘荡在婚礼现场给新人送去别样的祝福。她终究没有询问母亲,她与父亲结婚时是否也下雪,这涉及到生命源头的问题,让她难以启齿。她只在童年有幸参加过小舅的婚礼,鞭炮炸出的红泥溅落在皑皑白雪上,煞是触目。在没有冰箱、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食物的保鲜,人们会选择在冷天里举办宴席。食物烹煮时散发出的浓郁香气,给人无限遐想。人和动物都饥肠辘辘,胃口大开。
她见证了那一幕:穿红嫁衣的新娘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伴娘们为躲避鞭炮追逐奔跑在陌生的村街上,而雪花在她们头顶飞舞。面对此种场景,男人们乐得拍手大笑,好像这是无上荣耀,是婚礼带给新娘和伴娘的荣耀,也是雪带来的。
从那时候起,她就对一个女子出嫁路上遇见的一切感到恐惧。那个世界无所逃遁,鞭炮声能把人的耳朵震聋,把好端端的身体炸成碎片,而雪地又那么冷,雪的世界无处可藏。
秋去冬来、寒冷骤然降临的日子,她的身体在感到冷意袭来的同时,也会想起至今仍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亲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冬天离他们更近一些,雪花随时可能飘落在他们头顶。她总固执地感到自己来自一个寒冷的、有许多雪、屋檐下悬垂着冰柱的地方;当世界变冷的时候,她担心的永远是家里那边的人。这种噬骨蚀心般的担忧不会随时间流逝而终止,好似她的身体里藏着一条隐匿的通道,时刻向着过去狂奔。
一个下雪的日子,有人从老家给她打来电话。那个人路过她的村子,被人指点着知道了她从前居住的地方。有两间房子,一间在河的西面,另一间在河的东面。有两棵树,一棵是栗子树,还有一棵是橘树——它们都是她过世的祖父种下的。她父亲早逝。祠堂的石碑上刻着兄长的名字。屋宅的门楣上还留着儿时的涂鸦。那个地方的人都认识她,熟悉她的一切,哪怕她早已离开。
打电话的人好像站在一块高高的坡地上,他居高临下,诉说一切,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事情一目了然。她日夜担忧的人早已不在那里了,祖父走了,祖母死在一个温暖的冬天。房子里堆积着满满当当、面目模糊的旧物,散发出无人使用的气味。母亲的嫁妆也放在二楼卧房里,她带回一只画着梅花和兰草图案的箱子,当作书箱使用。箱子底部有明显磨损痕迹,箱体散布着隐约的蛀孔,她在上面搁置花瓶、咖啡杯、绿植和石膏头像,也让新的阳光和尘灰嵌入物体暗旧的表面。
那个屋里发生的一切还在她脑海里回荡,并永远回荡下去。所有寒冷的日子都留在那里,民间故事里的鬼怪精灵也留在那布满孔隙的板壁里,连同里面仍然活跃的虫蚁一家——而房屋产权的最初拥有者以及故事的讲述者早已长眠地下多年。她长满冻疮的手指,冻得像胡萝卜一般的手指,还在梦里拿取那个屋里的东西;它们小心翼翼地抚过尘灰密布的瓶瓶罐罐的表面,童年的美食正躺在陶瓮的底部,散发出甜烂、温暖的气息。它们是柿子晒成柿饼之后所漫溢出的气息,也是雪后灶膛里被炭火煨熟的红薯气息。
冬天的房间里,她闻到了雪的气味,火焰的气味,回忆的气味……不可抑制地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植物根茎部的甜味,那种与呼吸和梦境建立起隐秘联系的味道,此刻无论怎么品咂和感知都无法被确切地捕捉到。这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雪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