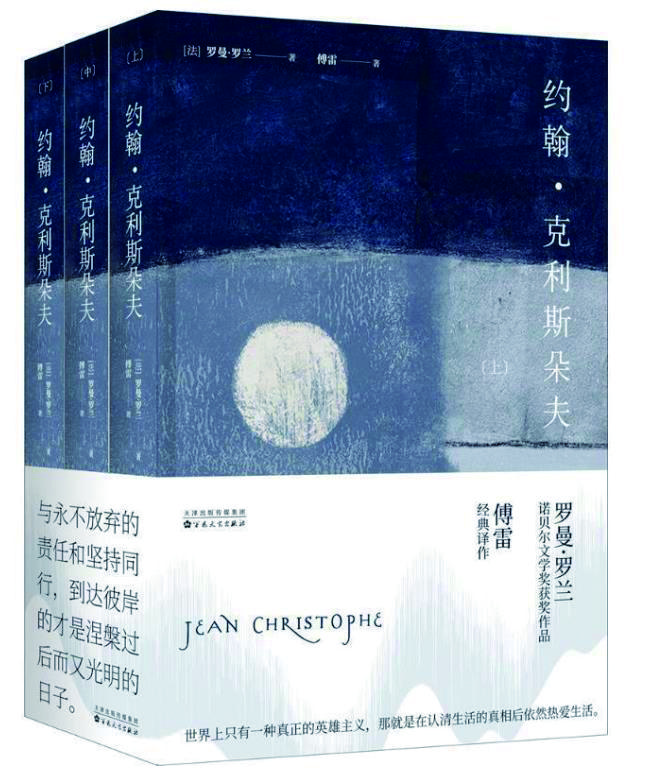尽管家境优渥,生活安逸,罗曼·罗兰的童年仍然笼罩在历史和个人双重命运的阴影之下。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失利,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对普鲁士的巨额赔款更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国内政局动荡,君主制被废除,先有巴黎公社革命,后有保守派、共和派、保皇派等政治派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而生命给他最初的极致体验是“窒息”,他此后的一生都深受其苦:“一个粗心的女仆,少不更世,大冬天把我一个人撇在室外,当时我还不满一周岁,差点冻死。从此落下了哮喘的毛病,呼吸急促。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样不自觉却频繁出现的表述:——窒息——打开的窗——英雄的气息……鸟儿或振翅翱翔,或病恹恹地蜷在窝里,捧着受伤的胸膛”。羸弱的身体不断受到病痛的侵扰:伤风、支气管炎、咽喉疼、止不住的鼻血。他感到自己身处“鼠笼”,“我是一个囚徒”,古老的房屋、胸闷和死亡带来的凶兆仿佛是他的三重监狱。他本能地找寻逃离的路线,在花园里,把自己想象成一朵在天空来去自由的云。
是音乐和文学给了小罗兰翅膀,先是贝多芬和莎士比亚,再后来是斯宾诺莎、瓦格纳和托尔斯泰,让他看到“漫长而昏暗的岁月中闪闪发光的艺术”和“真诚的信仰”,给予他迎战风暴、雷霆和布满暗礁的人生的勇气。1887年,在圣灵降临节的晚上,罗兰第一次给托尔斯泰——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和真理化身——写了信。那年夏天回家度假,他又在克拉姆西的老房子里写了第二封信,继续向大师倾诉自己内心的惶惑不安。
1887年10月14日,托尔斯泰用法语给这位住在巴黎穷街陋巷的无名小卒写来了复信,一共38页。先是亲切地称呼他“亲爱的兄弟”,说罗兰的信令他印象深刻,“我收到了你的第一封来信,含着眼泪把它读完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接着,大师阐释了自己对艺术的见解。他说,艺术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把人类团结在一起。真正的艺术家是那些可以为信仰做出牺牲的人们,成为艺术家的先决条件不应该只是热爱艺术,而是要热爱人类。只有充满人类之爱的艺术家才有希望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一周后,罗兰在巴黎米什莱路13号的住所收到了这封回信。托尔斯泰的善良友好之举比他信中的言辞更让罗兰感激万分。
对罗兰而言,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历。从此,罗兰以托翁为崇高的榜样,“我从未忘记艺术对于人类的责任和职责。”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中这样写道,“从拆开托尔斯泰来信的那一天起,他自己就成了一名乐于助人的人,一个亲如手足的顾问。他的全部工作,他的人生魄力从这儿找到了起点。自那以后,无论时间如何紧迫,他都牢记着托尔斯泰的帮助,任何陌生人感到良心不安求他帮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托尔斯泰花了一两天时间给他不熟悉的投信人回了一封信;罗兰则发扬了这一精神,写了上千封信给上千个陌生的朋友。种子的力量是无限的,今天它正在向全世界传播。这是仁爱的种子呀!”《九人:罗兰·罗兰与中国留学生》的作者刘志侠花了几年时间踏遍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等地,在故纸堆里寻找几乎被时光湮灭的日记、书信、照片、印刷品等珍贵文献,梳爬整理,条分缕析,如实还原了罗兰与盛成、敬隐渔、梁宗岱、李又然等9位中国青年的交往细节,他给予中国留学生物质和精神上的无私帮助以及他们之间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托尔斯泰对罗兰另一维度的影响是创作上的,《战争与和平》给罗兰提供了“第一个也是无与伦比的新史诗的典范”,虽然他从未模仿托翁的风格,但这部巨著为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后来的一些创作带来了启发,“这些作品虽披着小说或是戏剧的外衣,但却有着史诗的本质”。从《圣路易》《理性的胜利》《群狼》《丹东》《七月十四》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找到了创作的主题,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塑造出理想的英雄、坚强的灵魂,把真实和虚构结合起来。
从那时起,罗兰把目光从法国移到了全欧洲、全世界。“世界才是我们的主题,因为一个国家太小了。”席勒和歌德是他的引路人,前者说:“我是以一名世界公民来写作的。很早我就把祖国换成了人类。”后者说:“现在民族文学的意义很小,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于是罗兰振臂疾呼:“让歌德的预言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吧!”慢慢地,罗兰成了人道主义的化身、欧洲的良心、世界公民,从默默无闻走向举世瞩目。
如果说罗兰年轻时代写的系列剧和革新法国舞台的尝试都失败了,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对自由的捍卫却随着写作和思考的深入变得愈加坚定。“我厌恶那些懦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愿意看人生的悲剧和灵魂的弱点。如果一个民族易于对骗人的高谈阔论陷入幻想,对于这样的民族,首先有必要向他们说明,怯懦的英雄主义是假冒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活,热爱生活。”这种英雄主义只承认一个评判标准,它不是祖国、不是胜利、也不是狭隘的正义,而是至高无上的良心。在大灾难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和罗兰站在同一阵营,都热爱和平,都认为欧洲人自相残杀的战争是罪大恶极,是对文明的亵渎。但当1914年8月2日,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很多和平主义者瞬间就转变为斗志昂扬、不惜流血牺牲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1914年9月22日,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他说:“伟大的国家不仅要保卫自己的疆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理智,保卫自己免受战争助长的幻觉、不义、愚行的侵害。做到人尽其责:军人保卫自己的国土,思想家保卫法兰西思想……精神绝不是民族遗产中可有可无的东西。”罗兰谴责战争暴力,因为战争是一种“兽性的崇拜”和理性的泯灭,他将发动战争的人类比喻成一个无知的孩童,“他对自己孱弱的小手将要引爆的炸弹没有概念。有时,点火刹那,炸毁的将是一切。”
罗兰孤身一人客居在日内瓦湖畔的维尔纳夫小镇整整5年,几乎站在整个民族的对立面,向褊狭的祖国观念、群体的盲目冲动宣战。在“爱国者”的眼中,罗兰是危害祖国、动摇军心的叛徒,他的“罪行”在于,他坚持一种公正的不流血的和平,一种全面的和解,一种全欧洲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不是用战争和强制得来的和平。湖畔小房间与他曾在巴黎的住所很像:一堆堆书籍、文稿、一张粗陋的松木桌、一架钢琴,这是他闲暇时的伙伴。不论白天黑夜,他都在这里工作;很少出去散步,也难得有客人来访,因为朋友们都惊避远走,和他划清了界线。即便是他的父母和妹妹,每年也只能越过边境一次来探望他。最难以忍受的是生活在某种“玻璃房”内——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隐私,孤独地生活。法国政府派遣特务密切监视罗兰的一举一动,他收到的每封信都被别人审阅过,电话上讲的每句话都被记录在案,每一次会客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但就从那时起,罗兰与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能够帮助整整一代人,因为“他从孤云野鹤的高度,向世人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依靠忠于自己认定的真理的思想,而使这种思想永世不朽”。他的影响向四处散发,全世界都热切地希望听到他在孤独中发出的呐喊。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的最后一页,罗兰讲了圣徒传中的一则故事,化身孩子的耶稣深夜叫醒巨人圣克里斯托弗(圣基多福),请他扛自己过河。巨人欣然应允,开始觉得柔弱的孩子很轻,但当他越向前走,男孩就越重,压得他几乎也要沉到河底。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地嘲弄他,笑他。随后,黑夜来了。他们厌倦了”。他奋力前进,黎明时分终于到达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和故事中的巨人一样,罗兰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发现自己扛着整个一代人的命运、整个世界的意义和爱的信息在渡河,茫茫黑夜,无人赏识,无人帮助,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身后的河岸上传来怀疑、污蔑和嘲笑的声音,而他奋力向前,顶着逆流,不屈不挠,长达10年之久,奔赴未知的彼岸。罗兰渡过了河,他的作品和精神也帮助世界上一代代在困顿中寻找出路的人渡过了他们各自人生的黑夜和逆流。
1919年6月26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前夕,罗兰在他自己创办的刊物《人类》上发表了“思想独立宣言”,呼吁把“思想从各种拖累中解放出来,从无价值的联盟中解放出来,从掩饰了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盲目的争斗之上,要竖起一个“自由、团结又形式多样、永恒的思想”。他和甘地、泰戈尔、高尔基等人通信,和前辈相比,罗兰“有着更自觉的东方意识,更开放的视界,更远大的世界文化理想,他不满足于‘欧洲人’这个称谓,不相信欧洲文化高人一等的神话”。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标志欧洲衰败的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自救乏术已显而易见。它需要亚洲的思想,犹如当初亚洲吸收、利用欧洲思想一样。两者就如人脑的两半,一边瘫痪了,身体机能就退化了。必须致力于重建东西方的和谐和彼此健康的发展”。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世界公民,欧洲应该“同古老而在恢复青春的亚洲文明的代表——印度和中国携起手来,要组成一个具有共同精神宝藏的大同的人类社会”。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的景象:“上面枝桠相错,下面根须相连。通过精英和民众,输血得以完成。”这也是他早在1916年的日记里就已写下,且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是属于人类的,我是人,我要到处去寻求人的祖国。”一个没有阶级、人种、民族、国家之分,人人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姐妹的和平团结的“人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