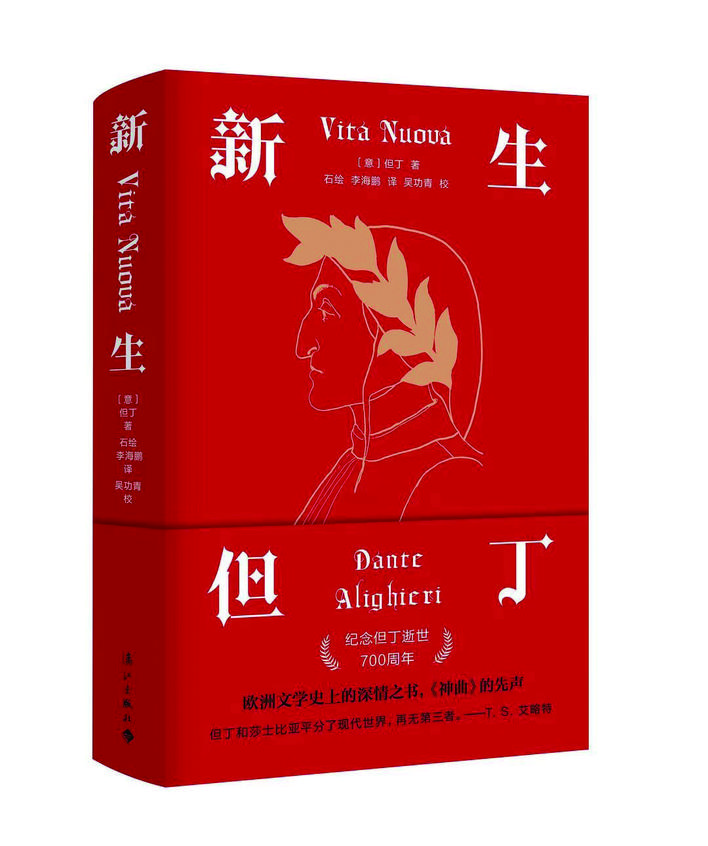《新生》(Vita Nuova)是但丁早年抒情诗的一本结集,完成于他30岁以前,也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后世的但丁研究中,这部早年诗集同但丁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飨宴》(Il Convivio)《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等作品一起被称为但丁的“次要著作”(opere minori)。当然,“主要著作”无疑是指伟大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尽管是“次要作品”,尽管“缺乏《神曲》的伟大力量”,但《新生》的地位还是十分特别的,诚如T.S.艾略特所说:“但丁所有的次要作品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但丁的作品;但是《新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神曲》。”艾略特甚至认为人们对《新生》的阅读应该排在读罢《神曲》以后,因为在他看来,“我们首次读它时,最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神曲》,而不是为了它本身”。《神曲》构成了阅读《新生》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将《新生》视为《神曲》的先声。事实上,二者的这种关系在很多意义上都能够成立。
抛开与《神曲》的关联看,《新生》在西方诗歌谱系中间,依然具有其主体性的价值与位置。文艺复兴研究的先驱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对此进行过较早的辨认与锚定:“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而他(指但丁)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主观的感受在这里有其充分客观的真实和伟大……即使没有《神曲》,但丁也会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篇划出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的界限。人类精神在向意识到它自己的内在生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布克哈特所言突出了《新生》中的“主观感受”与现代世界的融通,尽管但丁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的探索内在于他中世纪的虔诚。需要注意的是,但丁在《新生》中实现的“主观”,并非但丁一人独享,而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温柔新体派”(dolce stil nuovo)诗人们共同的诗歌主张,正是这样的诗歌主张,使得但丁等诗人与此前的普罗旺斯抒情诗及西西里诗派之间拉开了本质性的距离。这一点,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的第24歌中曾对贪食者波拿君塔(也是西西里诗派的代表)谦逊地坦承过:“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爱神给予我灵感时,我就记下来,并且依照他口授给我心中的方式写出来。”诗人与爱神之间“口授”的关系,正是但丁等新体诗人与旧体诗人之间最核心的差异,诚如波拿君塔听罢但丁之言所承认的那样:“我明白你们的笔紧紧追随着口授者,我们的笔的确不这样做。”与旧体诗人们书写爱情时因袭格套与侧重肉欲官能的方式不同,但丁们的笔“紧紧追随”爱神这一“口授者”。借助“爱神”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是新体诗人们将自身对爱情的主观感受人格化、客体化,正因如此,对“口授者”的追随,非但不是取消诗人的主观,反而恰好是主观的显现与传达。此外,“口授”的方式还意味着,相比于旧体诗人们侧重肉欲的方式,新体诗人们具有将爱情提升为精神性、思辨性范畴的崭新能力,这恰是“温柔新体派”的新之所在。在此之上,但丁则更进一步发展出了将爱情提升至宗教性高度的能力,其结果与证明,便是在《神曲》后面,贝阿特丽彩接引但丁升上天堂的情节。事实上,在《新生》时期,但丁便已埋下了伏笔、唱出了先声,只是当时的诗人自己也还没清晰意识到。在第一首组歌(canzone)中,诗人借助爱神的“口授”,写出了对贝阿特丽彩的爱恋,其中便暗藏了天堂的宗教性萌芽:
爱神称颂:“为何俗世肉身,生于
泥土,能够如此纯洁,如此美丽?”
祂又看了一眼,并对自己暗暗宣誓
是上帝借这形体谋划着尘世的新生。
她的肤色皎白如珍珠,匹配这美女
足够光彩照人,又刚好纷缊合宜;
她是造物之手能成就的最高形式,
照此标准,世上诸美为自己命名;
她的秋波顾盼,无论朝何处移动,
爱神的魂灵都熊熊燃烧如烈焰,
刺穿所有不禁凝眸注视者的眼,
并且蔓延,直抵每颗深邃的心宫:
她的脸庞浮现爱神栩栩的影像,
无人敢将目光在此放置得太久长。
爱神的“称颂”,正是诗人内心主观之所想;而“上帝”的谋划,暗示了在但丁这里,贝阿特丽彩是上帝之女,是一个圣迹(miracle),而非单纯的“俗世肉身”。她在《新生》文本中的位置相当于耶稣基督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一样。有趣的是,当波拿君塔在炼狱中认出但丁并与其谈论新旧诗体之别时,他所吟唱的但丁诗句正是这首组歌的开头:“女郎们,拥有着爱的智慧”(Donne ch’avete intelletto d’amore)。如果说“口授”与主观更多地带有着私人性的色彩,那么宗教与“圣迹”则相对来说是一种公共性的意识。但丁在《神曲》中对贝阿特丽彩的书写无疑超越了世俗之爱、理性之爱的“口授”高度,抵达了宗教之爱,这是一种极具公共性(public)的情感状态与书写方式,相比于前者,它更加崇高、更加前所未有。在《新生》结尾处,但丁曾说:“异象中的所见使我下定决心在有能力以一种更崇高的风格咏唱这位圣洁女郎之前封笔缄口。为达目标,我必焚膏继晷,淬砺致臻,这一点她定然知晓。倘若那位化育万物者愿意垂赐我生命以更多年岁,我希望以其他任何女人未曾得享的方式吟写她。”这“前所未有”的方式正是但丁在《神曲》中完成的方式,因此笼统来讲,但丁在《新生》中并未完成他梦寐以求的公共性。不过,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新生》的第30首诗(也是倒数第二首)意味着但丁这种公共性追求的觉醒。在我看来,这首商籁(sonnet)极为优美,堪称《新生》中最上乘的作品之一,布克哈特也曾表示这首诗是“这些诗篇中最美丽的”:
呜呼,朝圣者们凝重地赶路,
或许思念着此地所无之物,
你们来自遥远的居民与恋土,
脸庞的形容已将这秘密泄露。
没有啜泣传来,当你们穿过
这座浸透了悲恸的城镇半途,
正如那幢幢人影却魂灵枯疏,
难道不懂得它的凄惨落魄?
若你们驻足休憩,愿意聆听,
我心中叹息的预言必成真相:
当身影离去,你们将泪洒城中。
这里痛失的是它至福的女郎;
既然这些词语能诉说她的远行,
就有力量让赶路人泪水汹涌。
来自远方的“朝圣者们”只是途经这里,贝阿特丽彩的死他们并不知晓,也并不了解诗人的悲伤。目睹这一情形,但丁猛然意识到,自己对贝阿特丽彩既有的神话学建构,“绝对只是一种私人性的神话学,对于别人来说则毫无意义”,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一时刻在《新生》中昭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诗人的诗歌抱负,不再局限于追随“口授者”而写出主观的爱情感受,而是要将爱情的范畴扩大,让它从私人性中超越出来,抵达公共性的境界。于是,在《新生》的最后一首诗中,诗人依然借助“朝圣者们”,表达了自己未来的诗歌理想,尽管此时的但丁还并无能力理解与实现:
就看见一个女郎,收获着光华,
也施予了光彩;这辉煌的焕发,
吸引朝圣者的魂灵凝神注视。
目睹这般光景,言辞朝我涌来,
我却无法领悟它微妙的奥义,
尽管是心灵,曾疼痛中开启此门。
但我知道这些言辞温柔如斯,
因为传来的声音总是贝阿特丽彩。
《新生》写到这里,诗人对贝阿特丽彩的书写期待,已不再是让“朝圣者们”无动于衷,而是要“吸引朝圣者的魂灵凝神注视”,此刻作为诗人一己感动之人,未来必须要获得恒久的、公共性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此时从“口授者”那里超越出来,要开启的则是一段以全部余生来完成的“朝圣”之旅,直至《神曲》全部完成。若以后世的眼光看,没人会质疑但丁这一抱负的完美实现。一个有力的例证是,600年后,深受但丁影响的爱尔兰大诗人叶芝在写给毛特·岗的传世情诗《当你老了》中也使用了“朝圣者的魂灵”语,这一表述中实际上就跳动着《新生》中这句诗的踪影。行文至此,我们得以印证本文开头的话:《新生》在很多意义上都堪称《神曲》的先声。“它虽非《神曲》必要成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本类型,然而但丁却以之囊括了所有的话语、耳语、抱怨、噪音。”也就是说,《新生》虽非但丁诗歌的最终完成,但却几乎预示了后来的一切。
艾略特说:“《神曲》把我们带入了中世纪形象所组成的世界、思想与信条所组成的世界,而《新生》则把我们直接投入中世纪的感性中去。”对于当代新诗来说,诗人们如何能够先以主观的方式精确、全面而有条理地收集当代的感性,继而在此基础上携带并超越“口授者”,最终躬身完成一个向真正的公共性攀升的“朝圣”之旅,以及这一思路是否可能,或许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由此而言,尽管《新生》已距今700多年了,但我们对它的阅读,也许并非一件全然过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