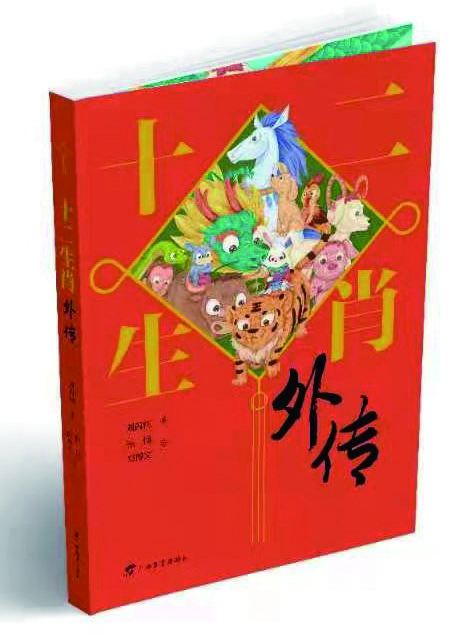童话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脱胎于远古神话和民间传说,汲取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养料,综合了先民的思维、文化、生活和历史,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千百年来在民间流播,是“原始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应该说,现今的童话创作,早已告别了早期的朴素面貌,即从传统的民间童话发展到作家个人自觉创作的“文人童话”,创作中有了浓厚的自我意识,体现了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也使童话这一文学形式具备了更为深广的表现空间和诗性意蕴。然而,文人童话的兴起,不应以民间童话的渐行渐远为代价。民间童话的魅力何在?千百年的流传和生生不息必有其根源,那就是,民间童话是对人类的基本愿望的诉求与满足。民间童话虽然以幻想为特点,但又与现实相勾连,以其荒诞、夸张,又简洁、朴实的形式,对理想的人生和人心底的诉求做出了最好的诠释。童话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更接近于“本质直观”。由此,民间童话虽然因其有限的角色和情节功能,在探求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深度上,不及“文人童话”,但其可知性、圆满性和“本质直观”认知世界的方式,又是只属于民间童话的特质与魅力。
作家刘丙钧的新作《十二生肖外传》就是一篇典型的民间童话架构。该书以子鼠篇《小老鼠好大胆》、丑牛篇《牛角挂书“牛很牛”》、寅虎篇《生来没有“王”字的豆豆虎》、卯兔篇《玉兔鬼精灵》、辰龙篇《大头鱼 大头龙》等12篇结构精巧的童话,依次为十二生肖作传;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十二生肖的形象又同时在各篇童话中出现,由此,将12篇童话连缀成了一个童话整体。作品中融入了诸多民间传说、成语典故、典籍故事,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风味,文笔简洁洗练、诗意唯美,略带幽默感,非常适宜儿童的文学启蒙和传统文化启蒙。
童话是可以与那个充满着诗性光辉和神秘色彩的远古时代联系起来的。光阴流逝,斗转星移,远古时代的神话渐渐褪色,但它们的光辉留在了童话、民间传说中,闪耀在人类的记忆深处。悲壮的宿命感时常呈现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之中,而童话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鉴证着世界与人的关系,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期望和理想。
比如,在子鼠篇《小老鼠好大胆》中,作家对《小老鼠上灯台》这首童谣和“老鼠嫁女”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全新的童话阐释:小老鼠好大胆为了给肠胃不好的弟弟“好软软”通便,大着胆子到寺庙去偷灯油;慷慨的“好大胆”和老猫先生交上了朋友;好大胆最喜欢的妹妹鼠小妹出嫁,老猫先生还当上了“保护神”。在辰龙篇《大头鱼 大头龙》中,善良的胖头鱼“大头鱼”为了躲避黄红鲤鱼的争斗,无意间越过高高的龙门,变成了一只能呼风唤雨、变化万千的神龙“大头龙”。显然,这个童话故事也是对民间传说“鲤鱼跃龙门”的化用。在这个单纯明丽的童话世界中,所有隐喻的、象征的真实,所有由幻想和想象生出的各种细节,都是原始思维对世界真实或美好愿望的反映。一个温馨甜美的“永无乡”,充满了奇妙的生物、瑰丽的幻想和甜蜜的结局。彼此之间充满感情,而且正邪对立、爱憎分明。勤劳、勇敢、善良、智慧永远是童话中褒扬的主题,邪恶、懒惰、懦弱一定会得到惩罚。民间童话虽然也会折射现实的矛盾,但所有的矛盾将在奇迹中得到圆满。
显然,民间童话的内核,就是不拘泥于现象真实,用内在的真实达到包容宇宙万物的宽度,用放弃表面真实来获得流光溢彩的魅力。那是先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原初经验。在那个时代,成人和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是用纯真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看待自然与生命,用整齐划一的“图式”,在其中呈现麦克斯·吕蒂所言的“缩小的宇宙”。
童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儿童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原始思维。原始先民认知世界的方式是直观、感性、具体、充满想象和联想的,而儿童也往往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和认知世界。在这样一个有情可感的世界里,老鼠可以和猫交朋友;生来个子小小的小老虎豆豆虎,因为乐于助人,补齐了额前的“王”字,成长为一只真正有力量的老虎;胖头鱼“大头鱼”因为善良,而无意间飞跃了龙门……弱小者必定会因为自我的善良与努力得到奖赏,得到成长,而邪恶一定会受到惩罚。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同构,不同于成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我向性”思维,即以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来认知和理解周围事物。儿童以主观的感受体验着这个世界,通过营造幻想来熟悉它,并在童话中战胜所有的生存困境。原始思维下产生的童话代表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变化和世界万物的统一,而儿童是这幻想世界中的“王”。
显然,民间童话承载的是人类集体的童年时期的幻梦、想象、思维和期盼。这里有着懵懂的对永生的期望、对死亡和被遗弃的恐惧、对阔大世界的认知、对自我的想象性的满足,这是童年思维最为深刻和真实的镜像。
童话是诗的典范,一切诗意的都必须是童话般的。童话中充满想象和梦幻的世界,正是突破现实世界的羁绊,从意识的表层世界进入到潜意识的深层世界,让读者体验无限与圆满。显然,作家也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其语言在简洁明快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唯美诗意的特质。
“高山的琴声一起,云不飘,鸟不飞,树静风止,观众们听得入神入迷;流水的琴弦一拨,鱼不游,虾不跳,水无波澜,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风伯抖开风袋,放出一阵寒风,推云童子推来浓浓厚厚的阴云,雪神手抚七弦琴,随着袅袅清音,雪花纷纷扬扬,飘飘而落,顷刻间,狗爷爷家的院落里一片洁白。”
类似的语句,体现出了作家丰厚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积蕴。
然而,与幻想小说中日常与幻境的“二元”叙事空间不同,传统童话就是“一元”的,现实与想象浑然一体,没有逻辑性的限制,也没有出入的“通道”。只有儿童那样纯净的心灵,才能感受这童话般的极致的美妙梦幻。诚如托尔金所言:“童话是一个独特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具有心理的真实性,一旦你不相信了,则魔咒破灭了。”
那么,长大后的你我,还持有童话的“信念”吗?也许,那些童真质朴,那些纯粹的欢乐和悲伤,那些急切的企盼和期许,或者还有绝妙的想象力和幻想力,都被成人们在脱掉“童年”外衣时也一同遗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