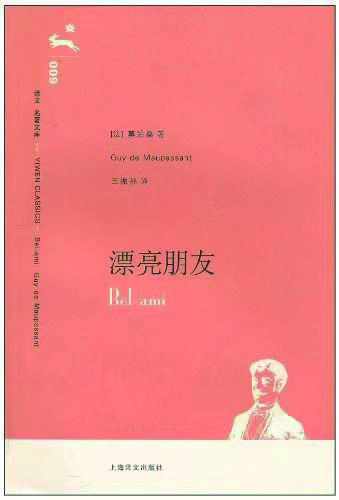很久没有想起莫泊桑了,忘记他,就像忘记一段曾经炽烈的旧情,无论当时怎样的神魂颠倒,如何的血脉偾张,但最终抵不过时间的耗蚀,在坚硬的现实与枯干的诗意面前,早已失却了那份情相牵、爱无眠的痴情。
过度的繁华
莫泊桑自己曾说过:“我像一颗流星进入文坛。”自谦吗?出自真心吗?大文豪想什么,谁能说得准?莫泊桑30岁时一举成名,在这之前的十多年写过诗歌、故事、短篇小说,甚至还写过蹩脚的剧本,但“这些东西一篇都没有留下”。究其原因,他最初的这些作品在福楼拜看来,缺乏“独创性”,弦外之音:是否立刻出版并不重要。年少轻狂的莫泊桑居然听从福楼拜的教诲,甘于寂寞直等到一声惊雷,写出千古流传的《羊脂球》。在他身上,沉默的成分是一种天赋,一切都是忍耐,一切都是等待,犹如悄无声息隐身于山水之间的彩虹,惟有等到光照、水雾,还有拿捏到位的角度来临的那一刻,它的绚丽才会翩然而现。
从成名到去世的短短十年间,莫泊桑发表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抒情游记,以及戏剧和评论文章。若不是天赐神力,从何而来如此可怕的笃定与坚持?有别于只为数量、在固定的套路下进行的取巧写作,从结果看,莫泊桑没有粗制滥造出一大堆“文学注水肉”,而是为世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再从接受美学来看,莫泊桑的艺术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巨匠法朗士赠以他“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这早已举世公认。就连契诃夫都把赞美莫泊桑当作“一件快活事”,认为自从莫泊桑凭自己的才华为创作定下那么高的要求以后,写作就变成了难事。
即便原来并不赞赏莫泊桑的屠格涅夫,后来读了《一家人》,也不得不承认:“看来他不是一颗一闪而灭的火星”,并将小说集《泰利埃公馆》推荐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读完之后立刻肯定了莫泊桑“天才的,真诚的,且有深入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认为莫泊桑是仅次于雨果的最优秀的作家。
福楼拜预言《羊脂球》将千古流传:结构、幽默和角度都出类拔萃——全篇构思浑然一体,独具一格,风格卓尔不群。景物和人物跃然纸上,心理描写很见功底,没有任何败笔!实际上,也就在《羊脂球》出版后不足一个月,福楼拜就过世了,若是泉下有知,当他看到莫泊桑后来创作的佳篇名作时,相信他依然会大加激赏,不吝溢美之词。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迄今为止,谁又能从莫泊桑的作品里找出一篇或一部平庸之作,可拿来诟病?
莫泊桑不是乔伊斯、爱默生、梭罗,诗人弗斯特那类属于“自我流放的漫游者”,也不是庄子、陶渊明式的看似出世超然实则逃避现实的逍遥派。如果说,那些自然中的“漫游者”疏离于家庭和整个社会环境,是为了自我飞越,或为孤独正名,那么莫泊桑最鲜明的特征则是疯狂地“介入”,竭尽全力地生活,生活,再生活,载浮载沉于社会现实的河流之中,无论是贴身底层,还是跻身上流,无论是纵情声色,还是勤奋创作,对于他寄身的社会之河,都在努力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审视和描绘。
有人说他是自然主义,有人说他是怀疑论者,有人说他是批判现实主义,其实他只是一个不倦的观察者,洞悉一切并述说一切。阅读他的小说,若不是浅尝辄止,若不是只图热闹,只要绕开那些戏剧性的情节,放慢阅读速度,便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被俯视”的感觉。他对普世的善恶的辨析,实在鞭辟入里,过犹不及,《圣经》中不一而足的罪性,譬如“邪恶、贪婪、恶毒、嫉妒、虚荣、无亲情、狂傲、诡诈、争竞、虚伪”,无不显露在一个个故事的细节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男人、妇女、老人、甚至孩子的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一个最极致的例子,《西蒙的爸爸》中一群乡下孩子在校园里欺凌没有爸爸的西蒙,和动物差不多残忍,就像“鸡场里的母鸡,只要发现它们中间有一只受了伤,就会争上去给予致命的一啄”。
问题是,一个在精神上高高在上,总比别人看得透看得远的人,本该遭人忌惮,遭人嫌弃才是,但莫泊桑却赚得盆满钵满,极有读者缘,这又是为什么?
维特根斯坦认为许多事物是无法陈述的,但可以被显示出来,因而凡不可说的,就应当沉默。在莫泊桑这里,世上哪有无法描述的事物?那是语言的懒惰,是作家的无能,即便人心难测,也难不倒他。在他的作品中,不论现实图景、生活场面还是人物性格,都妙趣横生,绝不雷同,更不落俗套或陷于程式化。另外,他的小说全然是一种视觉艺术,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印象主义的文字绘画,读者如临其境,深陷其中,乐而忘返。这都归因于他对自然美,对光与色的高度敏感,以及绘画艺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的交融渗透。
如果说热血性格又不失敏感细腻,也算作别样的文学天分,那么,莫泊桑对艺术的超常敏感是有文脉相传的,属于令人眼馋的“文二代”。他的母亲热爱文学,饱览群书,不但熟习莎士比亚,还时不时给挚友写哀歌体书信,而他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则是一位早熟的诗人,也是福楼拜最要好的朋友。这不就是文脉吗?莫泊桑的血液里流淌着绵绵的灵性与诗意,“生来就是为每天的生活、残酷的真理、强烈的绝望而歌唱”,在自然主义代表人物左拉看来,是“微笑的幸运之神牵着他的手,引导着他爬到自己想要的高度”。此言虽然不乏酸溜溜的艳羡,但更多的是富含深意的赞叹:“他就是明晰、淳朴和力量的化身,他留下的作品永远能够征服人心。莫泊桑的荣誉将世代流传。”
时间证明一切,莫泊桑更像尼采所描述的那种生命力过剩的、酒神式的人。他的能量太过强盛,才华实在过头,若不绽放出一树繁华,老天都不答应。伴随着功成名就,挡不住金钱女人从各种渠道滚滚而来,豪宅仆人游艇喧嚣着锦上添花。所谓胜者为王,龚古尔文学基金会的A·拉卢的“胡子”之说有点意思:“虽然他的胡子是19世纪的,但他这个人不是19世纪的,无论从他的生命,还是他的短篇小说,莫泊桑都是一个现代作家。”才华横溢的人,就连胡子都被津津乐道,拿来说事,虽说有点势利,但不服气不行。
匮乏的安宁
按照尼采的说法,才华外泄过度的人,生殖力往往过剩,不仅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尼采的表达可能抽象了点,但若是对应到莫泊桑身上,他的悲情体现在俯视一切,但这个“一切”惟独不包含他自己,最终因为“凝视深渊太久而变成深渊”。
莫泊桑凝视的“深渊”,正是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先后经历了拿破仑帝国、第二帝国的建立与覆灭,直到普法战争失败后建立第三共和国,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政治动荡中,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各种冲突层出不穷,导致“世俗主义”如脱缰野马肆虐开来。早在莫泊桑之前问世的《红与黑》《人间喜剧》《包法利夫人》就揭示了19世纪法国政治的飘摇不定与社会上物欲横流的丑陋现实。因而,无论独具睥睨人心及万物的眼光,还是洋溢着为人处世逢场作戏的一贯风格,莫泊桑都是信手拈来收放自如,并非矫揉造作后天生发。
如此社会大环境,民生艰难,飘蓬浮萍,柳絮随风,各种悲观厌世情绪泛滥弥漫,莫泊桑也时常为生计发愁,普法战争结束后,好不容易在海军部谋得一份抄抄写写的小文员职位,烦琐的日常杂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严重束缚着他的心灵和才情,每俟假日,他就去塞纳河畔散步,拨桨划船,常常在游艇上与女人寻欢作乐,沉溺于床笫之欢、口腹之欲,为此还遭到福楼拜的严厉批评。如果将莫泊桑的生命分成文学与人生两大块,相比璀璨的文学造诣,他的生命光景怎一个“浪”字了得,紧随其后的“漫”字实在可以休矣,还是删去为妙。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人问诗人索福克勒斯是否还能与女人做爱?诗人出人意料地回答:“能摆脱那件事,我可高兴了,高兴得就像一个从疯狂、冷酷的主人手下逃走的奴隶。”都说莫泊桑是被杨梅大疮毁灭的天才,他之所以拒绝婚姻,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是因为年少轻狂时的初恋遭受打击,不再相信女人和爱情,真是这样吗?这里忍不住小人小心眼一下,认定是男人的原始情欲奴役着他,让他始终摆脱不了“那件事”,而成功后的名利双收则是催情剂和助推器,将他一步步拽向欲望的深渊。文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俗人。
瞧瞧人类精神天空中那些闪耀的群星,有几个能在名利场上洁身自好?《圣经》中就连“最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在他人生巅峰时,不也犯下奸杀之罪,应验了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的论述?大卫王的儿子,那个被称为“智慧之王”的所罗门,在他极尽巅峰的时候同样纵欲无度,莫泊桑,一个30岁出头的大才子,仰慕的女人那么多,送上门来自不必说,不去享用岂不暴殄天物?这难道不是现实中赤裸裸的世俗观吗?
依照蒙田的说法,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描绘自己生命的确切图像,我们只得取其片段,我们都是小碎片。从莫泊桑的传记里获知,他短短的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深度的苦闷中度过,安宁无处可寻,更无处安放。道理很简单,人种下的是败坏,就不可能收获美善。“精神的躁动、高强度的运动和轻浮的享乐得到满足后,接踵而来的常常是黑暗的忧郁时刻”。人世间的蝇营狗苟如此虚无缥缈,除了对人世庸俗的厌恶,“无尽的沮丧将他淹没”。
这位花花公子把自己定义为“古老淫荡的动物”,“不再是人类一员”,语气中多少含有无奈与绝望,敏感脆弱的内心似乎始终有一个黑洞,等待一轮又一轮的欲望去填补。他年纪轻轻就经历过战争,死亡的影子在他多愁善感的脑海里飘来飘去,挥之不去,导师福楼拜的过世也让他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后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的惨死更增添了世界的虚无色调,甚至地下墓穴里存放的干尸都在提醒他及时行乐的重要性。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以及哲学家对人类本性的蔑视和失望,认为女人是“低等动物”的观点加深了他对生命的怀疑,没错,人生苦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一如才华有基因传承,莫泊桑子承父业,浮浪的基因算是遗传得比较到位,比较正宗。因为小时候目睹过浪荡的父亲殴打母亲的狠劲儿——“他使劲地抽打,发了疯似的,继续打呀,打呀”,所以,从幼年开始,他就相信婚姻注定失败,后来他把这些恐惧和痛苦写进小说《伙计,来一杯啤酒》中,用主人公自暴自弃的人生来揭示丑恶婚姻的杀伤力。
人生多寒凉,表面的光鲜遮掩不住生活的狼狈与悲凉,莫泊桑功成名就后,“用另外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写点东西尽可能多卖钱”。他身上的担子不轻,既要承担整个家族的经济负担,满足花钱如流水的母亲的物欲,还要资助软弱无能的弟弟,负担弟弟一家人的经济开销,亲戚朋友们的需求也不好怠慢,可是,当他弥留之际,转眼望去,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只能凄凉地发出一声嘶哑的叹息,眼中满是泪水。更可悲的是,在他死后,母亲、父亲和弟媳为了争夺他的遗产相互发难,相互攻讦。亲情和爱原本就是稀罕之物,在物欲面前不堪一击,既然人已逝去,所谓的亲情和爱,哪里赶得上钱财的重要?
“彗星的光芒不会永远那么耀眼,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衰老。”渐趋衰老带来的无尽的痛苦也是莫泊桑悲观主义的一抹蓝调。长篇小说《如死一般强》和短篇《戴假面具的人》敏锐而无情地讽刺了衰老对一个习惯于取悦他人的男人所产生的影响,荒唐而又可悲。另一个短篇《朱莉·罗曼》则针对的是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美人迟暮时的张皇与虚妄。《小步舞》描绘了一对老夫妇繁华落尽时的凄凉与不甘,他们曾是名噪一时的舞蹈家,“被国王宠爱过,被王公贵族宠爱过,被整个时代宠爱过”,但最后却活成“既悲惨可怜又滑稽可笑的幽灵幻象,另一个时代陈旧过时的影子”。
这三个短故事和一部长篇,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相似的人生观,无意间拼凑起一幅真实的生命晚景:当荣华富贵烟消云散,肉身走向衰败,情爱一去不返,喜乐渐行渐远,面对低谷,面对命运的急转直下,虽然有所预料和设想,一旦身临其境,深陷其中,那种茫然无措,那种悲催感怀,甚或丝丝缕缕的厌世,油然而生。伴随着对繁华的留恋,伴随着对孤独的恐慌,虚妄与自欺成为苦捱余生的一味安慰剂。
亨利·特罗亚所著《莫泊桑传》结尾处有一段对话令人回味无穷,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演员去看望莫泊桑的母亲,临别之际,这位形容枯槁、白发苍苍、目光呆滞的老妪对女演员说:“才华和名望,您都有了。我还能祝福您什么呢?”女演员回答她:“安宁。”老妪凄然一笑:“反过来,也请您把这份祝福送给死后才能安宁的我吧!”
人有千算,天只一算,莫泊桑不曾预料,未到凄凉晚景,自己就彻底疯掉了,四十出头便重归尘土。一手高擎文学的旗帜,追寻理想的家园,渴望精神的寄托,探求尊崇的高贵,而双脚却又深陷世俗的洪流和物欲的泥淖,继而不可避免地踏上油枯灯尽的决绝之路,失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被狰狞的浪潮裹挟而去。他没能找到,或者说没有获得期许已久的一种神力,可以让他在自由之精神与旦夕之欲望间游刃有余,来回穿梭,既能向上不断攀援,又可轻松荡平内心蠢蠢欲动的烈火。
人生匆匆百年,大多流连于繁华所在,沉醉其中,实在难觅神性之心旅。莫泊桑无出其右,始终徘徊在焦虑与决绝、沉湎与清醒、痴迷与冷静、癫狂与理智之间,于他而言,文学恰似一叶轻舟,载着他的精神与神性以及才华徜徉在知性的繁华处,而名利以及名利的衍生品,汹汹物欲,同样如同一叶扁舟,载着他的肉身沉醉于灯红酒绿,糜烂于俗世繁华。
目力所及之繁华,信手牵拽之繁华,感同身受之繁华,相较于心灵之繁华,神性之繁华,孰轻孰重?孰低孰高?茫茫人世间,谁又会弃舟登岸踏歌而行?谁又能避开这条世俗之路另辟蹊径?万幸的是,莫泊桑在这条世俗之路上,在这片江湖天地间留下许许多多熠熠生辉的文字,因此,请一起为他永远的“安宁”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