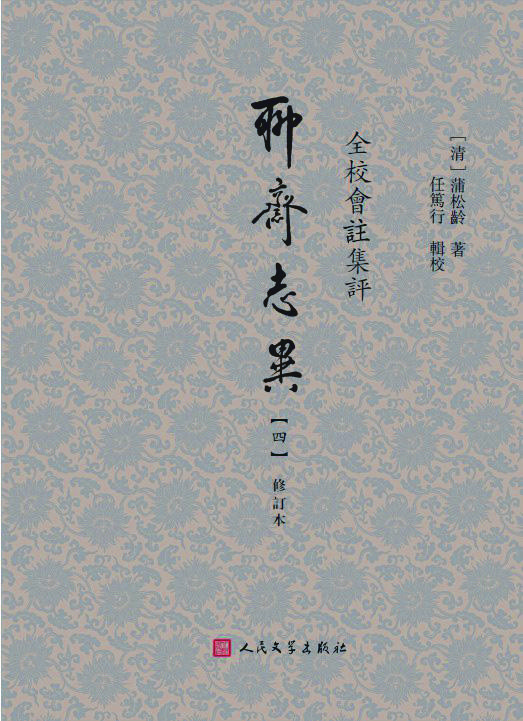笑骂文章奇千古
朱海啸:《聊斋志异》的创作应当说是具有交互性的,是在作者和读者以及其他群众的对话中完成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蒲松龄谈狐说鬼的故事题材很多都直接来自于亲朋好友(也即其最早的读者群)和其他普通群众。而除了这一类广搜而来的奇闻逸事,还有街头巷里的民间传说、前人已经写就的故事传奇,以及蒲松龄自己的想象创作。所以,在《聊斋》的成书过程中,“潜在的读者”与“现实的读者”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并且还成为了“潜在的”创作者。因此,《聊斋》的创作与接受在传世之初是紧密相连的,尤其生动的。
董恬:《聊斋志异》在清中后期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了,达到了“几乎家家有之,人人阅之”的地步。从地方传播到全国,这自然要归功于当时印刷媒介的发展,此外,文坛领袖王渔洋的青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清代,《聊斋》的仿作和续书已经大量涌现,从题材到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各方面,大多高度效仿原书,没有什么创新,这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真正确定《聊斋》一书在中国文学史坐标的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其为“专集之最有名者”,从而也开启了志怪小说创作的又一番热浪。
陈志伟:《聊斋志异》也广受域外读者的欢迎。18世纪中期开始,《聊斋》就通过翻译和介绍从中国走向了世界,首先在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传播开来,并引发了一股股仿作和研究热潮。鸦片战争后,《聊斋》逐渐走入了西方国家读者们的视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即以出人意料的高度肯定了蒲松龄的艺术成就:“这个(清)王朝的文学开拓者是一个讲述奇异故事的人”,认为《聊斋》和《红楼梦》是清代文学的代表。而法国汉学家克罗德·罗阿则说,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寓言。《聊斋》当之无愧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
人何寥落鬼何多
朱海啸:《聊斋》大部分篇章写的是狐仙鬼怪,但其实究其根本,也基本未跳出世俗世界的伦理道德,人类社会之伦理,及于狐仙、花妖、女鬼、禽兽,依然有效。如《胡氏》一篇,狐仙想和人类结亲家,但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半夜忽至,但凡有点脸面的狐狸,也是要规规矩矩地婚丧嫁娶。又如《夜叉国》一节,人类的男女之防、夫妻之专,在夜叉里也是有的,而且冲突的方式较人类更加激烈。《聊斋》成书于清初的变乱播迁之中,故事背景多涉动荡,而作为山东人的蒲松龄,身上又有神仙丹道和孔孟之教这两种迥异的文化基因,所以从夫妇伦常这个角度来讨论《聊斋》这部虚构得近乎荒诞的文学作品,也颇有趣味。
陈志伟:其实和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同,《聊斋》中的秀才们,对狐狸精的要求并不全然是“性”,纵欲之人往往下场悲惨,足以为戒;他们更希望找到“灵魂伴侣”。可见秀才们精神上的饥渴尤甚于身体上的饥渴,满足精神的需求往往比性欲的释放要难得多。《聊斋》里也很写了一些女子才华要高过男性的故事,比如《仙人岛》,神女实在看不下去丈夫蹩脚的文采,直接对丈夫说:“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于是丈夫“大惭,遂绝笔”。像这样女子才华见识高过男子者还有许多,这些狐女鬼神往往让我们想到柳如是、董小宛之类的传奇女子,以及《镜花缘》里多九公在黑齿国受两个少女“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之嘲的笑话。
董恬:狐仙们虽然神通广大,但面对的问题和人间主妇们并无不同。一个优秀的狐仙,要善于经营家庭的财富,借助自己的法力,使整个家庭的生活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如此这般狐狸夫人治家谨严而丈夫遂得雍容的故事,不鲜见于《聊斋》。更有妇把持家庭一切日常生计而致富,供夫读书进学者。而且即使是神通广大来去自由的狐仙,也没有“结/离婚自由”,婚礼乃是为和合两姓之好,不单单是夫妻二人的事情——即使亲家可能连人都不是。《聊斋》里多处可见宗族之间的械斗,就比如《胡氏》,一桩亲事定不下来,竟引发了人狐大战。
邹佳茹:狐仙们来无影去无踪,又本领高强,带着毫无理由的奉献精神,一头扎进秀才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待到书生不再孤独寂寞了,不需要她们了,她们又多半会迅速消失。《聊斋》中不但有大量的狐仙鬼怪前仆后继地投怀送抱,甚至还有两妖共同为书生侍妾者。但也有《婴宁》《青娥》那种男子仰慕女子而主动投奔女方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男子出于真挚的感情毅然翻山越岭地去追求姑娘,最终成就一段佳话。此类故事倒能算是爱情故事,而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狐仙们,于爱情味淡,于艳情味浓。
韶虞郑卫两相存
陈志伟:正如刚刚提到的,《聊斋》中许多故事都是对现实的映射,同时也是蒲松龄的自我抒写。《聊斋》中很明显的一大主题即为“士不遇”,这个主题往往伴随着科举不公、仕进无门这样的内容表现出来。例如《叶生》一篇,书中称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空有傲世之才而不逢知遇之士,即使受到丁成鹤的资助仍无法在科考场中遂愿。叶生因此郁郁而终,化鬼而终成举人,却已与昔日亲朋阴阳永隔。这样的故事在《聊斋》中数见不鲜,《考弊司》讽刺科举考场上行贿舞弊之事;《司文郎》《贾奉雉》嘲弄了考官的愚昧无知,这些应该都是与蒲松龄自身屡受挫于科场的经历不无关系的。
朱海啸:蒲松龄借鬼神事写人间事,悲恨之意摇荡笔端,所以《聊斋》中的故事才能如此切中肯綮,使人感同身受。蒲松龄纂集编写《聊斋》恰是我国古代“发愤著书”说的一种体现。司马迁受腐刑而著《史记》,其《报任安书》自明己志,在历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之徒遭逢困厄而成一家之言,明著于后世,功遗乎千载后,称这些作品“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蒲松龄编纂《聊斋志异》,同样是落魄孤茕之时,同样寄托着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无外乎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却有如此动人的力量,而成为不朽名作了。
邹佳茹:蒲松龄写作《聊斋》应该是有向史传书写取法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篇目后的“异史氏曰”,其实就是有意识地模仿《史记》的“太史公曰”。从蒲松龄效法史论的书写方式可以看出,他写作《聊斋》并不只是为了抒写自己的个人怀抱,且还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关怀。比如《金世成》,讲述一个疯癫的假和尚先靠饮食秽物夺人眼球,吸引到一大批信众,借机大肆敛财。县官看不过去,罚了他一顿板子,责令他修建孔庙。谁料愚蠢的信众执迷不悟,竟争相募捐以施救,孔庙仅半月便建了起来。这里,异史氏曰:“予闻金道人……谓金世成佛。……笞之不足辱,罚之适有济,南令公处法何良也!然学宫圮而烦妖道,亦士大夫之羞矣。”这就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表里不一、徒有虚名、妖言惑世之徒。蒲松龄在《聊斋》中是寄托了相当厚重的社会关怀的。
董恬:《聊斋》中的篇目,一部分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与现实精神,但是也有一部分,例如《耳中人》《瞳人语》等,并无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其实只是作为逸事被记载了下来,供人猎奇玩乐而已。《聊斋志异》中篇目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在蒲松龄的《自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火。”可以看到,《聊斋》中很多故事都是蒲松龄道听途说而来,作为奇物异事收录下来的。另一方面,他又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证明也有相当一部分篇目是蒲松龄苦心孤诣创作而有所寄托的。因此,阅读《聊斋》时必须重视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取向,否则难免有牵强附会之谈。
亦幻亦真演世情
董恬: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是非常普遍的,但毕竟二者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情节与主题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由程小东导演的三部电影《倩女幽魂Ⅰ:妖魔道》(1987)、《倩女幽魂Ⅱ:人间道》(1990)和《倩女幽魂Ⅲ:道道道》(1991),第一部虽然删去了小说《聂小倩》中聂与宁回府结婚生子的情节,并增加了“聂被迫嫁给黑山老妖”这一故事线,但总体上还是还原了小说,后两部则与小说完全脱离,甚至女主人公都被改换,小说则成了电影的“跳板”。《聊斋志异》同其他古典小说一样给影视界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宝藏,不仅是对小说的“覆现”,其中的“衍生品”也层出不穷。
邹佳茹:影视剧的主题也与小说有所不同,《聊斋》所呈现出来的是生死轮回、善恶果报等儒释道混杂的观念,小说《画壁》的主旨即如文末异史氏所说:“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而陈嘉上导演的《画壁》(2011)不仅大幅改动小说情节,还对小说的主题作了改动,电影《画壁》呈现出的是对男女情爱的肯定与赞扬,虽然电影里的仙境仍然被设定为“画中境”,是“幻”,但毋宁说这是平行世界的另一种现实,是“真”,“画中境”里的美与爱得到了尽情的渲染,这与小说《画壁》意在揭示“幻由人生”有很大的不同。
朱海啸:小说与影视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世情”的演说者。《聊斋》中画人画鬼、写狐写仙其实都是在描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贪官污吏对百姓的压迫,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最底层人民“善恶有报”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小说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影视剧则是表现当今社会的世情,《画壁》有一段情节是翠竹、云梅等仙女谈论自己喜欢的男人的类型,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爱情解放的隐喻,女性在爱情中可以占有主动权而不是男权的附属品。电影《画壁》里“姑姑”这一角色则贯穿古今,象征着存在于各个时代爱情的束缚者与扼杀者。
陈志伟: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它们并非意在表现神鬼与人间的对立,正如《倩女幽魂Ⅰ》中聂小倩的台词:“鬼跟人一样有好有坏,世界上许多人害人比鬼还凶”,《聊斋》里并没有“人—鬼”的对立,有的只是“善—恶”的分别,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始终的,所以小说《聂小倩》中宁采臣才会“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夺也”。《聊斋》写鬼怪狐仙实则也是在书写人世间,假如我们抛却“人鬼有别”的俗见来解读这部书,那么所谓的“虚幻奇特”其实就是“世间真实”,小说与影视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世人演说世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