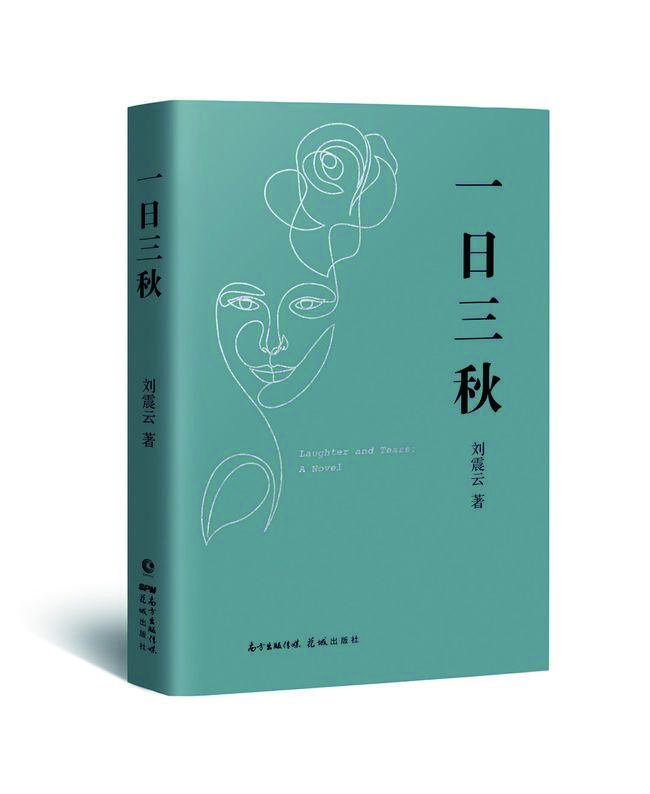在《故乡天下黄花》《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中,刘震云都在努力把握中国人的活法与想法。他说:“过去我也认为作品的‘社会’和‘历史’层面是重要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我过去的作品中。最后我发现‘社会’和‘历史’,都是有阶级性和局限性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这个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睡、如何玩以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社会、历史及其阶级性和局限性都表现在人的生活方法中。
“寻找”是刘震云持之以恒的写作主题。《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她不惜走出延津,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又走回延津。《一日三秋》延续了这个主题,对小说的叙事者而言是寻找一种恰当的叙事方式,对人物而言是要找到那个“说得着”的人。为了“说得着”,他笔下的人物出延津的出延津,回延津的回延津,出入成就了这块中原大地,让“延津”成为文学魔地:供养着花二娘这样从传说中来,到梦里专寻笑话的人,养育出樱桃这样从戏里来到戏里去的人,也生养着算命的、扫大街的、做豆腐的、炖羊汤的、炖猪蹄的、卖枣糕的、开杂货铺的“引车卖浆”之流。千百年来,延津人将沉默、痛苦和酸楚的白天提炼成笑话供养花二娘,滋养自己的梦境。白天的泪化成黑夜的笑,这就是延津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新作《一日三秋》别具怀抱,与莫言的《生死疲劳》对读别具意味。《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安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让地主西门闹轮回成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以动物的感官呈现20世纪下半叶的国族变革史。而《一日三秋》将此生与前生联系起来,将人物与动物(蛇、狗、猴)打通看,这不仅可以敞开宏阔的叙事空间,超越现实、魔幻的界限,更是一种触摸中国文化命脉的方式,维系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是同一条黄河。对于来世,聪慧如刘震云也保持缄默,用一句“天机不可泄漏”堵了大家的嘴,对未来存而不论,将希望留在心间。
标题“一日三秋”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时间感,开篇六叔的书法和结尾枣树雕的门匾写的都是“一日三秋”,这是人生经过秋季才能领悟的,见过枝头繁华遍地凋零,经历青丝变皑雪之后,“眼界始大,感慨邃深”。小说时空广大,人物繁多,次要人物三言两语,动物亦像精灵在字里行间跳跃。叙述的明暗呼应处理得非常讲究。“一日三秋”是此生与时间的关系,此生乃“一日”,是讲述的明面;“三秋”即前世、今生和来世,即小说的暗面,凸显“一日”,“三秋”则需读者自己去延长、捕捉和感悟。
前言“六叔的字画”交代该小说的写作机缘,叙事人放出诱饵等着批评家上钩,他将想法与疑虑一股脑儿全说出来:
把画作改成小说,并不容易。一幅一幅的画,是生活的一个个片段,其间并无关联,小说必须有连贯的人物和故事;还有,六叔有些画作属于后现代,人和环境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有些画作又非常写实,画的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常态,是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延续;二者之间,风格并不统一;画是一幅一幅的,可以这么做,而一部小说描写手法和文字风格必须统一。
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以日常生活为基调,把变形、夸张、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当作铺衬和火锅的底料;大部分章节,以日常生活为主,有些章节,出现些神神鬼鬼的后现代,博人一笑,想读者也不会认真;在主要人物的选择上,我从两米见方的剧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几个人,让其贯穿小说的始终;当然女主角之一,少不了六叔的红尘知己;所以这么做,是考虑这些人物离六叔更近。这些人物中,又以离开延津的人为主,因为只有离开延津的人,才能更知道延津;而六叔的画作,一直画的是延津;这是小说和绘画的区别;这方面跑出了画外,请六叔不要怪罪。同时,把场面拉开,也是给小说的辗转腾挪腾出空间。
小说与绘画的关系何尝不是文学与生活、现实与魔幻的关系?我们就着这把钥匙进入《一日三秋》俄罗斯套娃般的结构:表面涂层是叙事者倒叙自己的初衷。外层是花二娘的故事,小说结尾是陈明亮的化学老师司马牛写的《花二娘传》;中层是以樱桃为核心的上一代人的故事,魔幻和现实兼而有之,戏里戏外相互穿梭;里层是以明亮为中心的当下故事。各层互相关联,彼此照应。
花二娘来自传说。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望夫山(石),女性忠贞地等待丈夫归来是男权文化建构的集体无意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花二娘如此执意地要求笑话,就是因为她自己等待了三千年太苦。花二娘对应整个民族的无意识,樱桃的故事讲述的是女性的潜意识,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
樱桃的遭遇乃中国式的人鬼情未了。《白蛇传》的传说家喻户晓,从唐代民间流传至明代文人整理成文,几百年来有诸多版本。河南亦是该传说的发生地之一。无论是仙女下凡嫁书生,还是动物成精觅情郎,都是对纯粹爱情的肯定。大戏剧家汤显祖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白蛇挑战了人间的规矩却未改其志!爱是人间值得一过的有力证据。我国民间四大传说是颂扬至死不渝的爱情,为后世提供了爱情和人生的脚本。
《一日三秋》中,樱桃在戏里与李延生扮夫妻,现实中嫁给了法海扮演者陈长杰,他说戏时逗得樱桃咯咯笑,婚后却过不到一块,彼此都觉得“没劲”。樱桃上吊,葬乱坟岗遭受野鬼的欺凌,承续白蛇的命运。她的冤魂附体李延生到武汉去要求陈长杰为她迁坟,见到儿子就忘记了此行的初衷,附魂照片紧贴明亮身边,照片被后妈拿给马道婆施法,冤魂遭暴力不得不哀求儿子让他将照片投进长江,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樱桃的命运上接白蛇,下启儿媳马小萌,阳间和阴间的逻辑一致,女人只要漂亮就会被男性当成性资源加以开发。
明亮的人生是文本的主体。取名翰林时,他被望子成龙的宏愿压迫得发懵;于是奶奶为他改名明亮:明即聪明,亮乃慧根。明亮善解命意,从善如流,他为自己外出买汽水没能阻止母亲上吊自责,他为母亲灵魂的遭遇而痛苦;他为看奶奶走两个月回延津;他原谅抛弃自己的父亲,承担他的医疗费;他原谅妻子的污浊过去,马小萌曾为妓女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迫使他们离开故乡,又被迫离开道北菜市场,但也是靠了她攒的脏钱开了五家“天蓬元帅”连锁店。多年过去,儿子的同学仍以母亲的污点侮辱他。明亮牵挂奶奶渴望留个念想,一路追踪院子里的枣树打成的家具和门匾,却不知所终,就连曾挂此门匾的小楼也被夷平又按西洋景重建。明亮替父亲回老家迁了祖坟,而他母亲樱桃的墓却不在其中……
所有的故事无不悲欣交集,无非家长里短:明亮离开家是因为后母,马小萌离开家是因为后父。陈长杰不能养育自己的儿子,郭子凯不能让父亲去自己的家看看……父子、夫妻之间均有难言之隐。明亮在西安菜市场遭到同乡孙二货的欺侮,老董让他养毒蛇,结果却养了一条义犬“孙二货”,又因为狗死后思念不已而去探望自己的仇人孙二货,却被误认为是知交四海,其中渊源迂回曲折。这前世今生间的草蛇灰线就是命运,有慧根的人才能悟出这些来。延津有老董,武汉有马道婆,巫医文化在中国民间传统中无处不在。老董的看命生意戏仿了今天的医院,直播更是对网络带货的拟真。香秀临死前想要向她伤害过的马小萌当面道歉,这是人之将死,幡然悔悟,但伤害过陈明亮的孙二货却咬定自己“修理人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敞开了上辈子,这就好理解了。孙二货上辈子是猫精,而陈明亮妈妈是“蛇精”,自然就对上了。孔夫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认命也成了中国民间最普遍的哲学,它可以抚慰人的心灵。鲁迅批判阿Q精神渴望更新民族精神,刘震云提炼认命精神的积极面融入当代精神建构。藉此芸芸众生的小人物得以与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和解,宿命论亦在文学叙事中形成一股潜流。
《一日三秋》中,陈长杰从延津到武汉,两次婚姻都因为唱戏,临死却觉得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李延生未出延津,终老时也说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横行霸道的孙二货罹患老年痴呆仍要求看看自己的来生,马道婆也要求借好风去该去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吴大嘴前世贵为总理,此生当环卫工打扫自己,终因未曾准备笑话而被花二娘压死。六叔曾说“猴到中年”中那只猴是自己的自画像,后文写到明亮见到一只半老的猴子浑身道道血痕。六叔死后他的画就被六婶烧了,因为“那些破玩意儿,画些有的没的,除了他喜欢,没人喜欢”。司马牛终生搜集的、堆起来有谷草垛那么高的材料,在死后被他老婆当纸钱一把火烧了,儿子司马小牛告诉明亮:“那些东西,除了我爸当个宝,没人当回事”。花二娘与延津所起的化学反应再也没人研究了。
明面是思,暗面是梦。真实的梦境和魔幻的现实,孰真孰幻?梦对应着本我,乃最深的真,最真的我,可白昼来临即烟消云散。所有的人物都得忍住白天的泪、夜里备着笑话去梦会花二娘,她仍在苦苦等待早就死在黄河边的花二郎,这就是一日三秋的力量。
小说以司马牛写的极短的《花二娘传》结尾。“泪书、笑书、血书”这几个词汇亦适合《一日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