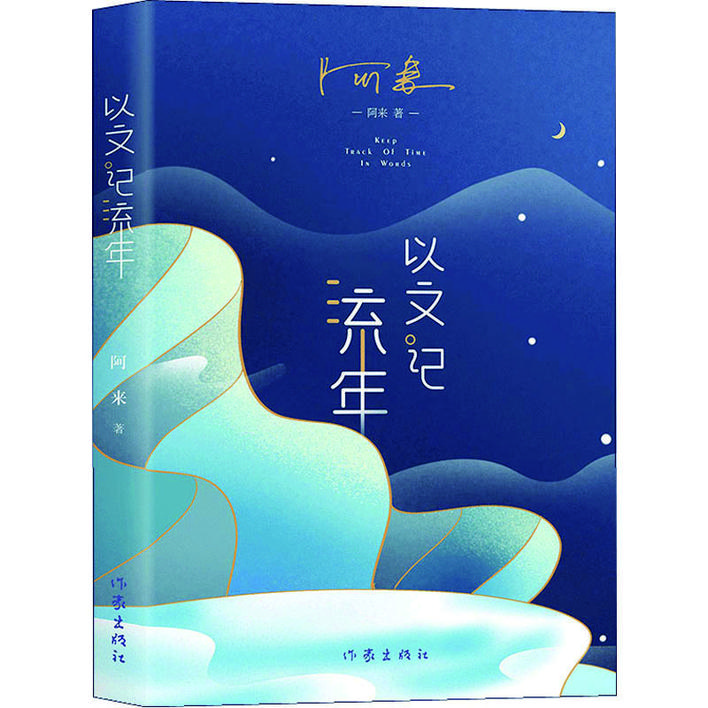在阿来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中,《让人们彼此看见》一文收入“鉴赏记”部分。比起那些洋洋万言的纪游文字,这篇为肖全金川摄影集写的序言不过2000多字,也许是这本书中最不起眼的篇什。然而我却愿意将其视为全书的“文眼”,因为它让我想起了20年前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屡屡提及的在相机快门上震颤不止的手指,也让我想起了他10年前出过的那本散文集,书名恰好就叫《看见》。“看见”是潜伏在阿来文字里的一条暗流,是属于他自己的一条文脉。铁凝曾经回忆过一段与阿来一同参加采风活动时的趣事:当大家都在为新疆那拉提草原神话般的仙境所迷醉并纷纷留影时,只有阿来抬着他沉重的相机离开了喧闹的人群,俯下身来,侧身半躺,镜头对准了草原上一支独自摇曳的小花。那一路上,阿来都在专注于这样的无名花草,发现它们短暂而异乎寻常的美丽。小说家的敏感,使铁凝捕捉到了阿来身上最异于常人的气质,那就是他对“看”的痴迷;而这种“看”,有时不仅要靠肉眼,还需要借助照相机的镜头——那是一种过滤后的“看见”。
在《看见》的自序中,阿来坦承自己“喜欢玩照相机,喜欢通过不同功能的镜头去‘看见’。但不是为了保存记忆,而是试图看见与肉眼所见不太相同的事物如何呈现”,而这种“看见”必须经过自己主动选择,并且要在经历、打量过的基础上加以思虑,从而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记忆库中打捞出来细细咀嚼”。这段夫子自道,与苏珊·桑塔格为人津津乐道的名言“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以及“摄影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形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因此,多年之后,他将桑塔格的话原封不动地抄录进《让人们彼此看见》中。
视觉无疑是人类最基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感觉。对此,柏拉图曾经给出一个有趣的解释——神在设计人的脸部时,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处于脸的上部,由此产生的视觉可以直达灵魂,“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蒂迈欧篇》)。但是,人类通过肉眼“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吗?换句话说,从古至今人们奉为圭臬的“眼见为实”,真的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吗?这其实就是一个困扰了哲学家们千百年的命题:如何看待原始的感官经验。在我看来,不管历史上对这一命题有过多少种解释,人类对最原始、单纯的“观看”都是不满足的,因此才会在其基础上渐渐衍生出“阅读”记录下来的文字、以绘画等艺术手段“再现”,以及借助照相机等工具去“看见”。诸如此类,均是对原始经验的提炼,是在“经历、打量过的基础上加以思虑”的产物,甚至所谓“发现”,也离不开心智的过滤和筛选。阿来评价肖全的摄影作品是对经验的“核实”而非“拒绝”,不是“逃离历史与现实经验的一种光影再造”,意味着他摈弃了两种态度,即“视而不见”和“全然虚构”,而这,也正是阿来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与原则。
收入《以文记流年》中的文字,都是阿来亲历的日常生活,阅读、游历、鉴赏自然离不开“看”,而书中最有“味道”的两篇《正逢重阳下沙时》和《川酒颂》,虽是写酒及与之相关的酒事,也与“看”须臾不可分。前一篇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传统酿酒技法中重要的“下沙”工序,皆是亲身所见所感;后一篇是浓缩的川酒历史,阿来在文中旁征博引,靠的是多年来阅读与思考的积淀,而他能在杜甫“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的名句中品出与“酒之美”并存的“风景之美”“人情之美”,更绝非单纯的“看见”,而是用心体悟的结果。一般的作者写酒,往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只顾得上渲染酒香之浓郁、酒味之淳厚,阿来却反其道而行之,很少涉及嗅觉与味觉,即使有,也不过是用“芬芳”等最普通的词语,却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描写自己所看到的,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联想和感想。这两篇文章,也就因此在近年来渐有泛滥之势的诸多“酒事文”中,彰显出卓尔不凡的质地。
上述几则,或是序跋,或是命题作文,或是主旨演讲,多多少少都有应酬之意。构成《以文记流年》主体的,则是收入“读书记”“出行记”“演说记”中的几篇长文。《回首锦城一茫茫》写杜甫与四川,特别是与成都的情缘。阿来别出心裁地用“诗史”的形式来写有“诗史”之誉的老杜,自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腊月杜甫自剑门入川写起,一直写到他在人生的末尾离川,在一叶孤舟上耗尽最后的时光,以诗串史,以史证诗。这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他想“诗意地栖居”而不得的10年,也是他“诗风大变”的10年,更是中国历史上盛衰突转的关键10年。阿来从杜甫的经历和诗作中映照出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氤氲在全文中的是对杜甫及其同时代人的“同情之理解”。全文就像一部杜甫客居四川生涯的纪录片,而阿来俨然身兼导演、摄像、旁白三职,带领读者回望杜甫一生、也是盛唐诗坛最后一缕余晖。《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是阿来第二次南美之行的笔记。感性的记游与理性的凝思交织成一幅绵密而厚重的印第安挂毯,和带着体温的文字一起抵御着南半球冬季凄冷的雨水。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句贯串阿来此次行走的始终,也勾连起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饱含血与泪的记忆。印加文明的辉煌、殖民者双手的血腥、覆盖在革命者遗体上残破的红旗,被诗人火一样的诗句映照,“我的炽烈的星星那样的心/将又一次在高空燃烧”。瓦尔帕莱索港的海滩是美的,拉巴斯港的湖边是美的,但这些美带给阿来的感受都不及他置身聂鲁达故居“船屋”时的沉思,以及在阿连德总统殉难的总统府前的惊鸿一瞥。而逡巡于利马旧城、印加故都、以及久负盛名的马克丘·毕克丘(通译“马丘比丘”)遗址,随着地势的不断抬升,面对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头骨,面对印加人留下的、原产于南美洲的农作物(例如玉米、马铃薯、番薯、西红柿、辣椒……)的巨大种子库,以及那个在强烈阳光下蔓延于山丘之上的、只能代表帝国昔日荣光的巨石废墟,不知阿来脑海中是否会想起他那部长篇散文的书名。他也曾经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一级一级地攀登那些“大地的阶梯”,试图在废弃的碉楼下追忆并寻找一个日渐远去的古老文明,四顾来路的漫漫与去路的苍茫。残骸与废墟,既是文明存在过的确证,也象征着生命的绵延。也许,复杂又特殊的民族身份,能使他更为刻骨铭心地理解眼前的景象。青藏高原与安第斯山脉,一东一西,两座世界屋脊,两个伟大文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此迸发出雄浑而悠长的回响。
阿来的“看见”,就是这样将目光从眼前转向久远的过去,同时又投向遥远的未来,就像他手中照相机的“不同功能的镜头”,常常能够充当“显微镜”或者“望远镜”,看见肉眼所不能见之处。在一张道光十七年的商品清单中,他能看出大清国正在从其天朝大梦中滑向迟暮之年,而在重新发现一个物种的故事里,他亦能看出“中国人也能以科学的方式重新发现和认知世界”。就在这篇书评的写作过程中,曾被阿来写入《海与风的幅面——从福州,到泉州》的泉州古城,于2021年7月25日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方徐徐展开的前景,扑面而来的海与风,正是中华复兴理想最舒展的幅度”,阿来用自己的方式看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正越过山和大海,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