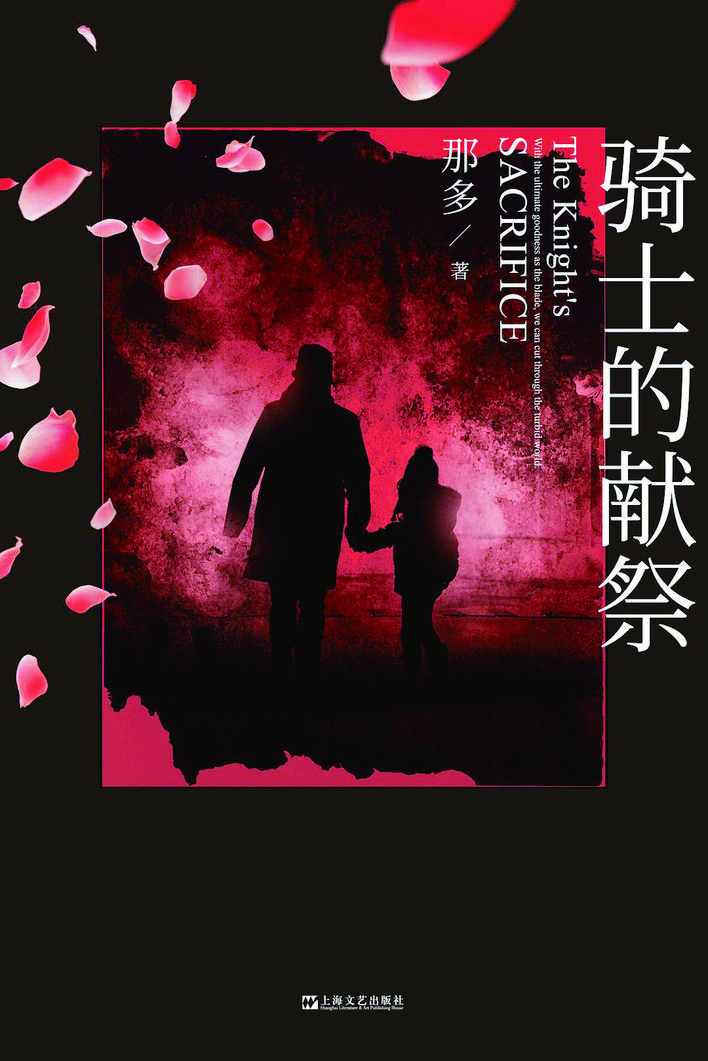那多2018年发表《十九年间谋杀小叙》,曾在他的老读者群里引发一阵不小的轰动,那多在类型小说的强度之外叠加了文学的强度,即人性的强度。在2020年的长篇小说《骑士的献祭》里,这种变化不但进一步鲜明,而且发生了新的意义。
《骑士的献祭》在那多的写作脉络中将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其意义不仅限于作者对类型小说创作的突破上。《骑士的献祭》明确地交代了它来源于社会新闻,小说甫一开头就交代了杀人凶手,也就是男主人公的存在,这种类型的推理小说当然也有,它使悬疑点落到了两个地方,一是凶手的杀人动机,二是警方如何识别并抓住杀人凶手。在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杀妻后不是一味藏匿,而是有他更大的计划与行动,因此是一桩未完成的犯罪,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他和警方之间的博弈是动态变化着的。另外,男主人公不是连环杀手类型,他未来的计划也与他过去的杀人动机紧密联系着,是同一桩事件,这就使得动机变得更加重要了。
然而这个故事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杀人动机,男主人公不是为“恶”杀人,而是为“善”杀人;不是自私无情地杀人,而是有情有义地杀人,甚至必须要用杀人来反证这种情义。小说的根本矛盾,除了找到杀人的真相外,更在于解释这个杀人的反常性,这也是小说标题“骑士”的意指。在推理杀人动机、作案手段的同时,也向读者揭示男主人公的个性心理特征。在一个现代市民社会里,何以还有“骑士”的存在?在市侩理性已成为生存首要法则的时代,何以还有“献祭”的行为?小说里的这个人,在结发的妻子抛弃了他和女儿之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七年后,他发现妻子回到所居住的城市,沦为乞丐,不但身怀六甲,而且患有精神分裂症,常有伤人、纵火等危险行为,但他依然把她从大街上捡回了家,并继续抚养她诞下的那个无生父的男孩。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善举,他也不会沦为杀人犯。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多写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看成是向社会推理小说的转型,小说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男主人公李善斌回沪知青子女的身份,女主人公时灵仪从农村到上海后的性格变化,以及后来独自南下闯荡的遭遇,涉及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史,“乡村——城市——新兴开发区”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所特有的空间分布与空间流动,与一代人的命运变化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骑士的献祭》确实更像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等小说,在长时段的罪案推理中展现社会变迁的面貌,并将两者交织在一起。但是,社会推理派小说的重点一般是落在犯罪的社会化过程及影响上,由此会做比较详尽的社会历史考察与记录,而这显然并非《骑士的献祭》的书写重点,小说没有完全用外部环境因素来阐释男主人公的行为,因此也不能简单地用社会推理小说去衡量它。
小说最后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这个专案组所有的警察一起,一人一元,共募捐了17元钱赠给李善彬的女儿李怡诺,这意味着警察与罪犯之间达到某种“心照不宣”,直到此处,小说在逻辑和美学上形成了完美的闭环,这种闭环不全是属于悬疑的破解与推理的完结,更是属于从人物内心出发的,哲理化的人物美学的达成。
这并不使小说失却了推理之美,可以说是从对杀人的推理变成了对杀人犯的推理。男主人公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这个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存在着这样巨大的情感能量,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能,但揭示芸芸众生身上属于“人”的原型的一切美与力,正是文学与艺术的功能所在。无论是《罪与罚》还是《悲惨世界》,都与罪案、追凶和赎罪有关,也都是从小人物内心上达人类的普遍思维,进一步上达历史、社会与宗教,而进入不朽。善于发现和挖掘也正是艺术创作最根本的特点。那多《骑士的献祭》最大的突破是,不仅仅在杀人案的层面看待杀人案,而是调动起一种观察杀人这样的特异事件的艺术眼光,正是这种眼光把这一事件的悲怆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一部好小说并非只靠意义取胜,这是肯定的,对小说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成功地再现。常常一个精彩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未必能生成一部同样精彩的小说。可以想象一下,有《骑士的献祭》中的这样一个现实原型故事摆在面前,用什么样的手法最能再现它,最能表达出真实之上的真实。那多作为优秀的推理小说家素有两个长处,其一是细节的认真与考究,其二是心理氛围的营造与渲染,这两点在《骑士的献祭》里依然展现得很充分,以至于其再现方式不但是有效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具体而言,《骑士的献祭》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虽是刻画人物、呈现人物心理,作者却并没有直接铺陈男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如果跟今年的另外一部新作《人间我来过》相比,后者中人物的主观心理渲染大大地增加了。在《骑士的献祭》里,读者认识男主人公,依然是依靠他者的眼光与种种细节的拼贴,通过各种旁观者提供的线索以及警察与专案组不断延伸的客观分析,来为这个主犯画像。在这个过程中,也生发出其他人物的描写空间,比如李怡诺、警察老冯等,都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有人会觉得,小说对男主人公这种旁敲侧击的写法,表现出作者在写作上的游移态度,是一种转型期写作的特征,在我看来,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倒不如说是由某种写作的能力决定的。刻画李善斌这样的人物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依靠叙事者全知全能的视角,带领读者对人物发生理解,这是多数现实主义小说会采用的,但这对作者的整体叙事能力与精神境界有较高的要求;二是采取内在视角,从人物内心出发,刻画心理、意识与主观感受,也能对人物形成较深的理解,但对某类人物客观的认知限度需要有精确的把握。在全知化、心理化之后出现的限制性视角叙事,不仅是对前两者的推进,也包含着极大的反思。《骑士的献祭》作为推理小说,集合种种有限的他者的视角来塑造人物主体,既符合推理小说的悬疑化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限制视角的写实手法,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展现出对客观世界的逻辑与合理性的尊重,不能不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写实的态度。
其实,这地地道道的写实态度,也就是一位小说家的基本素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