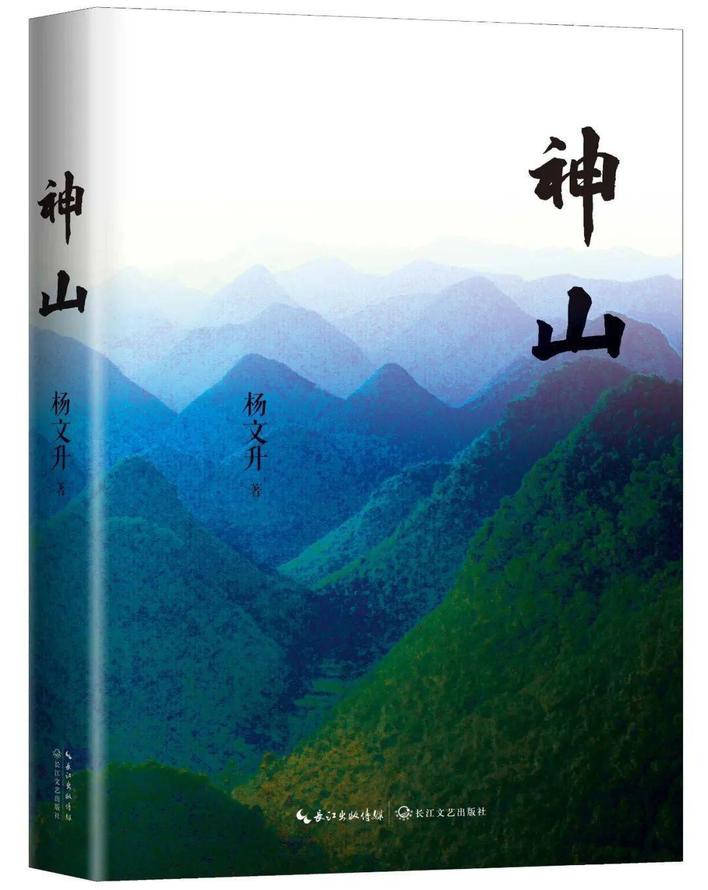纵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其中的史诗型叙事文本,往往呈现出家族兴衰史与民族发展史的交叉融合,这样也符合少数民族一般意义上的以宗族、家庭为主体的历史走向,在文本中形成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叙事;与此同时,其又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相呼应,从封闭的民族历史圈层中胀破而出,走向更为深远广阔的抗争史、革命史以至现代史,显露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面向,并在纵横交错的文化交融碰撞中,构成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性叙事的一种最重要的范型。
苗族作家杨文升的长篇小说《神山》是一部壮阔哀婉的苗族史诗。故事以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为开端,那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共和政体,历经军阀混战,直至土地革命战争,延续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前后解放军进驻桂西苗族地区,小说纵贯中国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成为苗族走出传统、朝向新生的现代史诗。
具体而言,小说以黔桂边界一个叫“挂丽姬”的苗族村庄为书写的中心,从祖父尤诺、祖母包诺和父亲尤本来到这里,便开启了属于尤氏家族的时代,也见证了村庄的跌宕浮沉。“挂丽姬”在苗语中意为“月亮闪烁的地方”,作者自述:“挂丽姬小如蚁,地图上找不到,历史书中无,卫星定位也没用,因它在本书出版前是默默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纯然的虚构,而是将一个容易被遗忘的或经常被误解的苗王尤本,以及他的族群故事和盘托出,重新表述和言说边缘之所在,并召唤一种“少数”之历史的记忆与纪念。
苗族人民天然对土地怀有一种不可割裂的依恋,那是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天人合一。比如,苞谷对苗族人而言是神圣的,在他们为饥饿所困时,天上会飞来大鸟并投下苞谷,“苗族人于是就种苞谷吃苞谷”。对苗族人而言,“苞谷是天底下苗族人的神食,苗族人血液里流淌着苞谷乳浆,每株苞谷都是苗族人身影!”又如在小说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芦笙,不仅是苗寨人表达哀怨情愁的乐器,更是他们生活和命运的象征,“吹着吹着,芦笙还会闪光,像镀了一层薄金。迷幻了,金笙,了不起的神韵。”我甚至觉得,小说之所谓“神山”,除了少数民族本身的自然崇拜和精神图腾之外,还在于映照更为广泛的器物自然如苞谷、笙箫等,它们通神、通人、通灵。
饶有意味的是,小说还重点描述了桂西地区苗族的民俗风情。比如,跳坡节是其中的一个大型传统节日,一般从每年春节正月初三到正月二十期间举办,成百上千的青年男女汇聚坡上,爬坡杆、吹芦笙、谈情说爱。苗寨的斗牛之风盛行,“斗牛好看,强强对垒,意志比拼,力量角逐,有得一看”,斗牛仿佛成为苗族人民果敢勇毅的精神象征。不仅如此,苗地的野猪岭、冷水江、难爱沟,以及小说中比比皆是的独特话语表达,如以南瓜比附人头,收人南瓜意为要人性命,“老庚”则为结拜兄弟间的互称等等,渐渐铺开苗族人民的生活图景,同时也代表着苗寨的地方性书写,更描述出了苗族文化的精神谱系。
然而自20世纪初期以降,苗族的传统遭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沉重打击。小说中,原本苗民赖以生存的苞谷,为洋烟以及稻米所取代;观云作为苗民重要的生活方式,也在村长尤本那里失去了魅力。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传统的苗寨遭受现代的物质形式、意识形态以及革命战争的冲击。不仅如此,小说还以一种开放式的叙事,不断以来自外在世界的未知,介入相对静止、固化的苗寨生活和苗人情感。20世纪前半叶遍地兵荒马乱,苗族人为了族群舍生忘死,为了情爱忘乎所以。而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于,小说以极为显豁的少数民族语言,包裹并推动着叙事,这是传统史诗性写作的范型。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描写了蒙古族人丁家四代近200年的历史,其中同样呈现出抒情与叙事相互包孕而生的修辞形态。可以说,《神山》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饱含着生活的情感,在精神的蕴续中喷薄,又在叙事涌动中重新开启感情的酝酿。小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以苗王为中心的叙事架构,与此同时又得以展露出苗族人民的生活史、情感史以至精神史。
可以说,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便是苗族人民的苦难史与反抗史,尤其在此过程中显现不可回避的破坏与持之以恒的重建。小说里,挂丽姬曾经历了严重的天瘟,2300人中死去了560人,而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重创中,又一次次顽强站立,重燃斗志,再创新生。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肃穆的悲剧之中,究其原由,出自尤本等人物身上的虔诚信念和丰沛情感。换言之,小说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复杂来表达人物的,而是通过一种古典的抒情气质,不断地烘托、渲染,裹挟着现实历史及人物命运推进向前。也因此,小说的叙事进程并不快,而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关于地方性路径、现实性场景与主体性情绪的凸显。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想要形成史诗的体量是有难度的。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叙事体量去承载,另一方面则是采取横断面的方式,以苗王尤本的家族史,映射整个苗族人民的民族史。可以说,杨文升的《神山》恢复了古典写作与现代经验的关联,其中所描写的苗王尤本的家族故事和情感变迁是极为典型的,既有流离失所无所凭依的悲情时刻,也不乏重建苗寨再起炉灶的豪情,有忠诚也有背叛,有情爱也有离散,有放弃亦有担当,由此塑造了以尤本为中心的复杂立体的苗族英雄群像。
除此之外,小说还由尤本家族的升落沉浮,发展出了另外的支线,如疯老太“杨钢奶”奋起反抗压迫,乱世女杰虽然最终人头落地,但轰轰烈烈的苗族农民起事,仍旧震慑了统治者,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根基。栗团长试图绞杀苗王尤本,侵占苗寨,尤本奋死拼杀,兵败后侥幸逃脱,在黔桂边界当起了路匪。偶然间,当地布依族压寨夫人成了“我”的“母亲七”。事实上包括尤本和女性们之间的情事,都颇具传奇色彩。小说由是赋诗于史,在崇山峻岭中上演了一出出鬼魅神奇的故事。这是1938年,苗王尤本折戟沉沙铁未销,山中两年,“天下大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抗日战争期间,尤本重新回到广西,参加民团干训学习,后成为挂丽姬地区民团专任团长,加入维持地方治安、团结抗击日寇侵略的队伍。挂丽姬也从一个最初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摇身一变成为500多户人居住的苗王寨。而且在尤本担任隆西民团副团长期间,励精图治,“隆西全境特别是隆西南部一大片苗冲多年来竟没有一丝匪患,苗民安居乐业,生活稳定,蒸蒸日上”。这成为了苗族人民真正的精神领地,甚至乎“粗壮的苞谷”与“娇嫩的洋烟”都能并立而生,共同收获。时间进入1940年代,在苗王尤本的主事下,一幢幢吊脚楼拔地而起,苗王寨得以建成。栗老团长也于此时送回了母亲丝丝,彼此言归于好。不仅如此,苗王尤本的儿女咪桑、尤拼、尤成、咪彩、咪瑛、尤冬、咪谷等,也各有曲折与传奇,不断延续着苗族的血脉。
从国民党统治到共产党隆西县政府成立,小说最后,当年的“老庚”红军营长黄政与尤本再度重逢,风云际会,新的时间开始了。解放军进驻苗寨,气象非比于寻常,三姐歌声缭绕,山河动容。挂丽姬“是我心中的爱山神山”,它展开了新的图景:“挂丽姬”历经磨难,依然生机勃勃,那个“月亮闪烁的地方”,就矗立于美轮美奂的群山绵延之中,苗族人民那歌诗一般如泣如诉的历史,也喻示了他们翘首以待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