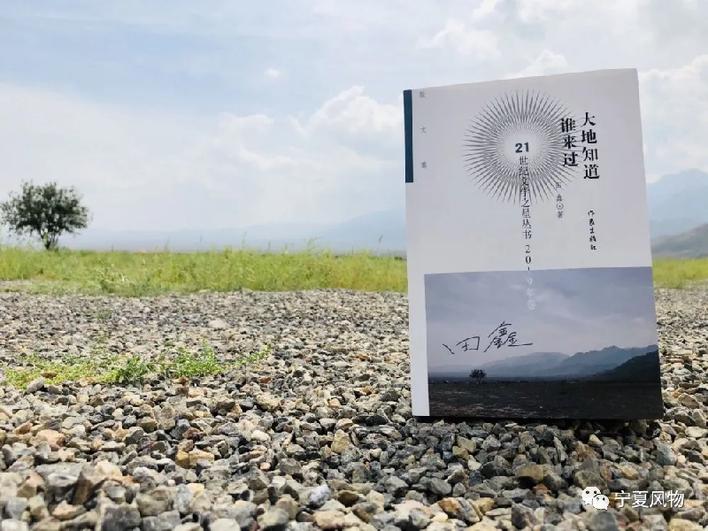对于宁夏乃至西部文学而言,西海固不仅因过往的贫瘠干旱而广为人知,它同时也因文风炽盛、作家辈出而令人瞩目。可以说,西海固独特的地域文化哺育了文学,而作家们对故乡大地的深情书写则使得西海固成为闪亮的地域文化名片。在郭文斌、石舒清、马金莲等作家笔下,西海固既是他们的生身之地,亦是滋养文学之心的源泉。与这些西海固作家相似,田鑫也在西海固的乡村长大,许是耕读传家的乡风熏染,许是少时失母的忧郁孤独,更或许是天生的读书种子,田鑫少时便如痴如醉地阅读书籍并激发出写作的热情。读大学时,他积极创办文学社团,与喜爱写作的同学一起写诗歌也写散文。大学毕业后,他在银川定居生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不改文学写作的痴心。与大多数西海固作家倾力书写小说不同,田鑫将主要的精力投注在散文写作中。他笔下的散文抒发出对童年岁月、对亲朋好友、对乡村故土的回望,流露出温情脉脉的怀旧和乡愁意绪。
某种程度上说,怀旧与乡愁几乎成了田鑫散文写作中无法抗拒的惯性与诱惑。在这样的情感心境统摄下,童年经验便成为作家不能割舍的审美对象和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在散文集《大地知道谁来过》中,童年经验并不仅仅是指作家对童年生活的忠实记录,它还包含了长大成人、侨寓到城市后的作家对乡村、对过往、对人世万物所葆有的纯真之心。当然,这里的绝假纯真之心,是马斯洛所谓的“第二天真”,即作家心智成熟后仍能保持的真诚之心,是经过世俗洗礼后,经过生存压力的淘洗后,向自然天性的回归。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曾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或者作家。”在田鑫的散文里,他深情书写故乡的吾土吾民,举凡河流、稻草人、风、脚印、牛、草、树木、地软等这些寻常物事,经过作者慧心的观察和诗意的描绘,便具有了返璞归真的稚拙,而读者也会因之矫正固有的认知,获得全新的审美感悟,进而与作者一同进入一个幻异而充满感性的世界里。
在《河流给不出答案》这篇散文中,作家以孩子的好奇探察河流的秘密:“河流内部的这些物种能提供一点关于秘密的蛛丝马迹。于是,我便开始琢磨着和水草、鱼以及蛙类对话。遗憾的是,浸润在河流里时间太久,水草已经熟悉地掌握了河流的内心,它熟悉自己主人的脾气,因此对我的打探圆滑而巧妙地予以了拒绝。青蛙由于带着祖先给的性格,一直游走在河流与岸之间,它没办法确定自己到底是河流的忠诚者还是叛徒,因此,对我的提问避而不谈,呱呱呱地卖弄着自己的嗓音。”在这段描写中,作家以童稚之心,运用移情的技法、飞扬的想象力及感官的全面打开,为读者呈现出河流的神秘热闹及大自然博大幽深的面向。在田鑫的散文中,他以儿童自由的天性、无羁的想象力及诗意化的语言描绘出一个泛灵化的生命世界。诚如童庆炳在《维纳斯的腰带》中所言,“真正的艺术家就是永远葆有童心的人,而他们的创作则的确是童心在更高的程度上的再现和复活。”
在田鑫迄今已完成的散文作品里,读者可以发现他的情感底色是沉郁而内敛的。少年失母的遭遇,成为他无法释怀的伤痕与隐痛,而广博的阅读则涵养出丰富敏慧的心灵。因之,田鑫的许多散文里总有一位孤独而忧郁的少年在村庄里漫游和思考。在《人总有一天会空缺》《花儿与少年》《把一个人种进土里》《供品》《灯光》等散文中,田鑫反复书写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巨大哀痛及终生无法弥补的缺憾。在《人一死事情就堆下了》的散文中,每到母亲的忌日,父亲“都会早早地备下香火,带着我给母亲送去。去的路上,我跟在父亲后面,偷偷抹眼泪,回来的时候,父亲跟在我后面,偷偷抹眼泪。”寥寥数语,写尽了夫妻之情、母子之情及父子之情的丰沛与深婉。这是颇见功力而又力透纸背的写作,展现出作家对生活的精微观察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当然,除了对母亲的思念,田鑫也写出了对祖父的思念、对少年朋友堆金的思念。更重要的是,作者推己及人,对乡村中那些隐忍、寂寞而又孤独的生和死的小人物,也以共情之心书写出他们在此生此世的生的艰难与死的挣扎。生命与死亡、孩子与村庄、人与自然被作家仿若带着魔力的语言召唤而出,这里面既有一个人的伤怀往事,也有对世道人心的体恤慈悲。或许,在田鑫眼中,岁月如同呼啸远去的单程列车,它携带着仓皇失措的我们通向生命的终点,然而站在列车上的作者则固执地保持着回望的姿态。于他而言,童年的真诚和逝去的风景永难忘怀,而在他的回忆和书写里,读者仿佛目见一个理想的、亲切的乡土中国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并用农业文明的舒缓挽歌来安抚我们日益斑驳、失根的心灵。
田鑫的散文承继了性灵派的传统,也借鉴了刘亮程散文思致轻灵的美学风格,以一个西部乡村和农民的观察者和遐想者的形象及风格化的文字著称。如果说刘亮程的散文是以“一个扛着铁锨在田野上闲荡的农民形象出现在文坛”的话,那么田鑫则是以一个孤独、沉郁的西部少年在乡村大地的思索者出现在散文写作的园地。他笔下的村庄和物事经心灵世界的提纯和淬炼,具有了浓郁的抒情性并达至认识论的高度。比如在《南墙根下》,作者体悟到生命的柔韧和脆弱:“突然觉得,老人们像是韭菜一样,被种在了南墙根下,岁月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真不知道哪一天,这一茬被割掉之后,会不会再也长不出新的来。”这种对生命的通透感悟既具有认识论的深度,又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田鑫已然是一位成熟的散文作家,他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他的散文写作也独辟性灵的蹊径。然而问题也是存在的,他的风格化和地域化固然能让人快速地记住他,但是假如相似的题材、场景、物事、观念总是没有变化的话,他的散文写作有可能滑向封闭化和单维化的藩篱。好在田鑫也似乎意识到惯性写作的弊端,在《飞翔》《准确》等作品中,作家的描写开始触及到当下时代村庄的新变,同时开始了对城市的观察和凝视。这些迹象表明田鑫的写作观念及观察世界的角度已然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转变尚未摆脱对乡土中国“滤镜”式的追忆。我们的期望是,田鑫在开采文学矿藏时能够摆脱对一个矿洞的过度依赖,他需要在群山和时代的风景中相见和感知。唯如此,他的散文才能不断扩大审美疆域,才能发现人世万物的幽微与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