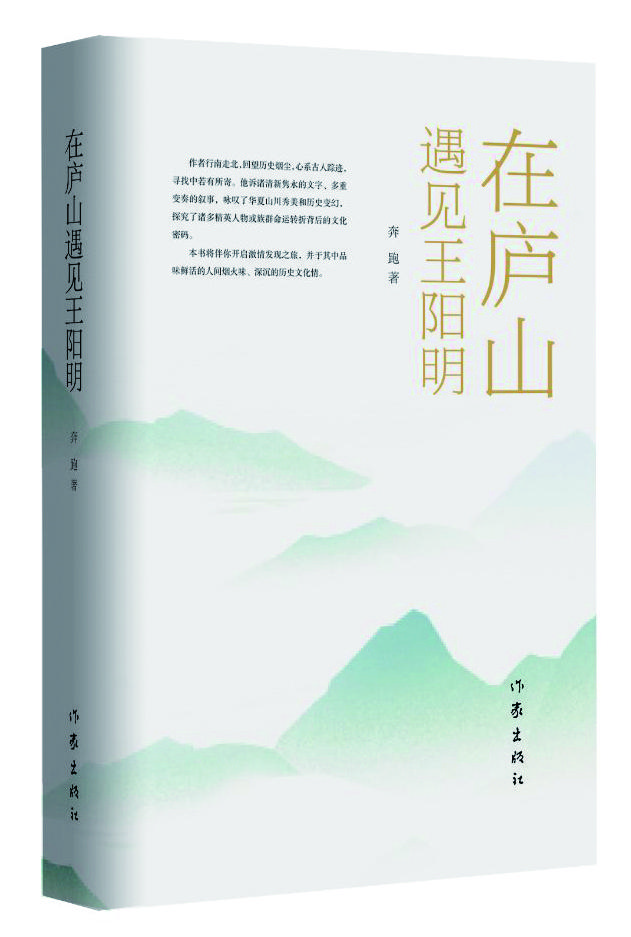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快乐成长/然后把一个/脸上涂着胭脂的女孩/领回家/你的名字叫陶醉/我想叫你陶越溪/通俗而简单/等你明白过来/我已经不在了
苏州的陶老师在某日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张刚出生的孙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粉嘟嘟的,还没有睁开眼。然后,他配上这样的诗。
深夜,在姑苏城的某个酒店房间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苏州老爷们儿的寄语中,有着活泼泼的生命体验,还有一缕淡淡的岁月惆怅,很打动人。当我把这份独特的“诗配画”作品推荐给朋友们后,颇感动了几个还远没有资格当爷爷的家伙。
陶老师者,《苏州杂志》主编陶文瑜先生是也。在他这里,我仿佛寻觅到了老苏州的踪迹。
此次苏州之行,是20年后的重访。
这些年,重访故地于我是既“怕”又“爱”。怕的,是在时光流逝中人非物亦非;爱的呢,那分明是因为曾经沧海。
苏州于我,便是如此。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高架快速路上,我心里颇忐忑不安。毕竟初次来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满怀热血童真的学生。
果然,远远看见那熟悉的塔影了,同时我知道,那虎丘几乎已沦为街心公园。
某个时刻,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仿佛苏醒过来,野蛮生长,生机勃勃,水泥建筑像雨后的爬山虎,快速漫过原本安静的郊野田园。我心里酸酸的,像与初恋的女孩不期而遇。她突然出现在你跟前,风采不再,带着点落寞萧条,轻而易举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海喧嚣中,变得难以辨识。
而当年造访这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在苏州大学借了自行车,满头大汗地骑来,像奔赴一场初恋之约,心头撞着鹿。口袋里则郑重地装着记事本和笔,我把她打动我的每一副隽永的楹联、每一通梦幻般的碑刻,都认真地抄录下来,回去后细细品味。
这次我只在陆羽井边的茶楼,要了一杯碧螺春,在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了片刻。
寒山寺,就不去了吧。甪直、同里,也不去了吧。于是干脆决定,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次统统不去了。就这样,我制定了一个“不招惹谁”的计划:白天去寻访几个名人故居,就在下榻酒店附近,有锦帆路的章太炎故居、凤凰街的吴大澂故居、滚绣坊的叶圣陶故居。晚上呢,去逛逛阊门。
遗憾的是,我在这三公旧馆都吃了闭门羹。
章太炎故居前的杂货铺老板微笑地看着心有不甘的我说,这里从不开放的,没收拾好,展品太少。吴大澂故居显然已经是一个修葺一新的文物旧货经营场所。邻居说,很多天没见开门呢。叶圣陶故居也大门紧闭,隔壁的大妈说,你要上班时间来,这里有人上班的。门口的匾牌显示,这里是《苏州杂志》的编辑部所在。看来,这是此行唯一的指望了。
似乎是要补偿我似的,次日上午的叶公旧馆之行则颇为惊喜。
门开着,照壁后就是一个普通小院,虽方寸天地,却充满苏州园林的自然精神。古树自必不可少,葡萄藤架下有石凳石桌,一捧池水清澈见底,竟也嬉戏着几尾鱼。这曲尺形的平房,就是当年的叶公寓所了。1935年,叶圣陶先生构此小筑,在此居住了两年多。
每间办公室都开着门,里边的主人都伏案在书堆中。对我们这样的游客,估计他们已修炼得可以熟视无睹了。
叶公的掌故且先放放,我想,陆文夫先生创刊《苏州杂志》时我就是读者,应该有资格去打扰一下这些坐拥书城的编辑先生。这曾经也是我理想中的职业呢!
推门而入随机拜访了两位,黄恽先生和陶文瑜先生。短暂的会谈让我感觉到,这方寸小院分明连接着江南文脉。
时间近午,黄恽先生正在不紧不慢地吃饭,端着不锈钢的饭盆边吃边与我聊天。他随手捡起一本装帧精美的书送我,给我题赠时问:你的名字怎么写?
这本名为《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的随笔集刚出版,是黄恽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他选择了一个有趣的领域:民国掌故。他说,“掌故”就是现在说的“八卦”。借生活所赐,他收藏了大量民国书刊,尤其擅长在小报上挖掘细节,写成饶有趣味的小随笔,集腋成裘,已经出版《秋水马蹄》《古色异香》《蠹痕散辑》等一批著作。
这样的研究,恐怕只有苏州学者才玩得来吧!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于“八卦”中也能见天地、见众生。这是黄恽先生给我的启示。他对周氏兄弟的掌故研究就很有趣。比如对至今为人所诟病的鲁迅婚姻,他从人们所不注意的小史料中挖掘出隐秘而有趣的细节,比如,鲁迅遭受过朱安两次“要挟”,对许广平也有家庭“冷暴史”。他于史料的辨析中,不经意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使得小研究有了“大”意义。他寥寥数语,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几年前,他曾公开发表高论,认为“民国”也成“热”是可悲的,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他努力做一些工作,就是在小报八卦中挖掘、考证,不加伪饰地呈现点滴的民国人和事。他的结论是,民国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他们就是你我一样的人,艰辛地活着。由此,观照当下以美化和缅怀为主流的“民国热”,恐怕只是今人借以浇心中块垒罢了。我想这是他所说的“可悲”之处吧。
黄恽先生看似琐碎的研究,貌似苏州男人的漫不经心,实则绵里藏针,跃动着一个学人思想的硬度。你稍靠近,他会硌疼你。
陶文瑜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景。
《苏州杂志》名誉主编范小青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看陶文瑜写字作画》,开篇说:“陶文瑜是写诗的,后来写小说,又写散文,写得都不错,再后来又搞书法,还没怎么的,就已经成了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了,接着又画画,不知是不是也要成为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了。”她赞叹:“真是个多艺的人才!”
不过“江南才子”陶文瑜没有和我谈写作与画画。见我主动进门寒暄,他就点燃了香烟,一副“聊聊也无妨”的样子。有人说他是陆文夫先生的学生,我不知道,也不在意,不过作为《苏州杂志》主编,他开口就说,陆老师那一代人走了,带走一个时代。烟雾缭绕中,他淡淡地而直接地比较着“两个时代”:他们对昆曲有感情,而我们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他们在人生历程中对国学有精深的研习,而我们呢?所以现在这本杂志,与那个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似乎连“乡愁”都没有了。
然而,没有“乡愁”的陶文瑜先生,似乎就沉浸在“乡愁”的一事一物之中。
他写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无非江南风物、苏州饮食、家长里短,不觉间出版了《苏式滋味》《茶来茶去》《红莲白藕》《纸上的园林》等多部作品。据说本本娓娓道来,出神入化,令人神往。我还没缘分阅读到,他手头也没有存书可供题赠。
他对自己的书法颇感慰藉,似乎自己的人生因此而没有白活。他的微信朋友圈里,不少是“写字等天亮”之类,可见写字对他的重要。他的书法浸染了江南文人的气息,楷风隶意,含蓄隽永。尤为打动人的是,他书写的内容多为自己的创作,说是创作,也不过日常生活,随手拈来。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他亲自手书的楹联,云:“春姑娘敲门,陶爷爷在家。”其中天真意味,令人忍俊不禁,心生欢喜。这样的门,你是不是也愿意去敲呢?
行文至此,本文篇首“陶爷爷”对新生孙儿的寄语诗,似可读出更多的内涵。他主持的这本著名杂志,似乎也是一期期“寄语”,写给这座寻找乡愁的古城。
好吧,可以去阊门看看了。
天公作美,知道这“烟雨江南”是要配上毛毛细雨的。不过,雨中踯躅的我,似乎失去了当年在此游历的全部记忆。只有一个印象,这阊门是古典舟行时代的“水门”,远行的人们在此上船,橹声咿呀,到七里外的枫桥镇住上一晚,再驳接运河上行走的航船。
一部《石头记》,是从这里开始的。黛玉姑娘上了船,要去经历她那絮絮叨叨的“木石前盟”。
苏东坡的“浪诗”已经被人醒目地挂在街头:“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
离愁在这里才刚刚酝酿,要到枫桥夜泊时才会小规模爆发。这条短短的七里水路,就是乡愁淌成的河。
似乎也带着某种隐喻,这里竟是所谓“寻根纪念地”。码头上立了一座碑,记载说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迁徙苏淞嘉湖杭五府人口,填充江淮。人们从这里出发,又把这城门作为游子归乡时辨认的标志。
出发地,也常常又是归乡路。能拥有如此完美时空对接的人,是多么幸运呢?更多的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归途的。
住在城东新区的朋友们来约见了,说阳澄湖的蟹正肥着呢。古老苏州不再走那相思成河的水路,而是在城东的广阔空间,蹚出了一片新天地。那里,已成为太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远行的目的地。
苏州的乡愁,该重新定义了吗?
(摘自《在庐山遇见王阳明》,奔跑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