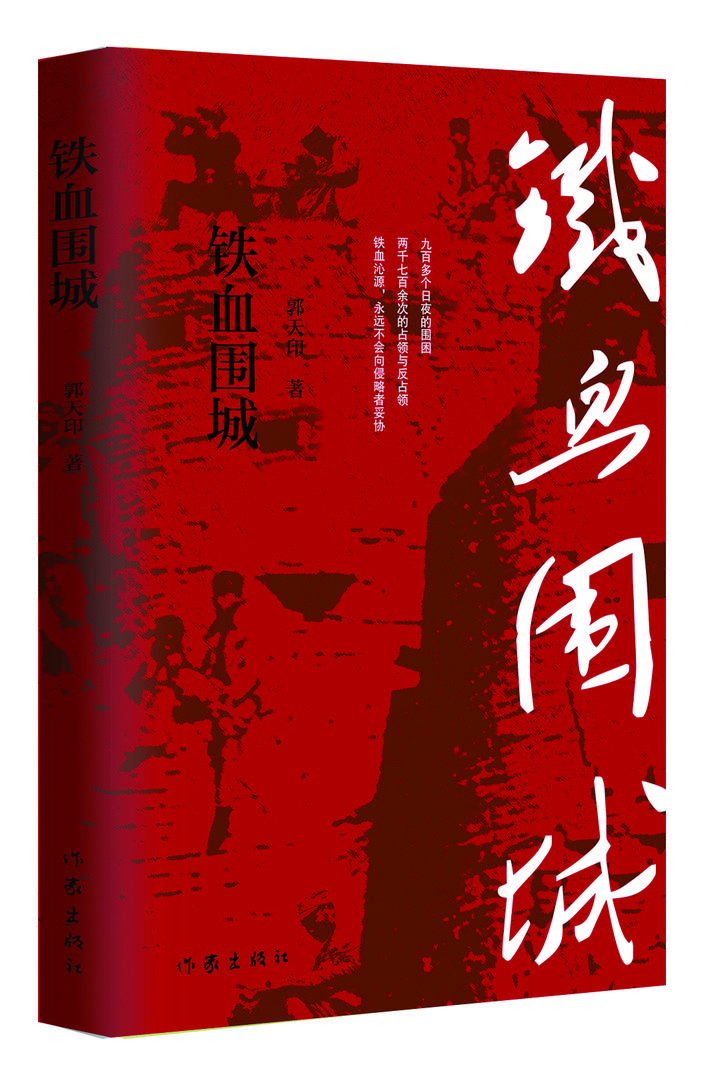当代的我们享受着前人从未有过的富足生活,然而又面临意义感的缺失与精神上的荒芜。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每个人开始审视生命的意义。“向死而生”,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死亡威胁的过程,就是内在的虚无感被洞察、进而有动力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波澜壮阔的过程。我们在郭天印新作长篇历史小说《铁血围城》中,就看到了历史向我们提供的最辉煌的例证,一个个平凡的个体是如何熠熠生辉,一个普通的群体又如何气壮山河。
《铁血围城》记叙了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整整两年半时间,在仅有8万人口的太岳山区腹地沁源,所发生的镌刻在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奇迹。奇迹之一是这8万人口的山区,保护和培育了太岳区八个县的抗日政权,容纳着决死队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两个子弟兵团;奇迹之二是这方2549平方千米的地域上,在此期间付出了一万多人的生命代价,却没有出现一个汉奸,人民群众高度的革命觉悟、党员干部坚定的党性,这个群体凝心聚智的向心力,都成为宝贵的革命财富;更绝妙的奇迹之三,是在战斗中爆发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智慧,让人人都成为战斗的“能动者”,每一个个体喷发的不仅是身体的潜能,还有大脑的潜能,他们用鬼斧神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粉碎了日酋冈村宁次精心设计的“山岳剿共实验区”作战计划,消灭了日寇精心培养的优秀军官,打垮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部队,尤其是沁源人民创造出了诸如“蛤蟆阵”“苍蝇蚊子阵”“鞭炮阵”等千变万化、奇思妙想的战术,让日寇心惊胆战夜不能寐,竟然纷纷“罹患”精神分裂,无药可治,烙下了终身的战争阴影,这也为世界腥风血雨的战争史增加了极富荒诞的戏剧感。
从创作题材角度来说,郭天印先生是战争写作的专家,是写作战争的高手,他对创作有要求有原则,这些年来,他用作品证明了他的实力。从早期的《美利坚大崩溃》《航空母舰北京号》,可以看到他对于国际国内大格局战争的理解和分析都有其独到之处,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前的十多年,他就在其小说《美利坚大崩溃》中有过相关预测,所以后来奥巴马当选之后,国内有不少媒体也曾专门对此有过采访。而他的历史小说《大宋三杰》《郑成功》和历史人物传记《狄仁杰传》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的探究深度,尤其涉及到战争和兵法方面,他总能自成体系。近年来,他更加专注于发挥其优势,在《太原保卫战》《沁源围困战》等几部作品中,他站在国际大格局、历史宏观背景下,去分析和描写局部战争,形成了大收大放、纵横开阖的洒脱感,将战争题材小说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沁源人,郭天印对家乡的热爱无比深沉。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土地,熟悉这里的每一种文化现象,熟悉这里的每一段历史。在写作《铁血围城》之前,他曾经向我展示了其从日本档案部门搜集到的关于战时大量日军官兵在沁源作战时期造成精神分裂,而日军医院诊断结果却是“不予投药”的最原始资料的照片。这些年来,他搜集到的来自于世界范围的有关沁源围困战方面的历史资料,应该是无人出其右了,因此,《铁血围城》中涉及到的历史和相关人物,都有原型。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但具有历史的准确性,还有活灵活现的历史细节还原。这种还原能力,使《铁血围城》无论从格局、情怀还是感染力上,都堪称教科书般的存在。
阅读《铁血围城》的收获是多方面的。一是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可以当作兵法博弈的教科书。熟悉日本文化的人知道,日本民族内在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外在则对其他优秀文化倾心向学,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文化对其影响甚大,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则转向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正因如此,在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之前,他们是做好了各方面精心准备的,其选拔的将领必然是深谙中国文化的,尤其是兵法上,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其他中国的兵法思想,他们都有过学习。而除了军官,日军士兵也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熟悉枪械格斗等战术,也有严酷的体格训练。在军队的管理方面,更有严密的规则。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他们采用拉拢、威慑、诱骗等手段让中国人自己内斗等,其计划可谓分外详尽,也确实收获颇丰。而这种实事求是的对于敌方阵营的描写,恰恰衬托了我军民在战胜日军整个过程中取得胜利的来之不易和智慧勇敢。同时,《铁血围城》是站在世界战争史的视角来描述沁源围困战的。书中“两个‘中国通’”一章中对冈村宁次大将和花谷正少将这两个著名日军军官的细节描写,准确地概述了他们的军事水平和战争智慧。作者通过列出其作战计划、攻打沁源的人员配置、各级军官的性格特点等等,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宏大战役的不同场景。不懂军事、不了解彼时敌我双方各种态势的人,是写不到如此生动又真实的。这种充满军事专业性的描写,让读者全方位了解了日军攻打沁源的周密准备,也使我们能够站在抗日战争全局的视角领会冈村宁次如何精心设计 “山岳剿共实验区”作战计划的阴毒与老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发生在沁源的这场战事对于其他战场的重要性,甚至还关乎着整个世界战场的走向。
在“激战迷魂谷”“伏击州西岭”等章节中,作者以环环紧扣的手法揭示了日寇之所以失败的关键。冈村也好、花谷正也好,他们的作战方略不可谓不精,自以为学习刻苦的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掌握了中国兵法的精妙,却不知“失道者寡助”这个前提,他们的残忍暴力狡诈和死亡威慑并没有吓倒沁源人民,反而激活了人民这个“可载舟亦能覆舟”的群体,日本军官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战争智慧就这样被卷进了人民战争滔滔不绝的洪流之中。正如萨特所说,死亡宣告了生命意义的虚无。人民群众在虚无中醒来,挣脱“烦、畏、怕”的牢笼后产生的潜能是不可估量的。在“李猛就义”的章节中,李猛和他的媳妇走向死亡的毅然决然,尤其是那位农村妇女在与丈夫一起赴死时的那回头一笑,瞬间让我们在鲜血和热泪中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逐渐醒来时爆发的巨大力量。
《铁血围城》阅读价值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战争的深度思考。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角度来说,现象要通过“意向性结构”来分析,要抛弃那种抽象的,固定的“本质”概念,因为这个所谓的“本质”只要是物化的,就不会固定不变。战争这个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它是扰乱空间和节奏的突变因素,它改变了所有卷入者的原定轨迹,是“固定本质”的破坏者。比如在《铁血围城》中,江德昌这个少年生来淘气活泼,按照原有的生活轨迹,发展下去就是娶媳妇、生孩子、为生计劳碌一生的众多百姓中的一员。但是战争发掘出了他神枪手的天赋,继而在党的培养下进一步成为优秀的指挥员。战场是智者的角逐,个体在死亡威慑下,都会激活属于自己的求生本能,从而发现自己的天赋,但天赋是把双刃剑,只有天赋和理性共同作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江德昌神枪手的天赋并不能让他成为战斗英雄,他只有通过在参加革命后的理论学习和训练,才能出类拔萃脱颖而出。此外,《铁血围城》中杨铭之的蜕变、洪尚礼的成熟、江淑英之为农村新女性,都是打破了原有的生命轨迹,走向了更高层级生命的典型代表,郭天印在塑造人物中的这种哲学高度,也形成了独属于他的战争叙事风格。
第三个方面是文化性。作者对当地文化现象不仅异常熟悉,还有长期且深入的研究,因此《铁血围城》中的人物对话所使用的语言、民间小调的唱词、当地衣食住行的细节等,都还原得很地道,有些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更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比如“冬天的故事冰坡伏击”“取义成仁有张成”两个章节中,李守清这个人物的言谈举止,他与张二俏的感情纠葛,就非常能体现当地风土人情。张二俏因为甜言蜜语而心动,因为有悖人伦而懊恼,因为仇恨而觉醒,这种性格的原始和率性,正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真实塑造。阅读《铁血围城》就如同进入到了沁源这片土地的深处,使读者能呼吸到太岳的风、尝到沁河水,穿过丛林土地,和那里的人民苦乐在一起,幸福在一起。
郭天印在后记中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时候,我们重温沁源围困战的历史,讲述这段历史中的一些永远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我想这应该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后人的负责。”正是如此,作者这一份对历史的尊重,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都浓缩在了《铁血围城》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