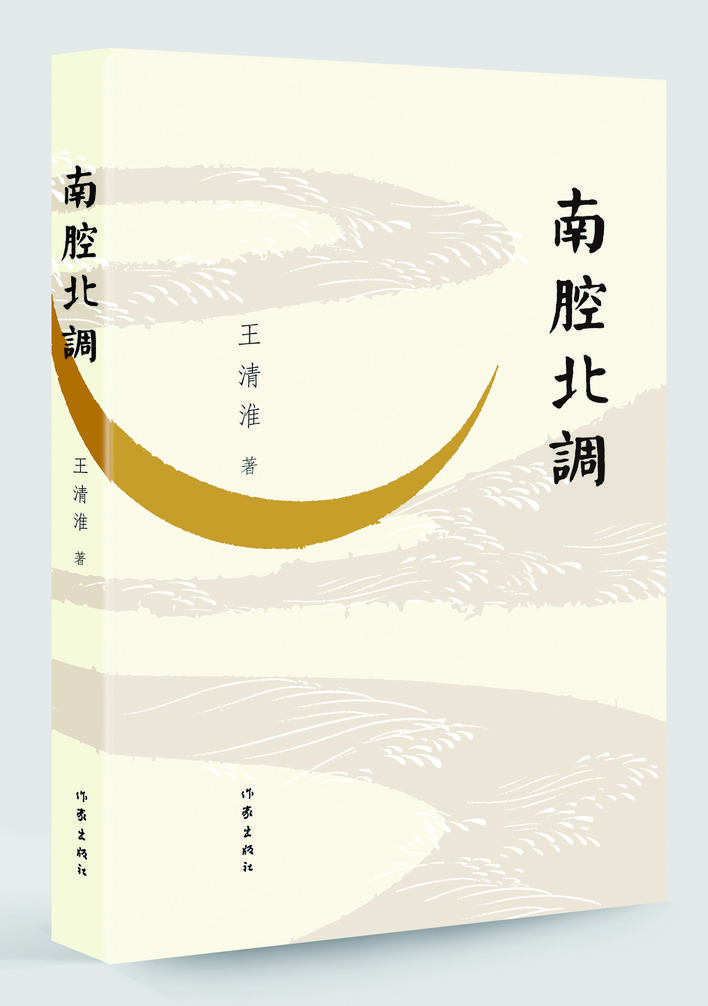理性批判与文化启蒙是中国现当代杂文创作的优秀传统,随着后现代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怨刺”杂文走向式微。王清淮新近出版的杂文集《南腔北调》,借用鲁迅“南腔北调”的式与势,抒写思想锐气,用“含泪的微笑”点破虚假的文化镜像,承担理性文化批评与社会启蒙教育责任。
《南腔北调》共收文76篇,分为“南腔北调”“朝花夕拾”“花边风月”“野草热风”“三闲二心”“故事新编”几个模块。诸模块在主题、风格、语言表达方面文脉贯通,总括内容,可分为文化解码、“伤痕”叙事、解构袪魅三大方面。
文化解码。主要集中于“南腔北调”部分。作者游走于村庄都市,边关隘口、戈壁大漠,沙里淘金,以审美之眼,谈笑间引领读者认知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遗珠,抨击当代人对文化传统的随意简化与阉割,让读者明白何谓当代精致的仿真文化垃圾,何谓“能指”坚挺、根脉明晰、纯真原味的民族传统文化根码。
《王二羊煎饼》《喀左茶》《低调的易县李家包子》《徐州把子肉》《敦煌回锅肉》《朔州鸡蛋》是一组“味觉”文化飨宴。有感于丢失魂魄的现代仿品的“无味”,作者更推崇传统工艺的坚守。而那些外表精致花哨、实则偷懒的现代工艺品,欺骗的就是生活在城市物欲的大茧里,在传统文化面前几近“盲视”又假装“精致”的现代人。传统的喀左煎饼、喀左茶早已因自私偷懒而变味。浮躁而无知的现代人吃的甚茶?不认识的普通树叶而已。而边缘小城易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包子,则朴实无华,低调自然,味道真纯。
《徐州把子肉》以奔放的味觉快感与语言快感,释放身体与味觉的存在主义,用北方传统最直接的感官味觉符号,嘲讽现代市民阶层追求的“假贵族”口味,解构当代伪市民趣味文化。《敦煌回锅肉》《朔州鸡蛋》则暗示现代背景下,“原味文化”只在边缘地带存在,在生命体验主体的味觉中存留。而大都市文化中心则充斥着千篇一律、批量加工、流水线生产的“同质同构”的当代嚼蜡文化伪本,它们与传统“原味文化”形似质异,同分异构。
《狗不理包子与二十四桥》《傻庙》《净土》三篇,批评很多地方将“原味文化”庸俗化现象,赞赏硕果仅存的文化“净土”。在作者的视域里,伪文化文本蠢得离谱,傻得可怜,而原汁原味的“文化底本”荡然无存。易县“后山奶奶庙”的世俗功利,荒诞胡为的现代化神像符号(手握方向盘的车神,手捧金元宝的财神),嘉峪关文殊山新建的“万佛塔”中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神像供奉,与“易县李家包子”“敦煌回锅肉”“徐州把子肉”“朔州鸡蛋”所秉持的“原味文化”追求形成鲜明的对比。
《净土》是作者少有的歌颂文章,在嘉峪关文殊山“傻庙伪神”林立之中,在不起眼处,作者偶遇被“孤魂野鬼”和“门票高墙”遮蔽的原味文化文本——古色斑斓的文殊寺,有一种“文化休克”般的狂喜。在这里,传统文化竟然没被利益熏染,其行为规则非常符合佛教的“原教旨”意蕴,遥远的地方保留着佛教的一方净土。《藏在核桃林的大学》对于当代大学校园频繁发生的“去真存伪,去精存粗” 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对于清除校园历史“文化包浆”的做法,予以嘲讽。
“伤痕”叙事。主要集中在“朝花夕拾”与“花边风月”部分。所谓“伤痕”叙事,是指打开个人记忆的阀门,以自我体验的边缘例证,撩拨历史巨人那藏不住的“小尾巴”,揭露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诡计”对多类人的捉弄。通过讲述亲身经历的变形小故事,填补当代中国宏大历史主流叙事遗留的缝隙,用历史“活体”话语与充满生命体验的细节描写、听觉与味觉物象,折射美与丑、崇高与卑俗、高光与暗影共生共存的复杂历史情境。
《亲亲曲麻菜》小中见大,感情充盈,是该杂文集中最富诗性体验的篇章。通过描写“我”与曲麻菜的特殊情缘,褒扬曲麻菜出身卑微、去来无痕,虽居功至伟但却追求无功无名的仁慈大德,借机宣泄一代人被压抑的“饥饿伤痕”形成的无意识心理。
《青藤上的苦瓜》《我的大学》《夏家河之殇》《欢乐邻居》四篇同频共振。通过记叙过去经历的荒诞往事,吐槽个人难以忘却的伤心史,类似于文学创作中的创伤记忆与心灵史叙事,即将那些影响自己价值观形成,且挥之不去的揪心往事叙述出来,缓解愁肠百结的文化焦虑,抚慰心灵的伤痛。
《青藤上的苦瓜》中的公社书记杨吵吵,伺机而动,牛皮吹破天,为了升官,驱赶村民孩童大冬天修“面子水利”,其结果是造成洪水泛滥,劳民伤财,甜了自己,苦了群众,闹得童年的“我”饿肚子。《我的大学》讲述小学校长谢宝树积极响应“学朝农,迈大步”号召,在偏僻山沟里的小学中办起了“南洼大学”,让初中毕业的“我”教高等数学,因不够积极挨了批斗。《夏家河之殇》《欢乐邻居》则是来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但“任性胡为”的主儿依然不少。《欢乐邻居》中的大学领导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硬是将一所大学的新建校园,活生生地整成一堆笑话,与《藏在核桃林的大学》中的“祭酒”成了难兄难弟。
夏家河,大连郊外一片达到梦幻美级别的浅海滩。它是大自然“无为”的存在,各类海生物与人类和谐相生的典范,也是一代人充满青春浪漫温暖气息的精神家园。骤然间,轰鸣的机器声打碎了沙滩上红男绿女的仲夏夜之梦,“温暖如绸缎、温柔似绵羊”的小海浪,柔软而亲和的细净沙滩,一夜之间变成了粗鄙的养虾场。后因台风肆虐,养虾场被毁,再变则成屎尿横流、臭气熏天的粪池。作者逃到成都读书,青城山的负离子空气和锦官城的花香,都没能将这股污秽之气洗涤干净,以致积淀为心灵上的夏家河之殇。
《工人贵族》《麻醉药》《磨刀人》同气连枝,作者将自己的痛点从对“有司”的声讨,转向对底层人的批判。与果戈理、契诃夫笔下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不同,在作者笔下,“小人物”的身形里隐匿着伺机伤人的利爪,内心中藏有“凌厉的阴毒”。《工人贵族》中有三个底层人物,一位农用拖拉机手,两位校车司机,他们依仗手握方向盘的权力,用坏心眼戏耍、百般羞辱服务对象。拖拉机手因嫌村民招待不周,竟然诓骗十几个农民站在尘土飞扬的大犁耙上“压犁铧”泄愤,差点闹出人命来。校车司机小李师傅,因整日接送一群“傻帽”知识分子而感到愤愤不平,为了出出心中的恶气,竟然每天以进加油站加油为名,大冬天驱赶教师下车,在寒风里挨冻等候。小袁师傅则更霸道,只要不是和他同一个“阶级”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乘他的车,都得噤若寒蝉,若有一人不小心说了句话,他就会路边停车,破口大骂。一车秀才,被他骂得瑟瑟发抖。就连校长见了小袁都要躲避,若是领导敢批评他,他就怀揣利刃,将车横在校门口,让整个学校窒息。《麻醉药》叙述医院里发生的荒诞事。作者在京都大医院里做腿静脉曲张“小手术”,因为没及时送上“红包”,胖大的男医生竟然两次让麻醉药“不起作用”,“我”几乎被割昏在手术台上。医者如此不仁,不仅疼在伤口,更痛在心上。《磨刀人》中的磨刀师傅,最底层的手艺人,竟也不讲诚信,偷奸耍滑小聪明,成功欺骗了非常信任他的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相信底层人的善良,其结果反被其私底下看成“傻叉”。
解构袪魅。主要收集在“野草热风”“三闲二心”部分。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启蒙,而启蒙则必然会碰撞一些伪范式和假典型。这里的袪魅解构,不仅有对名实不符的权威、典范、知识的消解之意,同时也有对假崇高真投机且作君子状人物的戏谑,特别是对一些名人的评价,有些“不留面子”。《偷》从偏远家乡一则民间传说“洋鬼子偷宝”切题,不是从发生学,而是从民间传说文本呈现出的中国“互文性”特征说开去,解读当代社会“阴谋论”盛行背后的文化心理。也许由于作者是反邪教专家的缘故,对于一些盲目崇拜民间神秘文化的反智现象,文章持开放性解构批判态度。《民科》列举了当代著名“民科”专家的种种劣迹,通过揭穿其荒唐的治病“秘方”“绝活”,警醒世人坚硬如铁的科学理性常识的重要性。《西医、中医和巫医》则以自己医院看病的经历,理性分析西医、中医、巫医的“功能”,警示世人切莫上江湖郎中的当。《孔子和我都没有当上大祭酒》挖苦那些学问平平却异常自信的“学者”。他们一朝披上官衣儿,就不自觉地开启“自我神化”的阀门,即使犯了常识性错误,为了颜面也绝不承认。他们犹如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笔下那个长着三根魔发的侏儒“小查克斯”,“大学祭酒”的名号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魔衣”。《司马左右》《罪人张学良》两篇,作者以锐利的目光直刺名人性格的蜂腰与肯綮,通过解构名人头顶的光环,祛除人们对权威知识的盲目崇拜心理。《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是杂文集的最后一篇,该篇通过大历史场景叙事,直刺那些智商堪忧、脱离现实,但又非常固执自信,常以永远正确且无比高尚的清流过激之语危害国家的“妖孽”与“乡愿”人物。
在艺术手法上,杂文集《南腔北调》也有其独到之处,以现代寓言故事方式表现主题,针砭时弊,启迪读者。与小说的情节取胜不同,杂文更讲究表达的睿智、语言的穿透、说理的无痕。该散文集在叙事表达与语言使用两方面皆有建树,熟练使用多种章法、技法,增强文本话语蕴含的深度与思想表达的硬度,以夸张、变形、象征、反讽、幽默、拼贴、戏仿、组接、陌生化、语言流等技法征服读者。既有后现代叙事风格,也有鲁迅笔法的影子,满足了读者对辣味语言体验的快感,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