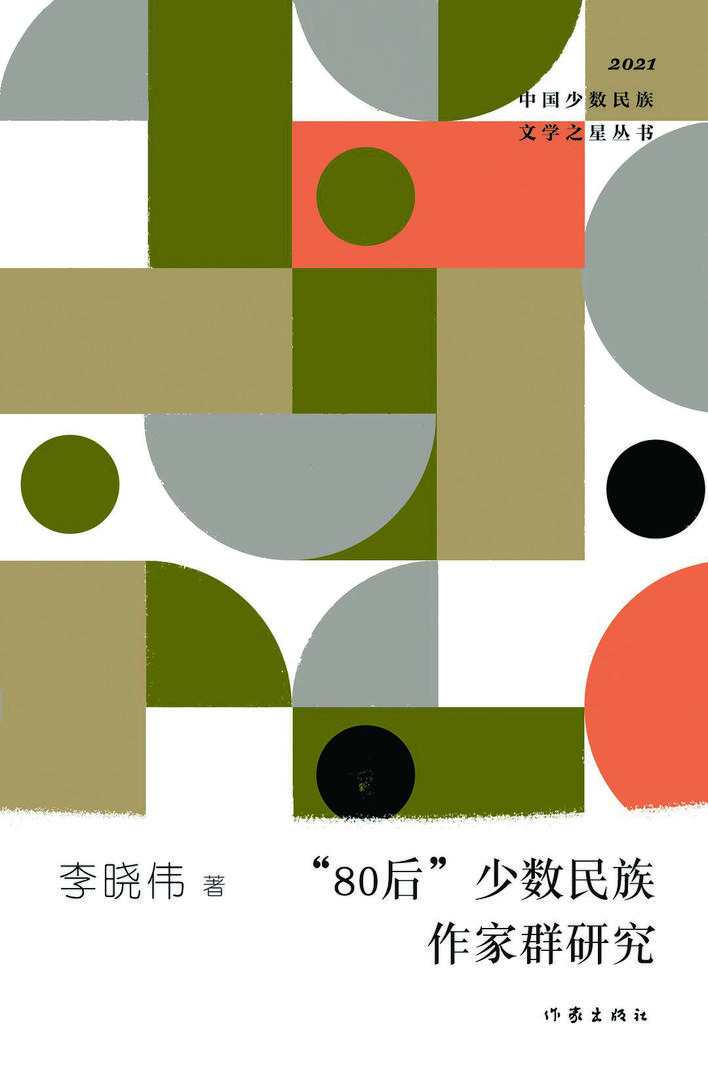2012年的夏天,我正在金陵攻读博士学位,古都如浪般的郁热推着我时常游走在学校附近的旧书店以及各种古迹、遗址中,去寻访幽幽的静谧,而伴随着湿热空气不期而至的,还有如何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棘手问题。茫然无措中,我只得到图书馆漫无目的地乱翻书,期盼着能在书海中寻觅得一些灵感。
那时学院还未搬迁至仙林校区,我差不多每天都会优哉游哉地从北大楼前晃荡而过,去文科楼的文学院图书馆乱翻书,就是在这里我偶然间翻阅到了几本白族诗人晓雪的诗集。一是因为诗人名字里透着的浪漫吸引了我,另外也因为自己和作者同为白族的关系,于是带着好奇心取下这几本诗集开始阅读。正是这次随心的翻阅,形成了我在博士期间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简论晓雪诗歌创作中的乡恋书写》,这大概可以算是我走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吧。虽然这些看似边缘的阅读并未成为我最后论文选题的方向,却为我之后学术道路的延续做好了铺垫。在这之后,我带着初步的学术兴趣,开始去翻阅和少数民族相关的文本,在随后的阅读中,研究的思路与目标也逐渐清晰起来。
接下来,达斡尔族的作家晶达在《边疆文学》上发表的散文《最后的莫日根》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在散文中,晶达写到了那些逐渐散失在时光中的达斡尔的“莫日根”(猎人),她文字中的深情与无奈让我触动颇深,这是与那个已经被“话题化”了的名词——“80后”完全不同的思考和表达。作为一个同辈人,我突然意识到,在市场与作家们“共谋”的叙述中,“80后”已经被固化,可是在那些被共享的文学共性之外,实际上还有着许多极富活力的个体或群体存在。对于我自己而言,在这种共性中去发现新的文学风景,可能会是我最有意义的学术维度,这些都是和那个由于身处其中而被自己忽略了的少数民族身份相关联着的。
于是,从这样的代际视野出发,我开始了以同代人的角度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察,诸多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了我阅读、交流的对象,如包倬、马金莲、何永飞、向迅、李达伟、晶达、张伟锋、杨蓥莹、英布草心……
这些作家看似零散,实际上是能够围绕他们特有的少数民族身份来构建起一个特别的作家群体的,即我所谓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这一“群体”可以从“大群体”—“小群体”的对应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整体的“80后”作家在以代际为依据的命名下,呈现出了大的群体特征,与之相对,在这一大群体之下,我们又可以以少数民族身份为坐标来找到一个小的群体,即“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另一方面,这样的“大”—“小”又能理解为大群体意义上的某一个或数个民族的“80后”作家,以及小群体意义上的以地域性为特质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在他们的文字中,我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们文学世界的多重维度,他们既保持着对现实的热切关注,也不忘对内向世界的深度开掘,胸怀讲述民族历史的雄心的同时又不乏有意味的文学试验。在新世纪的文学场域中,这就是一支新生的文学力量,对他们文学创作的研究,显然对于透视整个文学场域以及展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典型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构想之下,我开始了以“80后”少数民族作家为核心的思考和研究。学术构想产生于我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淳朴之情,但将之付诸学术研究的实践之中,却也需要更多深入的思考。因此,以同代人视角来进行文学观察,固然有着很多便利性,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将自己融入到研究场域之中去。“少数民族”与“研究者”,这两个身份也就成为了自己在做这一作家群研究(或者说是写这一本书)时的两个立足点。
作为一个“80后”的少数民族,面对这些同代作家时,我想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在场者。我与这些作家们共享着相似的时代情绪、乡土记忆和城市经验等,所以他们的作品首先打动我的,除了那些文学本身的质感之外,就是我们都曾有过的经验,如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自然有义务为这样的同代书写来记录。作家们用自己的笔将时代和个体的种种编织进文字的针脚之间,我亦用文字来观察、记录这些别样的文学风景,这样的研究或许能够少一些距离感,而多几分在场的温度。
而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亦看重研究者与作家之间的关联,即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因为作为文学生态场域中的重要一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对时下文学现象作出描写,描绘出“文学世界”的当下状况,可以说是作一种文学史的积累;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也更具时效性的,是以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来实现对当下文学趋向的引导,文学批评的重要职责正在于此。因此我力图以追踪式的文学现场观察,来保持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状态,希望能够与作家在一种互动的交流、对话中共生发展,并且推动作家的创作。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股文学力量的回应。同时,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与批评界关注不多这样的不平衡现象也频频被提起,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汉族学者较少,而少数民族批评家也不多,这部书可以看作是一次研究的尝试。
书后所附的系列访谈也是基于“在场者”和“批评者”的考虑而设计的,我试图通过这样的对谈,来为自己在文学现场的观察做一个注脚。略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作家的访谈没能进行,而且已完成的对话没有能够以面谈形式呈现,最终是以“问题+回答”的形式来完成的,虽有缺憾,但也未尝不是为之后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这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们以其极强的文学生长性,逐渐获得了认可。一本书的写作虽然画上了句号,但研究还在继续,作家们身上更多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对一种“在场”研究的持续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