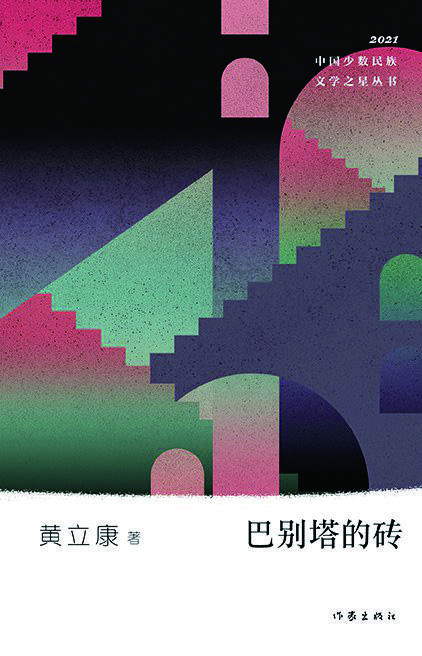像灯塔,作为一次航行的停顿,《巴别塔的砖》记录着我来时的航道和心路。在写这篇创作谈时,我其实早已再一次心怀感恩地启航,并且已探索许久,前方是未知之路,身后的“巴别塔”上传来的微弱灯光,作为定位的坐标,将会在写作旅途中给我力量和方向。
“写了什么”,以及“以后要写什么”,这是我想在这篇创作谈中简单谈论的两方面内容。这篇创作谈的写作,我也将按照《巴别塔的砖》中一以贯之的风格,为它套上一个隐喻性的结构,即“巴别塔的内与外”。“巴别塔之内”有什么?而在“巴别塔以外”,下一步,我又将去往何方?
先来谈一下“巴别塔之内”。我的写作以散文为主,从2016年第一次在《边疆文学》上发表散文《江边风物志》,到今年《巴别塔的砖》入选“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这本散文集收录了我近年创作的大部分散文。其中,“A面”共收录9篇散文,书写民族历史和地域文化;“B面”收录8篇散文,记录个人成长和人生记忆。
如果按照时间来排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散文创作的成长与变化、追索与确立的过程。从最早书写故乡风物、抒发田园乡愁的习作,到今年尝试历史题材、聚焦当下生活的表达,我努力将自己的写作推向开阔、复杂的层面,更大程度地呈现我所关注的世界的风貌。《巴别塔的砖》所呈现的,不仅仅只是我的写作状态,它是我与世界的联系,是生活状态和内外思辨的一小块结晶,而这小块结晶也浓缩地隐喻了我人生的脉象:我的农耕身世,现在居守城镇的生活,以及无可回避地要面对城市化生活挑战的未来。
故土风物、家族往事、民俗历史、个人心路、时代风貌,在《巴别塔的砖》中,我尝试着不断变换自己的写作题材,但早在写长篇散文《房间》时,似乎就已经预见性地架构了我这本散文集的结构。
因为篇幅原因,我将《房间》拆分为《A面房间》《B面房间》两篇散文,分别发表于《民族文学》和《青年文学》。《房间》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地分为“A面”“B面”两部分,以“磁带”和“歌曲”的形式呈现不同内容。这两“面”,像山的两侧,实为一体,却又各自独立。从此,我的散文写作就被划分为两个大板块,在力求“切入口小,结构精巧,层次丰富,气脉相通”的创作理念的基础上,一半写民族和现实,一半写自我和内心。例如,《抄木氏土司诗》便是“A面”板块的最后一篇,这篇散文是我对历史题材的第一次尝试,以“中华古诗”为切入点。写民族历史和时代呼唤,和“A面”收录的其它散文气脉相近。《抄木氏土司诗》与早期“风物志系列”的写作构思有相似处,都在呈现滇西北民族、地域、历史、文化的特色。不同之处在于,“风物志”的构思,是对田园牧歌消逝的哀悼,而《抄木氏土司诗》的写作,我将“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概念,融入到对木氏土司爱国情怀、边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纳西文化与中华文化融通的书写中。我的写作从云端降下,与当下时代有了紧密联系,有了地气,这是我在《巴别塔的砖》中的成长。
在A面中,我也尝试着对民族文化进行散文式的探讨。作为一个民族作家,我一直以“跨越者”的身份,借助中华文化看待纳西文化,依靠纳西文化去理解中华文化。不只如此,我生活的滇西北有多个民族在此世代聚居,文化多元交织,源远流长又互鉴共融。这块多元文化区域,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当我借助汉语表达时,我其实是这片山川风月的“翻译者”。我在相异的文化间,寻找相同之处,并试着以“信、达、雅”的标准,以散文的方式翻译而出,让更多人知晓生活在这方故土家园中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深远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与时俱进、进化蜕变,激发出丰沛绵长的生命之力。在文化基因“互译”时,我时刻让自己警惕,切忌盲目传承和歌颂。在多元文化中求同存异时,要贴近“人性”,要关注“现代性”。所有优秀文化都暗含着现代性,任何时代、任何族群,都要处理和时间、空间的关系,以确定我是谁、来自何处、要去何方。好在“传统”以其稳定的内核,为我们的写作带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头”“迁徙”“生死”“信仰”“时间”,这些都是每个人在过去、当下、未来所需面对的疑问。在“A面”的《风中的声音》中,我将声调和图腾融合,想要谈论的是纳西族传统中的时空、情感、信仰等观念,我将这些观念“翻译”成散文,让读者能够了解到纳西族的表与里、传统与现代,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巴别塔的砖》中有时代记忆、地域痕迹、民族特色,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和人心。人和塔的关系,本质上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本散文集中,我描写了许多与这个时代有交集的人。有我奋战于脱贫攻坚一线的同事,有红军长征过丽江、迪庆时的人与事,有我当乡村教师的姐姐和她的山区学生,有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巨变的边疆人民,有不断进取、去往大城市追逐梦想的年轻一代。我试着以我的执迷和语调,来讲述他们(或者说是我们)的悲喜和深情。
下面我要谈谈“巴别塔”的“B面”,这一面,我淡化了地域与民族的色彩,写得更自由,试着去探寻一个普通人在外部世界映照下的内心世界。这一面也连接着我未来的写作,关联着我会将写作视野聚焦于何处。在B面中,我已经摸到了我未来写作的脉搏,“巴别塔以外”是我将要去往的地方。
“B面”像一个万花筒,是我成长的心灵记录,记录我的童年往事、青春记忆、亲人别离和生活随想。散文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实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都是复杂而神秘的。即使是写一首短诗,都有可能调动你所有的知识储备、情感体验、想象力和感知力,短短一瞬,就能融汇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你走过的所有路。“B面”的写作正是这样,卸去我纳西族人的身份、云南人的标识,我只是一个个体,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世界,自言自语。
我是个乡村生活经验较少的人,城市生活的经验也是寥寥,我熟悉的是城镇。所以,当我回头看这一部分“心灵记录”时,我的视角都是一个小城镇人,我的经验也都是城镇生活的经验。可以说,我成长、生活其中的独一无二却又雷同相似的小县城,便是我写作的布景,笔下的事物也都带着城镇气息。《巴别塔的砖》里的看动物、摸纽扣、搓衣料,这是及物的细节,这些小动作连在一起,连成“通往城市的道路”,从一个小城镇人的视角,对比城镇与城市,呈现城市的开阔和幽深。《雪孩子》里“闻”这个动作,勾勒出一种小城生活的常态和普遍经验。
但我的生活并不是孤立在城镇。因为“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我常常需要去到乡村,有时候也需要出差到大城市去。我们的父母辈(也包括我们),通过奋斗来到城镇或是去往大城市生活,并在另一方天地里播种收获,那是一个时代走向。城市是大部分人将要面对的命题,我想,这是一个兼具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话题,所以我将会把未来的书写聚焦到生活在城市、城镇中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喜和命运上。而我也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们,有的开始返乡生活,这又是另一种未来的号角,我也会记录这一变化。
十分荣幸,我的散文集《巴别塔的砖》能够入选2021年“少数民族之星”丛书,作为一次停顿,我希望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新起点,我期待新的挑战和收获。一路走来,感谢文学相伴,感谢师友帮助,无以为报,自当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