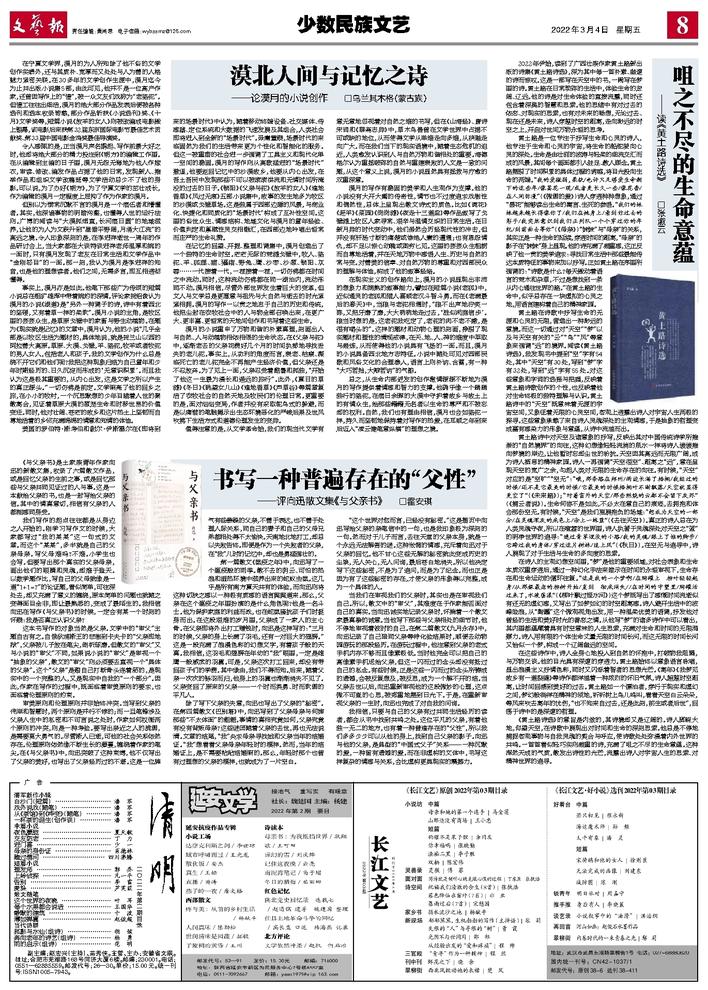在宁夏文学界,漠月的为人所知除了他不俗的文学创作实绩外,还与其质朴、宽厚而又处处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紧密关联。在3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漠月迄今为止共出版小说集5部,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位高产作家,还曾因写作上的“慢”,被一众文友们戏称为“老骆驼”。但慢工往往出细活,漠月的绝大部分作品发表后便被各种选刊和选本收录转载,部分作品斩获《小说选刊》奖、《十月》文学奖等,短篇小说《放羊的女人》则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该电影后来获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令人感佩的是,正当漠月声名鹊起、写作前景大好之时,他却将绝大部分的精力投注到《朔方》的编辑工作里。在从编辑到主编的日子里,漠月无怨无悔地为他人作嫁衣,审读、修改、编发作品占据了他的日常,发现新人、推举作品和组织文学改稿班等文学活动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可以说,为了办好《朔方》,为了宁夏文学的茁壮成长,作为编辑的漠月一定程度上屈抑了作为作家的漠月。
但别以为惯常沉默不言的漠月是一个落伍者和懵懂者。其实,他深谙事物的明暗沟壑,也懂得人世的运行法则。广博的阅读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域滋养,让他的为人为文跃升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高远之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李进祥逝世一周年的作品研讨会上,当大家都在大谈特谈进祥老师温厚和婉的一面时,只有漠月发现了老友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金刚怒目”的一面。那一刻,我认为漠月是李进祥的知音,也是他的理想读者。他们之间,无需多言,即互相透彻懂得。
事实上,漠月亦是如此。他笔下那些广为传颂的短篇小说总在粗犷雄浑中带着婉约的深情。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漠月的小说《湖道》是“另外一种调子的诗,诗中有着西北的坚硬,又有着草一样的柔软”。漠月小说的主角,是牧区里的芸芸众生,是草原戈壁中的家畜与野生动植物。在题为《现实就是记忆》的文章中,漠月认为,他的小说“几乎全部是以牧区生活为题材的,具体地说,就是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大高原。草原、大漠、戈壁,羊、骆驼,牧羊或者牧驼的男人女人,包括老人和孩子。我的文学创作为什么总是绕不开它们和他们呢?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的、日久沉淀而形成的‘无意识积累’。而且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从内心出发,这是文学之所以产生的真正源头。”一切仿佛是前定。文学照亮了他的回乡之旅,在小小的牧村,一个沉思默想的少年目睹着人世的聚散离合,见证着草原大漠的葱茏生命和时移世易的价值变迁。同时,他对壮阔、苍茫的故乡和这片热土上坚韧而自尊地活着的乡邻充满绵绵的情意和知情的体恤。
美国的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认为,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及其组合,人类社会即将进入到全新的“场景时代”。毋庸置疑,场景时代的来临固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为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但这一被重塑的社会进一步强调了工具主义和现代化单一空间的稳固。漠月的写作则从高歌猛进的“场景时代”撤退,他要返回记忆中的沙漠故乡,他要从内心出发,在吾土吾民中发现那些不可以被滚滚洪流和无情时间所淹没的过去的日子。《锁阳》《父亲与驼》《放羊的女人》《遍地香草》《风过无痕》五部小说集中,故事的发生地多为牧区的沙漠或戈壁草场。这是独属于西部边陲的风景,与商业化、快捷化和同质化的“场景时代”构成了互补性空间。这里的俗世众生、情感结构、地域文化与漠月的童年经验、价值判定和禀赋性灵交相融汇,在西部边地吟唱出恒常而庄严的生命礼赞。
在记忆的回望、开掘、整理和调集中,漠月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生命时空。茫茫无际的荒滩戈壁中,牧人、骆驼、羊、狐狸、猫、獾猪、野兔、鹰、沙枣、沙葱、锁阳、苁蓉……一代接着一代,一茬接着一茬,一切仿佛都在时间之中流动。同时,这种流动仿佛都在同一湖泊内,流动形同不动。漠月相信,尽管外部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但文人与文学总是更愿意与祖先与大自然与逝去的时光紧紧相拥。漠月的写作一以贯之地忠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他把尘封在农牧社会中的人与物全部召唤出来,在更广大、更丰富、更恒常的天地间创作和书写着这些生命。
漠月的小说重申了万物和谐的朴素真理,刻画出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相依相偎的生命状态。在《父亲与驼》中,逐渐老去的父亲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执拗地寻找丢失的老儿驼。事实上,从功利的角度而言,衰老、枯瘦、濒临死亡的老儿驼完全不再能产生经济价值,但父亲还是不忍放弃。为了见上一面,父亲忍受着酷暑和孤独,“开始了他这一生最为漫长和遥远的旅行”。此外,《夏日的草滩》《冬日》《眺望女儿山》《遍地香草》《芦草谷》等篇章复活了农牧社会的自然天地及牧民们的伦理日常。更重要的是,面对汹汹变局,作者并没有采取鸵鸟式的躲避,而是以痛惜的笔触揭示出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后果及世风吹拂下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发生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学革命始,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有意无意地忽视着对自然之维的书写,但在《山海经》、唐诗宋词和《聊斋志异》中,草木鸟兽曾在文学世界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从而使得文学从单维走向多维,从狭隘走向广大。而在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中,随着生态危机的迫近,人类愈发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海德格尔认为重拯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是一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漠月的小说显然具有拯救与疗愈的双重深意。
漠月的写作有稳固的美学和人生观作为支撑。他的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传奇性,情节也不过度追求戏剧性和偶然性,总体上呈现出散文诗式的质色。比如《谎花》《赶羊》《菜园》《岗岗滩》《夜走十三道梁》等作品叙写了戈壁滩上牧区人家寻常、艰辛与温情交织的日常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动中,他们虽然会历经现代性的冲击,但并没有肝肠寸断的痛楚或惨绝人寰的遭遇;也有恩怨情仇,却不足以惊心动魄或图穷匕见。这里的芸芸众生粗粝而自尊地活着,并在天地万物中感悟人生、历史与自然的常与变。对善美的信奉、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和对西部民众的理解与体恤,构成了他的叙事经络。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上,漠月的小说显现出丰沛的想象力和娴熟的叙事能力。譬如在短篇小说《老狐》中,近似通灵的老狐和猎人喜顺老汉斗智斗勇。而在《老满最后的春天》中,当狼与老驼相遇时,“狼不出声地狞笑一阵,又把牙磨了磨,大大咧咧地走过去,‘胜似闲庭信步’。狼当时想的是,这老驼我吃定了,老驼的肉不老不嫩,是很有嚼头的”。这样的题材和动物心理的刻画,挣脱了现实题材和理性的清规戒律,在天、地、人、神的维度中萃取与凝练,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具有飞扬的一面。而且,漠月的小说具备西北地方志特征。小说中随处可见对西部民歌和风俗文化的合理渗入,语言上则朴讷、含蓄,有一种“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气韵。
总之,从生命内部迸发的创作激情源源不断地为漠月的写作提供着情感和智力的支撑。他确乎像一个踽踽独行的骆驼,在落日余晖的大漠中守护着故乡与故土上的有情众生,给那些籍籍无名者以生命的尊严和不被忘却的权利。自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漠月也会如骆驼一样,持久而坚韧地保持着对写作的热爱,在耳顺之年到来后迈入“凌云健笔意纵横”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