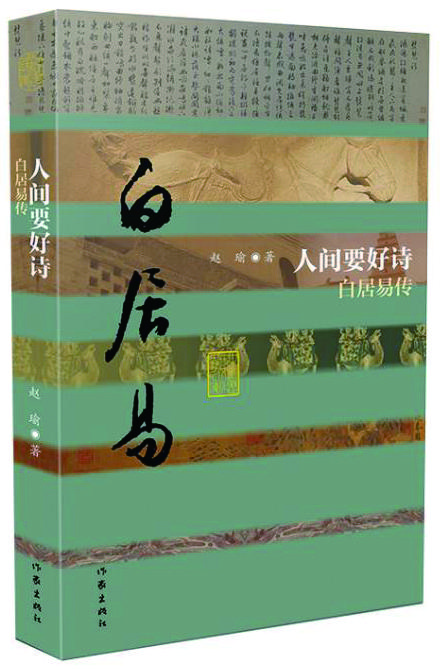为古代大文人作传,对作家要求极高。作家的知识水准和对天道、人道的认识之深度直接决定作品之程度。深者所见自深,浅者所见必浅,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参与《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写作,在创作交流会上三次遇到赵瑜先生并有所交流,知道他对于白居易的许多敏感问题都有过思考,对于其创作的《白居易传》便有期待。该书出版后,赵瑜先生在第一时间便快递给我一册,得以先睹为快,便一口气读完。掩卷深思,颇多感怀。
二十几年中,我先后在沈阳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中文系讲课,讲授课程主要是唐宋文学,而以唐代为主,故对唐代文人关注最多,对王维、韩愈、李商隐下功夫尤大一些。韩愈与白居易同代,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白居易与这几位关系都很密切,且都有诗文交往,这样对白居易接触很多,且讲课是必讲内容,对其生平大事基本了解,故自然带着挑剔的眼光去阅读和思考。
我很少如饥似渴般读书,但阅读此书可以这样来形容。因为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传记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作品是否有硬伤,有无明显错误。二是关于传主生平的大事是否都写到了,有无故意回避或大的遗漏。关于白居易的爱情经历、婚姻生活,他与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关系,以及他是如何在牛李党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官场和人际关系中独善其身等问题,都是我所留意的。随着阅读的展开,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了回答,而且颇为合乎情理。
对于白居易的爱情悲剧,作品交代得非常清楚,其实这是很难处理的,但作者娓娓道来,线索清晰,从缘起提笔,写到中年之后的相思与最后一次的会面,令人叹惋唏嘘。作者并没有归罪于封建礼教,也没有过多谴责白居易母亲,而是采取很温和的立场,好像母亲和儿子都没有错,但也透露出白居易母亲性格的执拗和对于儿子的不理解与不尊重。白居易是很无奈的,正因如此,白居易在爱情方面压抑得太久太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却到36岁还未能婚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显得有些另类。他爱的湘灵母亲坚决不认可,母亲选中的人又非他所爱,母子就这样僵持着。而在他36岁做周至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三人敞开胸怀议论古今,话题集中到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上,才约定由陈鸿写《长恨传》,白居易写《长恨歌》。其实,这只是外因,是写作《长恨歌》的缘起,但白居易把这首长诗写得如此娓娓动人,令读者回肠荡气,也是因为他本人感情的全部投入,作者需要先感动自己然后才可以感动读者。因为他对湘灵有着刻骨铭心的爱,而又以悲情告终。这对他是锥心刺骨的痛,人的初恋是最美好、最深刻而无法忘却的。他把自己对湘灵的思念情怀移植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上,才会写出“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段令人百读不厌、读罢就想背诵出来的精美诗句。白居易是借唐明皇思念杨贵妃来抒发自己对湘灵的刻骨思念,读者甚至可以感知白居易当年写完这段文字时两眼晶莹的泪花。或许,正是因为写完《长恨歌》排遣释放了在爱情方面受到的巨大伤痛,才使这种情怀得以缓解,进而在次年结婚。这样的描写是入情入理的,他的另外一首获取极高知名度的长诗《琵琶行》也是对女性在爱情方面受到极大伤害的深度同情所抒发的感伤,其间有自己仕途坎坷的感伤,也隐喻着对于湘灵的怀念和感伤。
对于元白关系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求实精神,而这正是传记作者最需要的。元白关系是无法避开的重头戏,关于白居易是否写过《论请不用奸臣表》而与元稹断交时,他首先引证白居易研究专家吴伟斌先生对此事的考证辨析,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说得非常有分寸,“说白居易愤而撰写奏章与元稹绝交,可能性非常小。”类似这种有关生平大事,赵瑜都是先概括介绍学术界主流观点,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就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介绍前人成果时,一一注明出处,表示对其他学者的尊重,这种学风颇令人敬重。他书中先后借用过当代学者王拾遗、谢思炜、尚永亮等人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书的学术品位。王拾遗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过《白居易传》,是白居易研究的前辈学者。谢思炜和尚永亮都是我们同代人,谢思炜在白居易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尚永亮在贬谪文学方面成就斐然。这几位都是我熟悉并很敬重的学者,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之学风踏实,为人坦诚,值得敬佩。
另值得一提的是,赵瑜是报告文学作家,他把创作报告文学的风格代入到《白居易传》的写作中,给人一种此书即使在唐代出版也可以被读者接受的写实感。这对于人物传记写作而言,颇为难得。赵瑜虽然不是专业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但本书对唐代文化精神以及对白居易生平的把握上,是很能经得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