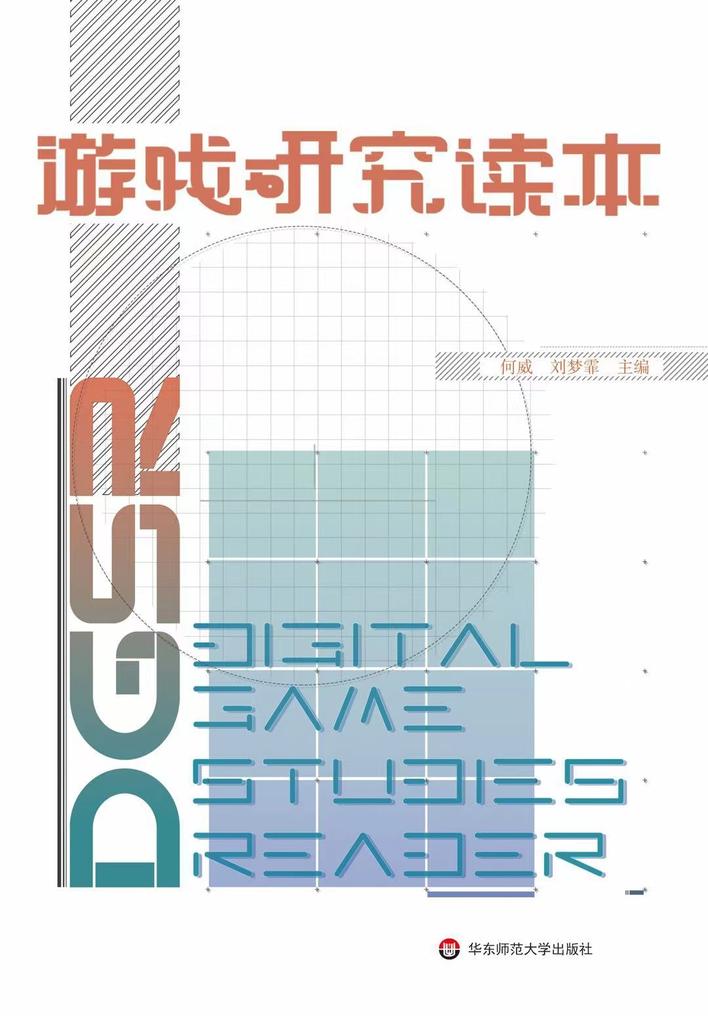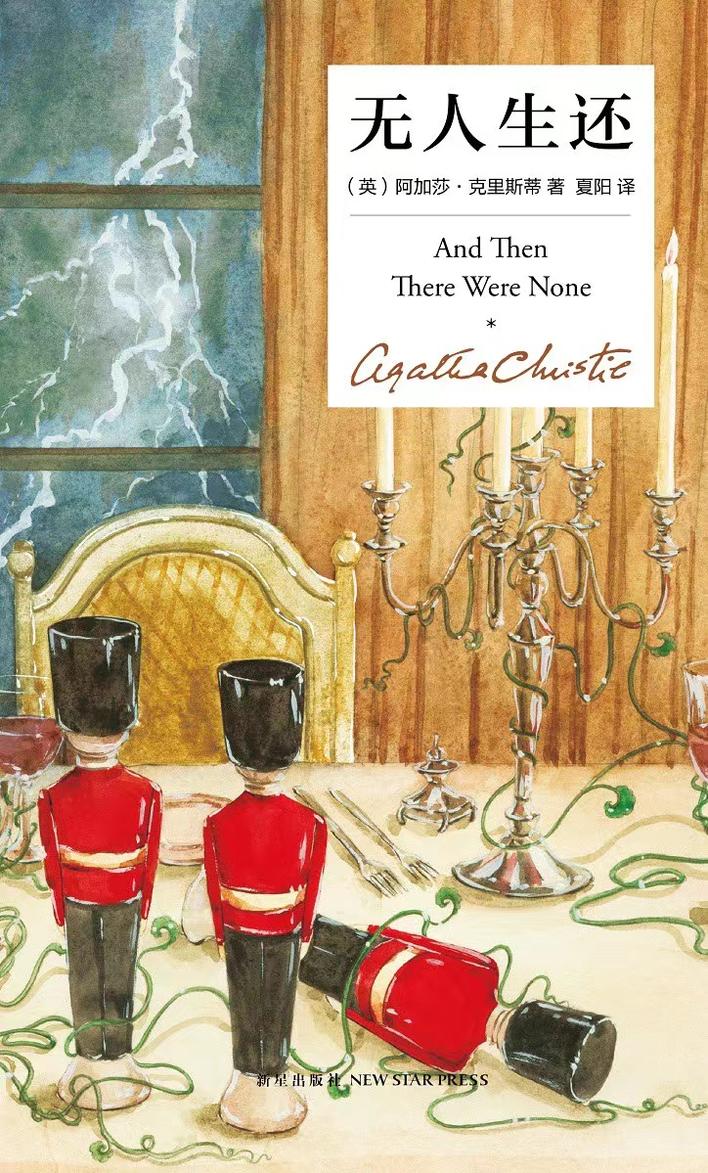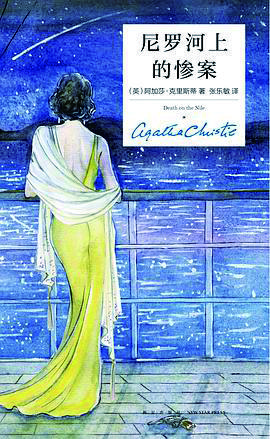现如今流行的“推理本”几乎大多是采取“阿加莎模式”,甚至于直接就是某种“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变体,这其中既因为封闭空间和有限嫌疑人等类型特征更利于游戏本身的设计和进行,也源于“阿加莎模式”中侦探破案更多依靠访谈与对话——而非追捕与搏击。访谈与对话又和剧本杀所内含的现代社交属性在形式上深度契合,而这也正是剧本杀在网上经常被戏称为“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的原因之一。
从更根本性的层面来说,不同“推理本”中不同的故事场景与剧情设置,为吸引玩家提供了某种“求新”“求异”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属性,但作为“推理本”中某些固定的游戏类型“程式”,却反过来保障了玩家在游戏进行中的“安全感”和基本类型期待。于是,剧本杀中的“不同”与“重复”就构成了一组吸引玩家的有趣悖反。
剧本杀作为当代年轻人非常热衷的社交娱乐方式之一,已经发展出了诸如情感本、阵营本、酒本等不同类型的游戏玩法和沉浸体验。本文所聚焦的讨论对象还是最为经典的硬核推理类剧本杀(后文简称“推理本”)。一方面,“推理本”通常被认为最初起源于欧美聚会游戏“谋杀之谜”(“Murder Mystery”),后者则以其悬疑性、社交性和游戏CNP(come and play)机制而广受欢迎。另一方面,“推理本”又和推理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将其视为推理小说发展趋势延长线上的某种泛文化现象。
“阿加莎模式”:封闭空间与有限嫌疑人
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最经典的模式当属柯南·道尔所开创的“福尔摩斯模式”,福尔摩斯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侦探”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侦探福尔摩斯除了被认为“他是一架世界上最完美的用于推理和观察的机器”(《波希米亚丑闻》)之外,还有着“善用棍棒,精于刀剑拳术”(《血字的研究》)的人设。而福尔摩斯所破获的案件也多半具有惊险小说的传奇色彩,比如其中大多数短篇都是以“The Adventure of……”为题,便是一个例证。此外,小说中福尔摩斯和助手华生调查案件与追踪凶手的地理空间范围几乎遍布整个伦敦城,乃至英国各郡县乡村,马车、自行车、火车和快艇等都是辅助其出行并拓展其查案地理空间半径的重要交通工具。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必须用更为传统且经典的“侦探小说”概念来指称“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而不宜用后来的“推理小说”这一说法,因为在福尔摩斯破案的过程中,除了逻辑推理之外,搜索、追捕、格斗、枪战等手段都经常被反复使用,即“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具有更大程度的行动性特征。
随着欧美侦探小说发展至“黄金时代”——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埃勒里·奎因为代表,这一小说类型大概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转变趋势。一是在对于案件情状的设计上,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多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区域——如一幢别墅(《Y的悲剧》)、一艘游轮(《尼罗河上的惨案》)、一列火车车厢(《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者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无人生还》)——内出现杀人案或连环伤害案件,而且这一区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都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即可以概括为“封闭空间内的有限嫌疑人”。二是侦探在破案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更少的“行动力”,毕竟无论是“身材矮胖”的侦探波洛,还是年近七旬的马普尔小姐,抑或是患有耳聋的退休莎剧演员哲瑞·雷恩,都不具备直接抓捕犯人的身体能力,他们破案所依靠的,更多是“小小的灰色细胞”(波洛)。粗略来看,这些小说似乎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推理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想象。当然,“推理小说”取代“侦探小说”这一名词转变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日文改革历史和汉语翻译历程,此处不赘言。
简言之,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大致存在着一个由“福尔摩斯模式”向“阿加莎模式”转变的趋势,即由动作惊险转向逻辑推理、由全城追捕转向封闭空间、由“异域来的邪恶凶手”转向“在场人人皆有嫌疑”、由凸显侦探自身的能动性转向“重视犯罪事件的谜的复杂性”(考维尔蒂语)。而后世很多广受欢迎的推理文化产品与文化现象也都有着明显的“阿加莎模式”的影子,比如早期《名侦探柯南》中的大多数剧集,以及现如今流行的“推理本”也显然是在“阿加莎模式”的延长线上符合并继承了侦探小说的这一发展趋势。
“人人皆有嫌疑”:悬疑感的追求与限度
毫无疑问,现如今流行的“推理本”几乎大多是采取“阿加莎模式”,甚至于直接就是某种“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变体,这其中既因为封闭空间和有限嫌疑人等类型特征更利于游戏本身的设计和进行,也源于“阿加莎模式”中侦探破案更多依靠访谈与对话——而非追捕与搏击。访谈与对话又和剧本杀所内含的现代社交属性在形式上深度契合,而这也正是剧本杀在网上经常被戏称为“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的原因之一。
当然,“推理本”又和“阿加莎模式”的推理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不同。比如对于一般的推理小说而言,侦探通常是小说的绝对主角,其他几个嫌疑人也存在着彼此间戏份强弱上的区别,即所谓首要配角、次要配角或“打酱油”人物。但对于“推理本”来说,DM(主持人)的角色身份固然重要,并且关系到对整个游戏进程与节奏的把握,但我们很难说DM就是一场剧本杀的主角,甚至对于一场合格的剧本杀而言,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区别。因为对于每一名玩家来说,他们都需要感受到同样的游戏参与度和沉浸体验感(没有玩家是花钱来当“路人”的),而这种每一名玩家对于游戏参与感的追求也就抹平了游戏过程中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差别,即“推理本”必须在游戏过程中造成“人人皆有嫌疑”“人人嫌疑相当”的局面,但这并不是一般推理小说创作中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每名玩家“嫌疑度”与“参与感”的平衡性追求,看似是对“推理本”的故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其同时也限制了“推理本”自身展开的可能。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平衡每位玩家的嫌疑程度,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诸如“建立隐藏人物关系”之类的手法,建立隐藏人物关系的好处一方面在于容易平衡不同玩家的嫌疑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有效拉长整个游戏的进行时间,即在完成“寻找真凶”这一最终任务的过程中,同时揭开其他几个人物身上所隐藏的秘密,将“大任务”与诸多“小任务”相互嵌套、组合。但这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即是人物关系揭秘与反转的模式化,比如三角恋情、同父异母的兄弟、失散多年的亲人、车祸失忆、表面恩人实为仇人、“三刀两毒”(多人都对“死者”施加杀手,但最后只有一人的行为直接致“死”)等等,都是在各种“推理本”中被“用滥”的套路。
与上述因追求建立隐藏人物关系而产生的游戏情节套路相类似的情况是,很多“推理本”为了增强整个游戏的悬疑感并保持一定的游戏时长,因而会在游戏中间部分或偏后半程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情节大“反转”,但追求这种“情节大反转”的手段却经常显得比较有限,无非是催眠幻觉、灵魂交换、虚拟现实、时空穿越等等,其概括起来无非就是通过颠倒整个游戏场景设定的虚/实想象来进一步推进游戏情节本身的曲折性和复杂程度,即完成一种“暴风雪山庄”+科幻/魔幻/玄幻的情节组合套路。
类型“程式”与游戏机制
既然剧本杀在建立人物隐藏关系与完成整体性情节反转上的手段无非几种固定模式,那么它作为一种大量依靠“粉丝玩家”与“回头客”的线下体验型游戏是如何保持其自身的吸引力的?在这里,尤其对成熟玩家而言,具体剧本的故事时空设定其实并不重要,无论是古代宫斗,还是民国谍战,无论是日本校园,还是未来科幻,这些花样繁多的故事与场景只不过是一些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壳,而作为核心游戏机制的人物隐藏关系与整体性情节反转在不同的剧本中却往往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对于一名有着一定游戏经验积累的“大神”玩家而言,玩一局新的“推理本”,表面上看是遭遇了不同的故事场景,实际上却是在重复体验着同样的游戏机制。
有意味的是,这种不断“重复”的游戏机制可能正是剧本杀吸引“粉丝玩家”与“回头客”的关键之所在。一方面,相对稳定且重复的游戏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即防止有玩家中途“自爆”而导致游戏“翻车”(游戏中途无法进行下去),或者是尽量避免角色扮演上的“尬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地方则在于,“推理本”中这种相对固定的游戏机制,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作为类型小说之一种的推理小说所具有的类型“程式”。所谓类型“程式”,是美国通俗文学研究者考维尔蒂在研究欧美古典侦探小说时所提出的概念,他虽没有对“程式”做严格定义,但其大体上意味着一组稳定的、重复出现的、与内容相关的形式元素。比如早期侦探小说中的倒叙结构、“华生视角”、“倒数第二章挑战读者”,或者是惊险电影中的“双雄对峙”“死里逃生”(a narrow escape)与“最后一分钟营救”(Griffith's last minute rescure)等等,就都是很典型的小说类型“程式”。而在小说、电影或游戏“叙事”过程中采取某些固定“程式”的好处在于,在创作上尽可能有效利用前人反复验证、打磨过的经验结果,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最大限度的类型保障。与此同时,在读者/观众/玩家那里能够迅速捕捉并辨认到某种类型“程式”,从而确认该“作品”是此前诸多同类型作品大家族中的一员。甚至于从更根本性的层面来说,不同“推理本”中不同的故事场景与剧情设置,为吸引玩家提供了某种“求新”“求异”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属性,但作为“推理本”中某些固定的游戏类型“程式”,却反过来保障了玩家在游戏进行中的“安全感”和基本类型期待。于是,剧本杀中的“不同”与“重复”在这里就构成了一组吸引玩家的有趣悖反。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在于,这种“不同”与“重复”之间也绝非外在内容与内在机制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因为游戏内容与游戏机制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将不同的游戏内容与机制进行更为灵活、耦合式的对接,根据不同游戏场景与内容对游戏机制本身做出某些增益,才是产生经典本或“爆款本”的关键性因素。
此外,在“推理本”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游戏机制在于平衡玩家阅读剧本与进行游戏之间的关系,玩家过于长时间、大篇幅阅读剧本固然不利于游戏趣味性的提升,而将大量剧情信息以道具、卡牌、线索提示等方式融入到游戏过程之中,将完整的剧情叙述切割为不同的玩家行动片段则是增加玩家参与度和体验感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样一种游戏机制并非传统推理小说中所固有,而是游戏作为一种更为综合的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跨媒介叙事现象。而我们在分析这种“读剧本”和“玩游戏”的“跨媒介”与游戏机制平衡时,或许可以借鉴青年学者朱小枫在考察数字游戏《致命框架》时对于其中“看影片”与“玩游戏”之间关系的相关分析:“‘影像’的核心行为是‘观看’。游戏的核心行为是‘玩’。在电影中观众通过‘凝视’完成情绪积累。而在游戏中玩家则需要通过对操作的期待和反馈来达成‘心流’的体验。”而在“推理本”中,“读剧本”和“玩游戏”是整个剧本情节推进的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保证了相关情节元素传达的稳定和准确,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玩家之间的“视域”差别,后者则有助于增加玩家的参与感并发挥其能动性,能否做到在二者间一张一弛的有效组合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推理本”的整个游戏进程与体验。
总结来说,虽然“推理本”往往被追认到“谋杀之谜”的“远源”和《明星大侦探》的综艺影响之中,但其和传统推理小说之间的血脉关联也不容忽视。除了时常出现的“推理本”对于经典推理小说核心诡计的“致敬”或“抄袭”新闻之外,其更在根本上符合推理小说从“福尔摩斯模式”到“阿加莎模式”的文类转型趋势,并可以视为推理小说这一发展趋势延长线上的泛文化产品与现象。抛弃表面上千变万化的剧情故事,而抓住更为深层的类型“程式”与“游戏机制”可能才是我们从根本上把握“推理本”的有效途径。当然,“推理本”作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游戏产品,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甚至是跨媒介的叙事方式,而如何更加具体地把握这些叙事方式,也是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推理本”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对于研究“推理本”中的类型“程式”、跨媒介叙事方式与游戏机制更高的理想追求可能还是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否能找到以此为形式中介的社会历史关联,进而考察出“推理本”背后的社会文化症候和情感结构,而对于这些情感结构的挖掘也正是未来“推理本”与侦探小说的相关研究中所期望抵达的某种研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