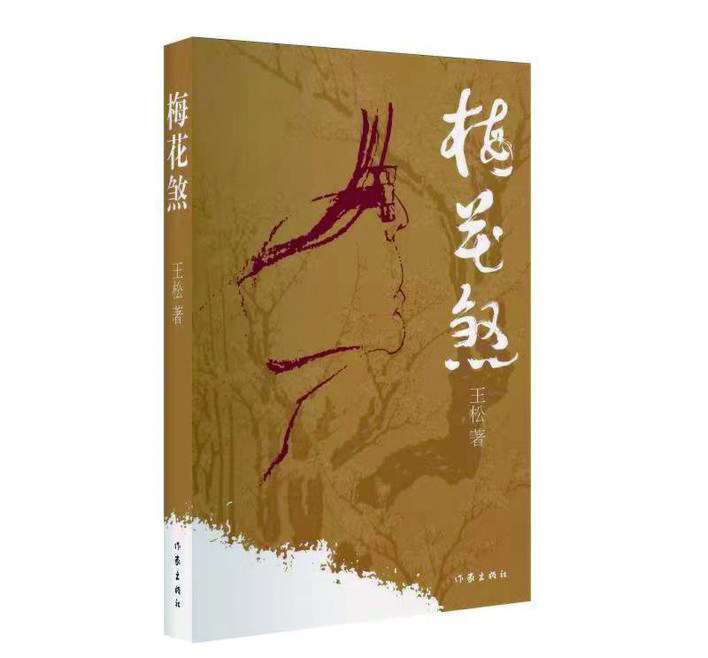王松的中篇小说集《梅花煞》是他近期写作的一次醒目展示,也只是其海量作品的冰山一角。《梅花煞》包括六部中篇,背景横跨大半个世纪,涉及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些小说描摹个体生命的悲欢沉浮,把碎片式日常细节整合为具有人文价值的叙事经纬,以此洞视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王松深入民间,打捞历史,为小说文本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酷烈却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叙事风格。
小说《梅花煞》以回溯的视角聚焦于昔日曲坛的众生相,梳理当年枝枝蔓蔓、影影绰绰的模糊往事,让历史真相变得清晰起来。动荡年代,老艺人郝连瑞写信揭发另一位老艺人白燕升曾有汉奸嫌疑,后不了了之。小字辈叶汶意外发现了这些陈年旧事,不免好奇,为了解真相,他开始暗自查访。叶汶的查访并不顺利。仅有的几位健在者多已年迈体衰,对当年白燕升并无非议,却说不出更多事实,即使是叶汶家里的知情老人也总是语焉不详。最终,叶汶了解到,白燕升并非揭发者所说的那样,他多次拒绝日本人“红帽衙门”的拉拢,一次次躲避怀有目的的日本女人,最终仍为日本人唱了三天,忍受如此屈辱,也是万般无奈。后来他偷偷花钱,在《庸报》上登了一个自己溺水身亡的消息,意在彻底消失,离开此类纠缠,却未果,后来莫名失踪。关于这位著名鼓曲艺人的传说坊间有多种版本,一直是个悬案,清白做人没有争议,只是命运多舛,以“煞”了结。
《梨花楼》中的梨花楼不是戏楼,不是酒楼,而是只有一层房间的普通茶馆,天津叫茶园。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来茶园的常客多为养虫儿养鸟的,有的性格不合,相互看不上眼;有的人品不正,旁人尽量躲着。还有贪小便宜的、嘴没把门的、嗜赌成性的,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属于社会的寻常一景。这里不见刀光剑影、深仇大恨,琐碎的日子波澜不惊却见微知著,让人从中体会到了空茫、怅然。至此,王松决不饶舌,梨花楼门上挂了一把大铜锁,结束了故事。岁月的滋味浸润着小说肌理,渗透于叙述话语的毛细血管,也蔓延在读者内心。
王松的写作一般不大注重所谓“形而上”意义,他更注重叙述的密度要大于故事的密度。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准确。在王松看来,对于小说,准确既不是单纯的建筑材料,也不是技术性的建筑手段,而是关乎建筑本身的成色和质地。叙述准确为王松带来了一种强大、从容和自信。王松准确规定了小说的速度,这就需要挤干语言水分,力图轻装简从、直击要害,“小说的速度应该是被作家的叙述语言控制的,一旦发动起这个速度,也就容不得再有半点语言杂质,否则就会增加叙述的摩擦力”。由此,小说的语感、语境也会内含玄机,充满张力。
《王三奶奶考》写的是地道的津人津事,却意在当下与历史的对接,折射市场经济年代中的一种诡异现象与精神畸变。小说“考证”王三奶奶的身世之谜与死亡之因,几近不厌其烦,却有深意在焉。关于王三奶奶的传说,坊间有许多不同版本,但小说只写了“考证”,而不负责评价。吴珂在考证过程中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不是王三奶奶不简单,而是黄乙清的动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单纯,他的“饮水思源”和“寻根”是有利益驱动的。吴珂意识到,王三奶奶只是黄乙清现代经营模式的一个金字招牌,他利用信众的虔诚与无知诱导消费,以各种堂而皇之、美丽诱人的名目谋求私利。吴珂痛苦的是,自己无意中为黄乙清提供了论据,那一刻,他觉得被羞辱的不是自己,而是“俗神”王三奶奶。小说由此折射出了当今社会的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
王松讲老天津人的故事,很在意其文化和性格的元素。他坦言,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天津,但很“喜欢”乃至“热爱”这座城市,它“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自于自身”,“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王松的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曲艺元素,他喜欢相声,多次谈到“万相归春”的话题,相信世间万物皆可“入活儿”,并认为天津相声是天津人性格和城市“杂色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一朵文化奇葩。
《春景》中的朱胖子就是在茶园里说相声的,因一次表演中走神儿接错了词,被观众叫着倒好轰下场,搞得一同表演的师父罗鼓点很没面子。朱胖子走神儿与坐在场下的唐先生有关。朱胖子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挺着师父、护着师弟,他喜欢唱京韵大鼓的小桃红却不穷追猛打,而是默默关怀,处处呵护。最后,朱胖子终于明白小桃红喜欢的是唐先生,点头称是,默默离开。如此通透性格和处事方式,也是天津文化涵养的结果。《春景》借鉴了传统相声艺术手法,铺平垫稳,针脚绵密,一旦“包袱儿”抖响,戛然而止,不再多言。进入小说叙述,王松不是没有立场和思想,但他的意图表达是隐蔽的、内敛的、留白的,充满暗示,诱人想象。
《一溜儿堂》中,刘福有给自己经营的棺材铺取名“一溜儿堂”,也随之叫刘一溜儿。其实,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只有十几岁的粑粑三儿,这个男孩虽未成年,却看过并经历了太多与死亡相关的场面。他爹是棺材铺的苦木匠,人称吃阴阳饭的,意外身亡后,粑粑三儿不得不开始直面生计问题,他不打算子承父业再干这行,打算跟施杏雨学医卖药而不成,又想跟郭瞎子学针灸,郭瞎子却不见了。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为了活下去,只得跟着表哥崔大梨、崔二梨冒险,扒掉阵亡士兵军装,再把血迹斑斑的军装洗一洗,一条龙成批倒卖出去。这营生景象血腥,险象环生,每次都是连滚带爬地离开现场。一次遇到围堵,粑粑三儿亲眼看到崔二梨怎样被一阵乱枪打死,受到极大惊吓的粑粑三儿意外得知,刘一溜儿居然是收军装的下家,更没想到的是,精明如刘一溜儿者竟会因此而丧命,同样没想到的是,那个失踪的郭瞎子摇身一变成了“一溜儿堂”的主人,只不过此处改为针灸馆。故事的反转,为血色的“一溜儿堂”涂抹了戏剧性油彩。王松善于把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具化为一种斗智斗狠的胶着状态,叙事中常于不动声色中暗含“杀机”。那里面枝杈纵横、悬疑密布,充满了蓄谋已久的紧张和隐患,相互较劲,彼此消长,放大或显微人的精神断面受到的冲击和应激反应。
王松一直注重小说的好读指数,为解决“怎么写”绞尽脑汁。他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故事性,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讲故事固然是小说家的天职,但谁在讲故事、以怎样的方式和腔调讲故事,这里面很有讲究。王松的小说故事是一种被充分叙述过却不含水分的故事,他深感“找一个好的表述方式比找一个好的故事更难”。高明的小说家只负责提供好读的叙述,而优秀的文本往往是大于作家的。王松用小说打造一面独有的镜子,用来照出人的真实面目,这面镜子既映现出“应然世界”,也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叙事的逻辑、小说的逻辑、文学的逻辑,把蹊跷事写出合理性,让不可能变得可信,这也正是其“万花筒叙事”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