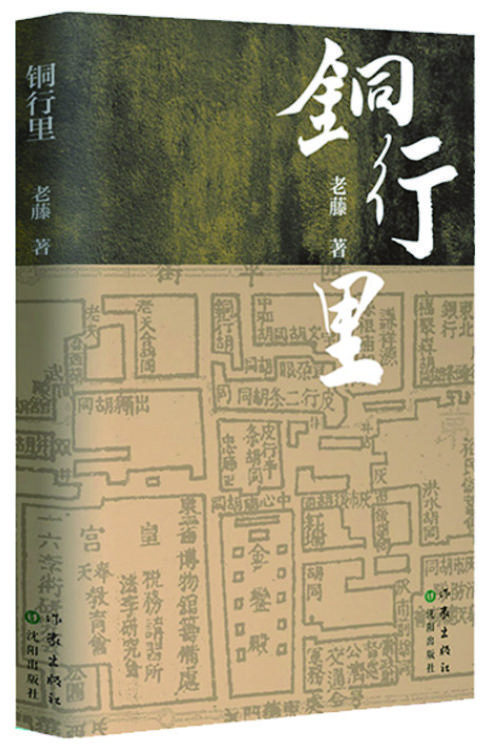我始终认为,中华的早期文化是青铜文化,因为青铜的发展要先于瓷。中国是瓷之故乡,这一点毋庸置疑,商代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6世纪,华夏大地已经出现了瓷器,可惜这个时期瓷器传世不多,且出土多是粗瓷和陶器。青铜器就不一样了,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夏朝,是夏商周文化的核心要素,青铜器不仅尊为王侯礼器,而且已经进入贵族家庭成为实用器具。青铜文化在西周晚期达到了顶峰,而瓷器直到宋代才真正成熟,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著称于世。当然,瓷后来者居上,势头盖过了铜,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我对铜感兴趣,源自家里的两只青铜爵。我家当时在胶东即墨县田横镇,一个“人家犹有古风存”的古老村落,村里春节祭祖庄严隆重,即或在上个世纪70年代,祭祖之风也未能禁绝。春节临近,家族祭祖的主场设在我大伯父家。大伯父会支起梯子,从天棚上取下油布包好的家谱、牌位、香炉、烛台、青铜爵等等,恭恭敬敬地将家谱挂在墙上,家谱下面安放供桌,铺上大红台布,摆好香炉、烛台、青铜爵等,供家人依次叩头祭拜。因为烛光暗淡,家谱上先祖的画像又面目凛然,少年的我便有些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说来奇怪,当叩首后抬头看到那两只盛满米酒的青铜爵时,心里会生出一丝亲切感来,因为我家中条案上也有同样的两只。两只爵出自哪个朝代没有印象,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无法给文物断代。后来因为屡次搬家,那两只传世的青铜爵不知所终,成了我心头无法弥补的遗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物价格低廉,造假之风未起,老宅里这两只青铜爵是真品无疑,要是不遗失的话一定会被我尊为至宝。
因为有青铜情结,每到一地我总会关注铜器,探寻一下城与铜的关联。我想,沈阳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可能与铜无缘,我看过许多辽金时期的铜镜,做工非常精美,辽国六府皆有工匠可制。沈阳历史悠久,从战国时期的候城、辽金的沈州,到元代沈阳路、明代沈阳中卫,再到后来的盛京、奉天,这样一处东北旺地,从大家闺秀到小家碧玉,至少离不开铜镜吧,但因缺少史料,沈阳的铜缘我只能追溯到沈阳中卫。据《辽宁通史》记载:“永乐九年,沈阳中卫有局造匠人69名,生产了196台佛郎机。”佛郎机作为仿制葡萄牙的速射铁炮,由炮管、炮腹和子炮组成,沈阳中卫的工匠曾尝试用铜来铸造子炮。在翻阅清代盛京地图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城中心地段竟然标有一条铜行胡同,正是铜行胡同这个地名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在了解了这条胡同的来龙去脉后,我觉得应该打捞并修复这段被时光淹没的城市记忆,因为铜行胡同不仅是沈阳工匠精神之滥觞,这里还静默着沈阳民俗文化之密码,铜行胡同就像一条铜纽带,将这座城市的百年历史串连成一幅生动的铜雕。
铜行胡同又称铜行里,与沈阳故宫毗邻,长约百步,宽不过八步,南始沈阳城的原点中心庙,北通沈阳最繁华的四平街,据说在清中晚期,这里锻造铜器之声响彻昼夜,店铺生意红红火火,众多堂号出品的火锅盆碗、幔钩把手、首饰环锁、香炉烛台、锣镲管号、神像吉兽,可谓应有尽有,知名度堪比北京的琉璃厂。铜行胡同的名字与盛京城扩建有关,1625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次年,皇太极登基后将沈阳更名盛京,并按都城规制进行大范围改造。传说为了给盛京赋予江山永固的“铜心”“铁胆”,皇太极下令将全城的铜器店集中于城中心小关帝庙处,铁匠铺则分布于城垣四周,这便有了闻名遐迩的铜行胡同。铜行胡同集中了多少家铜器店已经无从查考,乾隆回盛京祭祖,当地官员因担心铜器店锻打声惊驾,要求胡同里的铜匠停工外迁,当时记载的店铺应为60余家。
铜行里声名鹊起得益于一张小小的奉锣。民国初期,老字号富发诚出品的奉锣风靡一时,供不应求,京津沪的戏班子如果没有奉锣,乐队便算不上标配。加工奉锣是富发诚老师傅的绝活儿,成语“一锤定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奉锣皆为手工锻制,由徒弟们在胶床上将锣锻制成型,最后决定音色的一锤要由老师傅来敲,刚刚还锣声喑哑,老师傅几锤下去,锣声立马变得清澈亮丽起来,一张抢手的奉锣由此制成。铜行里的敲打声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时期,各家店铺争先恐后为赴朝参战部队加工军号、徽章、皮带扣、马具等。后来,经过公私合营改革,铜器店先后并入规模更大的国营、集体企业,铜行里的手工业生产模式便淡出了视野。但胡同依然存在,偶尔还有锤錾之声从胡同里响起,在中心庙的灰墙上激起几丝回音。上世纪80年代,城市改造浪潮风起云涌,古城老旧的街巷被荡涤几尽,铜行胡同也未能幸免,被彻底地抹去了,只剩一块临街的牌坊在睥睨熙熙攘攘的过客。我到中街踏察过,发现这牌坊石新漆亮,没有任何老旧相貌,一问才知这是近年新竖的。铜行里原址建了个名曰兴隆大家庭的商业广场,可惜这个兴隆大家庭并不兴隆,一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惨淡状,据说政府已经在考虑新的规划了。
300年铜行里,靠的是师徒传承,靠的是铜心、铜气和铜缘。富化诚铜器店的老掌门规定,到富化诚学徒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其中辨铜气让我脑洞大开,老掌门的后人解释说,铜与人一样有种看不见的气在,铜匠若不辨铜气,则识不了铜性,达不到人铜合一,做出的器物就会缺少灵气。老掌门认为铜匠要惜铜如命,因为铜不是死材料,而是活生命,铜气是有味道的,与人的体味相近,这恰恰是一种生命的味道。老掌门还认为铜匠传承不单单是传授手艺,传授的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精铜须经九炼,技艺便是时间,铜经九炼不生锈,錾落千锤始成型,这些铜匠们耳熟能详的话语,透出的则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奥妙。富化诚有关铜的职业理念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的确,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命的全部意义是繁衍,布鲁德蝉在泥土里蛰伏17年,羽化成蝉后只完成一次交配便会死去,而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传承,传承包含着生命和文化两重含义,对于人来说,生命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同样重要。从明朝的佛郎机,到清朝的红衣大炮,再到民国初期的奉锣,沈阳一直保持着绵绵不绝的工匠传承,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厚积薄发、梦想成真,当家作主的工人们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大国重器,让沈阳有了工业重镇、英雄之城的美誉。
历史是一道痕迹斑驳的时空长廊,吸引眼球的往往是那些价值非凡的器物,而成就器物的工匠却往往名不见经传。沈阳故宫大政殿,是当时盛京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一直被后人所称奇,但大政殿的设计者是谁?主持施工的匠师又是何人?无法找到明确记载。后母戊鼎、西周大盂鼎、毛公鼎,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出自哪位工匠之手,也没有人知晓。史书上记载的大都是器物的所有者而非创造者,即或像建了赵州桥的李春,除了唐人张嘉贞在铭文中写了一句“隋匠李春之迹也”,再也找不到李春的其他生平文字。我们应该感谢张嘉贞,如果他不在铭记中写下这7个字,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赵州桥是谁人所建,功劳只能记在隋文帝和隋炀帝头上。选择性记录是封建史官的立场所致,这是时代的局限,但史官的缺失,作家可以补位,作家的书写是另一种历史,作家书写的历史不仅有其艺术感染力,而且更有可能是一部信史,因为大多数作家是靠良知在写作。这一点,我们从曹雪芹、鲁迅、巴尔扎克、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都能得到验证。
我努力让自己的笔墨更多地用在“小人物”的书写上。如果说写地位显赫、事业辉煌的“大人物”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写“小人物”就是一种温情、一种互动、一种躬行。历史上有太多被忽略的“小人物”值得书写,他们才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写“小人物”可能不讨巧,但不一定不能传世,《搜神记》里的《韩凭夫妇》就是写的“小人物”,不畏权势双双殉情的韩凭夫妇,今天读来还令人潸然泪下。
我有幸认识了一个值得书写的“小人物”石洪祥。当然,此人已经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国内铜雕行业的名家,但我没有把他当大人物来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书写的“小人物”。石洪祥是铜行里奉锣的最后一代传人,是铜行里铜匠后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石洪祥一直自称铜匠之子,尽管他毕业于上海美院,有正高级职称,荣获过国家大奖,但他身上一直保持着铜匠本色,他亲自画图、锻制、制模、浇铸,整日弄得铜色满面,他说铜匠本色没法改变,铜气和铜性已经融化到了血液基因当中。石洪祥花费10年时间,依《营造法式》工艺,按十比一的比例复制了一座纯铜大政殿,铜殿每一个构件都可以自由拆卸,他当场给我演示了拆卸门窗、立柱,果然相当自如。我问他为何十年造一殿,有十年之功,会创作多少价值不菲的铜雕,而铜质大政殿如果不出售的话谈不上经济效益。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传承,如果不复制,大政殿这种古老的建筑工艺就会失传,复制大政殿,等于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活教材。我从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了富化诚老掌门的存在,这是一种难得的责任传承。正是通过石洪祥,我才真正走进了淹没在时光里的铜行胡同,走进了已经消亡的12家铜器店,走进了100个铜匠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人们可以遗忘很多,但不应该遗忘那些成就奇迹的工匠之花,“百工之事,圣人之作”,工匠呕心沥血之作俱是文明的结晶,属于人类应该善待的财富,像奉锣这种地理标志产品,形成不易,理应珍惜,把它从尘封中打捞出来擦拭一新,再度呈献给世人,不啻是文学的一份功德。孔子故里有块牌匾,上书“金声玉振”四个大字,这金声就是敲击铜钟发出的声音,铜钟奉锣皆发金声,让久违的奉锣金声玉振起来,至少会给生活增添些乐感。
任何一座古老的城市都是文学的富矿,如同一潭湖水,沉淀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盲盒”。在湖面上荡桨划过固然惬意,若是静坐船头,垂一根钓线来钩沉抉隐,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创作《铜行里》之前我问周围许多人知不知道盛京城的铜行胡同,他们纷纷摇头;我又问知不知道享誉全国的奉锣,他们还是摇头,这情形坚定了我写《铜行里》的念头,我要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城市记忆打捞出来,让后人记住沈阳城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胡同,尽管它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但在当年,这条胡同就是沈阳心脏中的一条动脉,血脉偾张了三百余载,这动脉里的血,就是铜匠们代代相因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