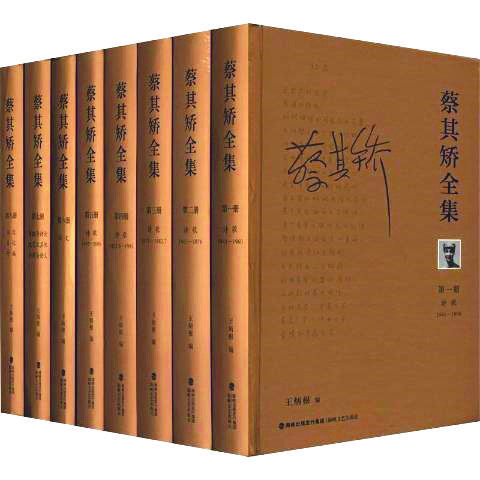蔡其矫(1918—2007)一生写诗,前后长达60余年,《蔡其矫全集》(王炳根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收入诗作1299首,其中510首属于第一次发表。这些未发表的诗,有的是因为时机不合,无以发表,更多的则是他对诗有自己的要求,而不愿发表。蔡其矫曾在华北抗日联大、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写诗之外还讲诗,在不同场合下谈过诗歌的创作,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新诗讨论中,他积极参与其中。在其全集中,讲稿、诗论、诗序等,便收集了一大卷。他的一些诗歌观念,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仍有意义。
第一,现实与想象。蔡其矫的诗歌十分关注现实,他认为关在房间里是写不出诗的,他的一生都在大地上行走,直到晚年还有西藏、新疆、内蒙古、海南等地的壮游。因而,蔡其矫有大量描写现实的诗,行军打仗、战场厮杀、水兵巡航、伐木场景、海峡长堤、渔港码头、苍凉大漠、雪山湖海等等。那么,这是一些直接描写现实场面、真实场景的诗吗?答案却是否定的。他认为:“诗的创作,虽扎根于现实,却绽放于想象。诗人需要有能力投入事物的核心,与事物合一,这是单凭实物描写或客观陈述所不能达到的。”他这里所说的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诗。而能不能达到这两者的统一,进入诗的境界,关键在于诗人有没有能力投入事物的核心,而不是说有没有能力接触到事物。只有当诗人的能力强大到能与事物“合二为一”时,诗歌才产生了。他还将现实比喻为大地,想象比喻为彩霞,认为大地是永远存在的,而彩霞却是千变万化。这种由现实的大地之实,进入想象的彩霞之虚,“是人生经历所抽象出来的更高境界,是逝去的哀伤和未来的希望,是心的最深处的隐秘的感情,在现实的具体感触上面飞翔的翅膀”。在有了现实大地之后,蔡其矫最为看重想象彩霞所编织的景象,这“是作者灵魂的再现,是诗人全部审美主动性的展示”。(《诗的虚实及其它》,1984年)
对现实的把握与描写,蔡其矫还有细化的陈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不是关注现实的普遍性,不是关注外在与表面,而在于关注别人所可能忽视的现象与事实的细节,也就是说可以略过现实的外在与表层,进入到对细节的关注。而诗歌的细节,与小说、散文关注的细节,还有一定的区别。诗歌的细节不一定是生活中的确实存在,有可能是对现实“走样的回忆”,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细节具象,并不一定是生活中的细节,那可能是走了样的回忆中的细节。这种诗歌中的细节,“是人的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留下的精华”。他认为任何存在的真实,都是经过修饰、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改观,才可以进入到作品中来。诗人的能力就是体现在对细节的描写上。而细节反过来又是作者心灵在作品中的延续,是心灵的历史中每一事件的“五彩缤纷又各自分散的为感情节奏所萦绕的深思”。蔡其矫坚持这些诗歌观念,也用这个标准检验自己的诗,从而主动向外人屏蔽了不少自己的作品。1955年夏日,蔡其矫曾在东北小兴安岭等地生活了一个月,得诗21首,诗成后对大多数的诗作不甚满意。在诗人看来,它们没有达到与事物合一的境界,游离于事物的表面,或只做客观的陈述,虽有现实的场面,但缺少诗歌的“彩霞之美”。这些作品便一直沉睡在他的诗歌稿本中,只有《不夜城》《沈阳的夜》《草原的中午》《松花江上》《人参岛》等五首,发表后收录到他的诗集《双虹》之中。同样,像《川江号子》《雾中汉水》这样的诗歌,作者十分看重,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便是在于作者在描写汉水、川江上的纤夫赤裸着双脚倾身向前的身影与喘息时,注入了想象的彩虹:“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
第二,诗的双轨。这是蔡其矫对诗歌是“现实与想象合一”产物观点的进一步表述。他在《蔡其矫诗歌回廊》自序中说:“如果可以为诗下个定义,我以为,人生一段经验或一时感受,加上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便是诗。”诗人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写作材料,必须用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来照亮它,诗才得以产生。这是个双轨,一是经验与感受的轨道,虽然诗产生于一时的经验,但不可能停留于这一刹那,即所谓的灵感,它在取得这个前提之后,必须迅速地进行转化,从体验、认识到表现,从眼到手,从无形到有形。另一个轨道是内存的经验,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即通过书籍接受前人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外部来的经验。这个“内在”与“外部”也许不怎么确切,如果揣摩其实质,则是与“现实”与“想象”是对应的。人生的经验与感受,显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接触与把握而产生的,而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则是想象空间的深层。也就是说,进入诗歌的想象,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凭空产生,要有才华与气韵的输入,这个输入就是用头脑里贮藏的全部知识、全部感情与良心、全部才能、全部艺术手段,去酝酿,去催生,去赋予一定的形式和字句。这个才华与气韵,蔡其矫用了一句“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没有这种全人类文化成果,想象无法张开,更不能形成多彩的景象。(《诗的双轨》,1999年)关于“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更具体的阐述:“但是文化,并非一个人知识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他辨别人、了解人乃至帮助人的那种能力。许多最有教养的人,都远不及普通的士兵、农民、工人甚至狂人那样有文化。有文化的人乃是那心胸坦率,而不是上起柏拉图,下至卡夫卡、乔埃斯的引经据典的人。”(《传统与现代化》1983年)
第三,朦胧与晦涩。上世纪70年代末,蔡其矫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有较多的往来,那是因为他有一部分诗作,与当年那一批“朦胧诗”比较接近,所以在有关“朦胧诗”的讨论中,他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年轻人的兴趣一般不在于理解一首诗,而在于感觉一首诗。他们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捏造品感到厌倦。他们热烈希望多产生一些出自真情实感的创作。当诗人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时,他们就自己来写这种偏重感觉的诗。”他这里首先将朦胧诗定格在“感觉”上,指出偏重感觉的原因是当时的诗歌中有很多“千篇一律的捏造品”,故而以自己的感觉来写诗。这个观念与他的“想象的彩霞”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些诗在当年曾遭到了批评,说是晦涩难懂。蔡其矫为其辩护,语气还不平静:“艺术多种多样,诗也各自不同,有的一目了然,有的深藏不露,为什么要祭起这两把尺子,来打杀新种呢?”
蔡其矫熟读中国古典诗歌,他说李商隐的无题诗,因其造境深沉、意象新颖,为人称赞,但也有“晦涩难懂”之评语;李贺的诗偏重于感觉,因为有了比较切实的注释,后人才不难了解诗人的深意;李白的诗在群众中的影响广泛,但他的《蜀道难》,千百年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李白那首妇孺皆知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有刘禹锡关于桃花的两首诗、张继的《枫桥夜泊》都曾被误读误解。在诗歌史面前,蔡其矫认为应该保护那些暂时读不懂的诗,他给出的说明是:“为了保护一己身名,为嫌恶赤裸裸的表露,诗人有权利把诗写得含蓄些、朦胧些,更多地动用借喻,控制感情,少用陈述,探求某种瘦硬的口语,用若干有关心境的并列意象,诉之于读者的感觉。这是诗人的权利。要保护这正当的权利不受侵犯,对任何哄骗,都不接受。”
在为朦胧诗进行辩护的同时,蔡其矫对诗评家也颇多微词。他认为:“大部分评论家,都是备受恩宠而生活平静的学究,历来都从事维持现状。他们强行推销的美学,往往是那种不费心血就可以获得的东西。他们有话要说,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还存在,不惜把昨日的经念道又吟道。年轻一代的诗自然就难以进入他们的内心。真正的诗,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那些身负荆棘,双手流血,心里有理想、有追求、有痛苦的人的写照,必定涉及他们的欢乐和悲哀、信仰和怀疑。”这里的语气不仅是不平静,而是很尖锐了。这些观点都写在了《您真的看不懂?》(1981年)这篇文章中,而这篇文章本来是一家诗歌刊物的约稿,但最后却是没有刊发。不知是语言尖刻还是观念不符,反正是在多年后才与读者见面的。
(作者系评论家、冰心文学馆创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