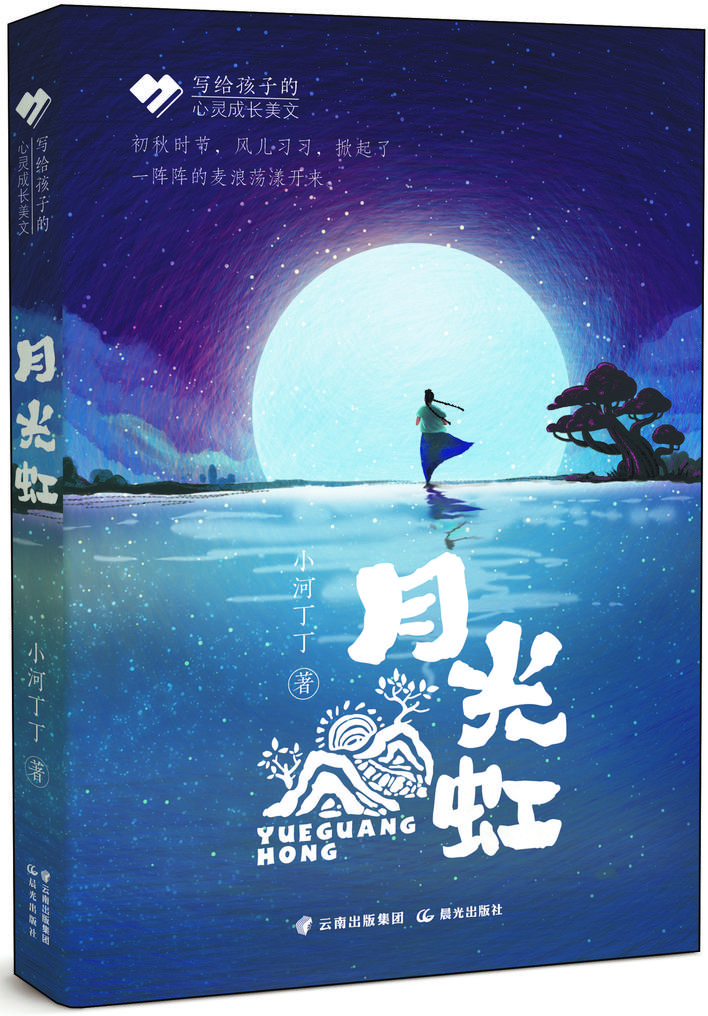小河丁丁的散文书稿《月光虹》在我电脑桌面躺了快一年了——为确证这个时间,我翻出邮件,居然记忆如此不靠谱,确切说是小半年——怎会有这么大的出入?思忖半晌,只能说丁丁以无声胜有声的涵养、很沉得住气地不来催问,反成了我潜意识里的一桩心事。我每天打开电脑,丁丁的这个文档就提醒我一次,跟着就心里抱歉一回。手头琐事总是应接不暇,我担心延误了出版,短信去婉谢“辞请”,丁丁回复:“不急不急,清心恭候,学习静守师傅。”他把“静守师傅”请出来了,那是我散文里写到的一个小庙和尚。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告诉他书稿正看,序文写成即发来。丁丁回我一段话:“好像慕名探访梅园,踏雪而来,只见柴扉掩闭,不敢贸然叩问。徘徊良久,终于听见园里有人说话啦!”
这个丁丁,前世定是山野间一株谦谦君子兰,今生来到这个扰攘世间,很多热闹的场合,他肯定是离群的一个。于是心里了然,丁丁这么执念地不找闻人名师写序,反求诸我这样的“野”,是呦呦和(hè)鹿鸣啊!谢谢丁丁,我虽鼓瑟不擅,且清音以对罢。
我同丁丁的交集不多,止于两三回儿童文学会上的照面,倒是近来常有他消息,丁丁又出新小说了,丁丁又获奖了,可见他在写作上的精进。脑海里存着这么一个印象:小河丁丁的眼睛很特别,不怎么熟悉他的人,很容易从他的眼睛里发现一些秘密。他腼腆不爱说话,倘若要他在广众之下发表一个演说,他的眼睛会先于大脑和身体做出反应,收起光芒,垂下眼帘,不看他人。那一刻,他的眼睛明确发出信号:我想沉默。台上的他安静站着,台下的人屏息等着,无端上演一场隐形的拔河。僵持之际,他突然一个飞身,狂奔到猎猎春风里,丢下一屋子的讶异,张开双臂陶陶然……
这个意象太强烈了,那么多年过去,仍驻留在我脑海里。而今的丁丁怎么样?大抵更沉稳、更自信、更笃定了,这是我从他文字里猜想的。但是他的眼睛依然特别——特别在他看世间万物的角度,放低了身子,和植物、花草、虫鱼一个维度,相当于躬身而行,跟个孩子一样,所以他看到的都是很细微的动态,着急赶路的大人根本看不到。
比如他注意到稻田里分界的小田埂,软软的,不好用来走路,小田埂下有个拇指粗细的洞,以为是老鼠洞,扒开来,竟然是黄鳝的家!公园一角,有樟树有石椅,弯腰扫去石椅上的落叶,看到一片“比小指甲一半还小的、白色的花,原来不是花,竟是一只虫子……这么小的生命,长成花的模样,也是一种拟态吗?”他惊奇得像是发现一个大秘密。街上走一圈,繁华热闹不入他的眼,他留意的都是人们一掠而过的场景,比如不会用手机卖木瓜的女人、聚光灯照不到的无名伴舞者、没有观众自得其乐的唱歌老人、无悲无喜不愿接受世人怜悯的流浪汉,还有山村教师、不曾晤面的文友……有篇《大王椰子》,说的是路边有人摆摊卖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果实,“显目的棕红色,比枇杷大不了多少,果枝像棕榈。那么大的果枝,果实总有上百枚,斜倚着货篓摆在地上。跟它相伴的,还有三只花母鸡,五六个剥了绿皮的椰子,其中一个敲破了,露出白色的肉。还有几盆花木,一盆居然是小桑树,不到一米高,零星结了几颗桑椹。”简白文字,场景如在目前。这水果买回去却不能吃,太太笑他上了当,丁丁怎么反应?“人家拿大王椰子——还有小桑树和敲破了的普通椰子——来卖钱,当真有几分童心。”看到这里我真要笑了,有童心的人才能看到童心吧?丁丁笔锋一转,又说:“写着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忽然闪过一念,心头隐隐发酸:也许,人家实在没有挣钱的路子吧?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文友,文友却说:也许人家根本就不卖,你问了,才卖?我愣了一下,差点儿笑出声来。”
这样平实、有趣、来神的文字,难道只是童心吗?这是一个有童心的作家难得的天真气、诚恳心和美好的感情。丁丁用如此珍重的心情描画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又以活泼泼的生趣择取寻常日子里的美善和感动,这样的观看姿态是低的、小的。因其低,他探知到了大自然的秘密;因其小,他得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的世界。有个社会学家说:“如果是‘大’的话,就总是从自身出发,去定义别人,而不是去观察。一个特别张扬的人当然惹人瞩目,但总是不够智慧,骄傲自大过了头也叫人讨厌。”
丁丁当然是智慧的,他懂得在日常里体察人情物理,懂得审词定气,慢慢闲闲,闲中才能着色——读他文字,我看到后面站着一个人——“惟悠闲才能精细”的汪曾祺。丁丁的文字干净也传神,对话克制,气韵生动,以简笔勾勒风神意,所以他定然也体悟过汪先生对语言揉面一样的反复抟弄,那份“苦心经营的随便”。
丁丁将一块老家山上的石头当传家宝搬到工作生活的广东新家,视若珍宝给它洗刷,女儿哂笑这个爸爸:“我们家的传家宝,在别人眼里,那价值还比不上塑料袋。”(《传家宝》)——缘由是那个装石头的塑料袋在搬家时,临时放在了我家楼下,小区清洁工以为没人要,将石头扔在了花坛树下,把充气塑料袋拿走了。
丁丁写白玉兰,那种喜欢,眉目生动,叫人想起他的故乡前辈沈从文,也是一样的欢喜和深邃感人。“我喜欢它的高大,洁白,芬芳,但它又是寂寞的,安静的,不张扬的。尤其是那些藏在枝叶深处的花朵,除非是有心人,不大容易发现。”(《白玉兰》)不知道丁丁在写下这段话时有没有自知,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写出了自己。
《开辟鸿蒙》一篇写他的文学梦,虽然很多写作者的文学路都艰难,都曲折,都执念不改——没有这份初心,也就不成回忆了——但是丁丁的文字依然有打动人心处,原因在于他始终持有一颗赤子真心。他喜欢阿城小说《棋王》里到处找人下棋的王一生,“不仅棋下得好,还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觉得“有什么样的追求就有什么样的外在特质”,王一生就是一个单纯执着、有点呆气的人,正是这点宝贵的呆气成就了王一生的棋艺。“文艺的大道不是车水马龙的,我们找到了它,就找到了孤独——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症呀,这时候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真正优秀的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话:不要向外求索。”(《王一生的呆气》)这段有感而发写下的话堪比丁丁的文心之光。
读丁丁的这些儿童散文,我的脑海里跳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理解作家笔下的天真?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讲天真、美善、诚恳这样的字眼了,觉得根本不好意思写出来。写给孩子呢,又觉得过于说教,未必通达孩子的心灵。可是天真、美善、诚恳在一些“古典作家”那里,比如雨果、歌德、罗曼·罗兰,比如冰心、萧红、沈从文等,又被很珍重地善待。他们的文章常常还出现在语文课本和学生必读书目里,也就是说,我们一面在课本里强调这些好词,一面又轻率地打发了这些好词——这是眼下文学写作、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内或多或少患上的一个“浮躁病”。非常难得的是,我在丁丁的文字里看不到这种浮躁,他是那样清雅有味地欣赏着,记录着,生活着。他怎样生活,也就长出怎样面目的文章来,好的文字就是生活本身。所以,本质上,天真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作家洞悉了生活以后,依然能够笃信,看得见光和亮的朴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