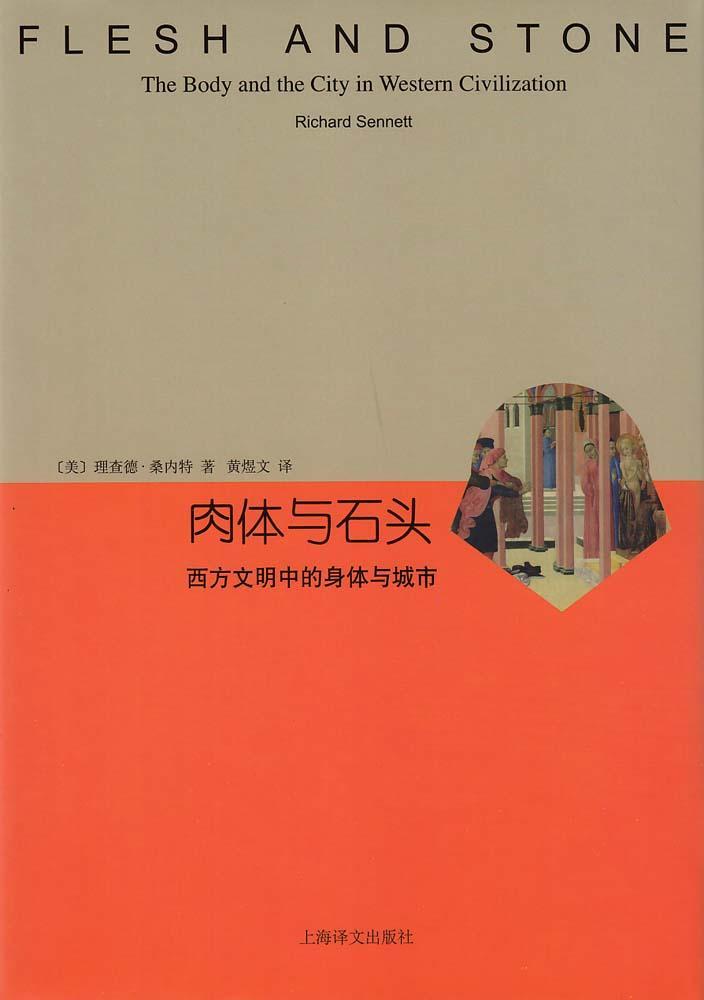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包含三层隐喻,第一层是肉体与石头,宏观指向城市与肉身;第二层是具体的身体器官和生命体征与城市文化的对仗;第三层是更细微具体的知识颗粒层面的“象征”,帮我们弥补曾经的历史常识。本书明显受到福柯的影响,可以看作是身体权力书写的都市性延伸,或是城市身体批判史或空间政治身体学。有学者将之归类为城市文化史,有学者称之为空间社会学,本书是公认的城市研究名著。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后文简称《肉体与石头》)这本书充满了对抗性。字里行间还充满了愤懑——原谅我用这个词汇,因为只有这个词能勾起我记忆中的理查德·桑内特印象。
桑内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在我看来,他是少有的在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建立广泛影响力却依然保留学术味的学者。准确地说,不是喜欢,是喜爱。有两个事件,使我对桑内特的学问印象深刻,一次是2017年其在哈佛大学GSD的演讲,有公众号对此做了详尽的报道。还有一次,张永和等人在北京组织的“基多宣言:开放城市”论坛活动,桑内特与萨森夫妇二人来到了现场。他们的学说和演讲饶有趣味,我收获了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这种一厢情愿的“渊源”还要增添一笔,和阅读芒福德的感受一样,桑内特的书写总埋藏着“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以及很深的追古情怀。所以,“愤懑”的印象终于找到了出处。
《肉体与石头》这本书,有的将之归类为城市文化史,有的称之为空间社会学,但无一例外的是公认为城市研究的名著。对书本内容的解读已有很多,我只从三个角度切入,略抒一二。
文风奇崛,想象瑰丽
桑内特文风奇崛,想象瑰丽,不仅指的是行文表述风格,也包括观点。所以,阅读《肉体与石头》这样的书很可能会有“不适感”,——这不是“常规”印象中的学术书写。我们会发现桑内特“招数”很多,各种“套娃”式写作。尤其是不断嵌套的隐喻式表达,把读者抛进螺旋的知性虫洞。这或许是桑内特的炫技的表现。知识存货如何用出来,需要借助这种表达方式,于是大量的交叠嵌套的隐喻、换喻、映射、类比和象征登场了。读者的任务是除了消解内容本身还要习惯表述风格,私以为恰恰这样的书写才是学术的。
隐喻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起到暗示的作用,但必须掩埋在知识逻辑和知识背景下,这样就具备了很强的创见性和学术味。就本书来说,第一层很明显是肉体与石头,这是一个宏观的隐喻,指向了城市与肉身。第二层是具体的身体器官和生命体征与城市文化的对仗。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用“声音和眼睛的力量”参与城市生活,反映民主天性与秩序驯化。“心脏的运动”则探讨中世纪时期灵魂与信仰如何左右城市空间,例如对威尼斯经贸市场的分析,建筑的隔断分区指涉了跳动的心室。最后是“动脉与静脉”,现代都市的通畅、高速、舒适成为双刃剑,个人主义得到强化,排斥了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人们的感官感受能力越来越弱。
第三层是更细微具体的知识颗粒层面的“象征”,帮我们弥补曾经的历史常识。例如,在古罗马,连婚姻的房间都应该是“秩序行为的学校”——灌输什么是“正确”。但这意味着多元性被拒斥。还有,中古时期巴黎人认为花园设计必须有三个要素:凉亭、迷宫和池塘;凉亭是有顶的空间,意味着在公共空间里面避免他人侵扰的边界;迷宫象征着灵魂努力地想在它自己的中心找到上帝;池塘则是可以反射的表面,是人们可以照的镜子。
如果象征、类比和隐喻都失去绝对界限,写作就变得复杂。书籍变成了“电影”,不但导演的招数尽显,而且观者的解读视角和感受极为丰富。令我想到了大卫·林奇和大卫·芬奇的电影,电影的重屏类比于文本的想象力。这样的写作不同于综述性历史写作,也不是质量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而是“才气”写作,因而也很“危险”,好在桑内特的旁征博引,进而消解了对学术体例规范的诘问。
“城市身体史”
本书明显受到福柯的影响,这就需要聊一聊“城市身体史”的概念。此中又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城市拟人的研究传统,再一个是“身体史”的城市延伸。
卷帙浩繁的城建史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城市拟人史。《肉体与石头》扉页既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城市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这句话已经宣明了城市的政治性,也表露了桑内特的价值底色。古希腊人通过展示身体培育公共精神,也丈量了城市。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到的“三位一体”原则肯定离不开人体感受的考量,“人的物性是发自人的生命和生存的需要及追求。人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需要空间接触。”也就是说,城市是人体的延伸。回到现代,斯皮罗·科斯托夫的《城市的形成》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都具备极强的学究味道和保守价值倾向。在他们的笔墨中城市就是承载和孕育人性的容器,甚至是冥想盆。他们将只有人类才有的“灵”赋予、寄托给了城市。芒福德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科斯托夫说:“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进而形成独特的城市性格,也就是说,城市早在以完整的设计形式被匠人落实之前就已蔓延,并抹去了图纸上优美规整的形态。即使是那些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的优秀城市设计案例,和那些通过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控制建立起来的地区,从高空看去,其边界早已与新城和郊野含混一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更加天然和难以捉摸的形状。
此为何意?其实就是抵制反人性的“华丽”,从日常寻觅创造力。芒福德、科斯托夫、简·雅各布斯、桑内特、藤本壮介,无一例外都喜欢有机生长、杂乱蔓延的价值美学,也就是“超越图纸”。而这显然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的身体隐喻不是一个路数。
另一条线索,是独立的身体史研究对城市的渐进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逐渐成为各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维度,衍生出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美学、身体叙事学、文学身体学等分支学科(一般统称为身体研究、身体学)。历史学研究范围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吸纳各学科研究方法为方法。自然科学兴起则有‘史学科学化’历程,社会科学鼎盛则有史学的‘经济学转向’‘社会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后现代思潮滥觞自必有包括史学的‘身体转向’‘语言学转向’等在内的所谓‘后现代转向’——‘身体史’便缓慢显影了:福柯本人的《惩罚与规训:监狱的诞生》《古典时代疯狂史》《性经验史》就是身体史最早的‘影像’”。福柯的重要性在于开启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研究,从此,身体成为运用后现代主义书写政治史的重要内容。
桑内特认为,“不管是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形式,身体政治都按照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建立了社会的规则。”书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段话:“集体的统治意象所引起的身体矛盾与暧昧,通过都市形式的改变与污损以及都市空间的破坏性使用,而在西方城市中显示出来。……整体性、一元性以及一贯性……是痛苦与不幸的根源。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凡是能接受这一点的人,对于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的理解,往往要比那些接受支配形式的人理解得更深刻。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作的神圣承诺。”《肉体与石头》这本书尝试要了解承诺是如何约定下来的,而后来又是如何被打破的,尤其这个过程的发生地点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城市,既可以作为权力所在,也可以以人本身的意象为模板,讲求一致性与整体性,意象在城市空间中不断分裂。
如果说福柯是“社会—权力—身体—疼痛”,桑内特就是“城市—权力—身体—疼痛”,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可以看作是身体权力书写的都市性延伸,是城市身体批判史或空间政治身体学。
感性复苏,回归价值
既然提到了权力,就必须回应下书本终章那宣言式的呐喊。桑内特的主张非常清冽。如同《城市发展史》和《城市文化》将芒福德的价值取向暴露到了极致。
《肉体与石头》的第十章和结论部分,桑内特呼吁我们去“拥抱痛苦”——起码我是这样理解的。通过感性的复苏,换回“灵觉”,这其实非常stoicism。回归价值,就是回归肉身以及通过肉身建立的秩序规范和溢出的灵性感知。
“舒适和快速是以麻木人的心灵和同情心为代价的。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描述,桑内特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理念却在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加速社会带来了异化和新的失控,桑内特说都市中那些“速度的激流”正在潜移默化中规训着人类,他倡导复兴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和过去的公共空间。那要不要放下元宇宙、智能屏幕、高速光纤和太空旅行呢?基于“高速”,桑内特提出一个“再现影像清单”的概念,与现象学中的“盈余”异曲同工。
桑内特不是纸面上的理想主义者,注重多样性,但更看重真实性,他影射了雅各布斯大加赞誉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现代都市,个人主义在发展,而个人在城市里则逐渐沉默了。街道、咖啡馆、百货公司、铁路、巴士以及地铁,都成了受人关注的场所而非谈话的地方。在现代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言语连接难以维系,城市里的个人这时看到身旁的场景所产生的同情心,也会因此变得短促——就像对于生活上的一张快照。”
但他们总归有共同的愿景,即尊重市民价值,注重社区网络,强调同理心,推崇烟火气的美好生活,将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容器仔细呵护,并保持深远的忧思——人类如何安放自身?想起了芒福德对“真东西”的描述,以及桑内特本人的宗教信仰,恍惚间,似乎那句话是真的:其实几千年来人类没有变,人性没有变,城市没有变,一切只是外在形式和技术工具的变幻而已。
桑内特的重要特点是不回避解决方案。他不是理论到理论的学者。在《肉体与石头》的最后,伴随着那些爆炸状的词句,感官退步、人类学介入、文明忧思、物质力量的增长、自我尊重的危机、自我意识和地位的混乱、公共和城市生活变动的形式,他终于点出了一种办法——“超越愉悦”的设计实践。我相信,这与他提出的“开放城市”三原则相勾连。
桑内特并不古板无趣,因为无论语言、形象还是主张都太美了。如果不信,且看我愿将之作为结尾的这段文字:“能够接受疼痛的身体才能算是市民的身体,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让疼痛在街道上展现出来,疼痛才会变得可以忍受——即便如此,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解释他或她对他人的感觉是什么。但是,身体仍可以遵循着这个市民轨道而行,只要它能认识到在社会上身体的痛苦是没有解药的,身体的不幸来自于别的地方,至于身体的痛苦则源自上帝要求流放者应一起生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