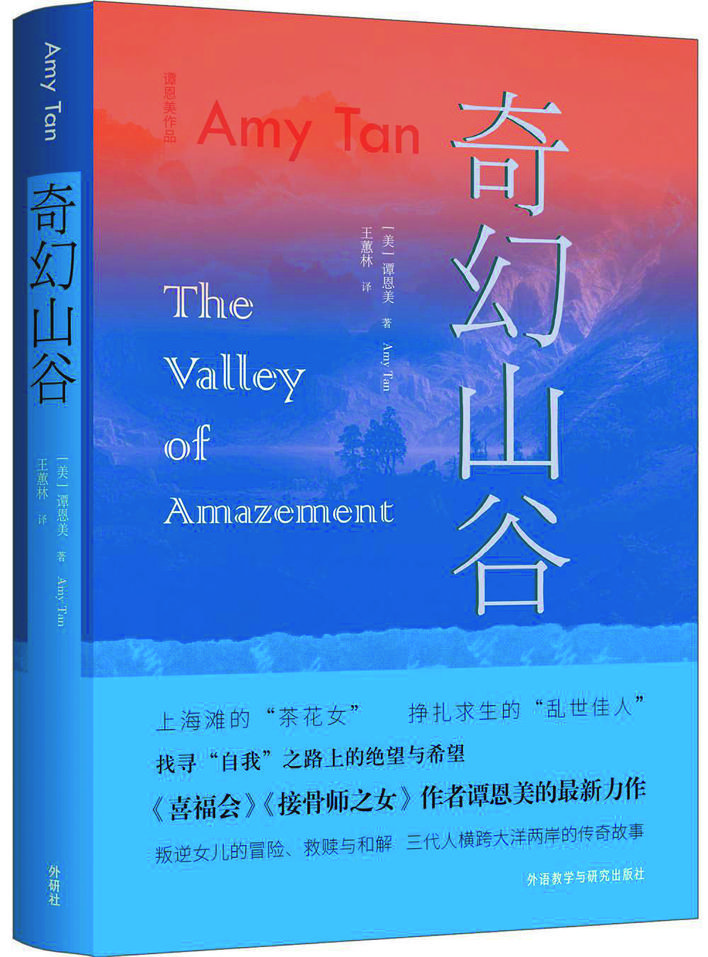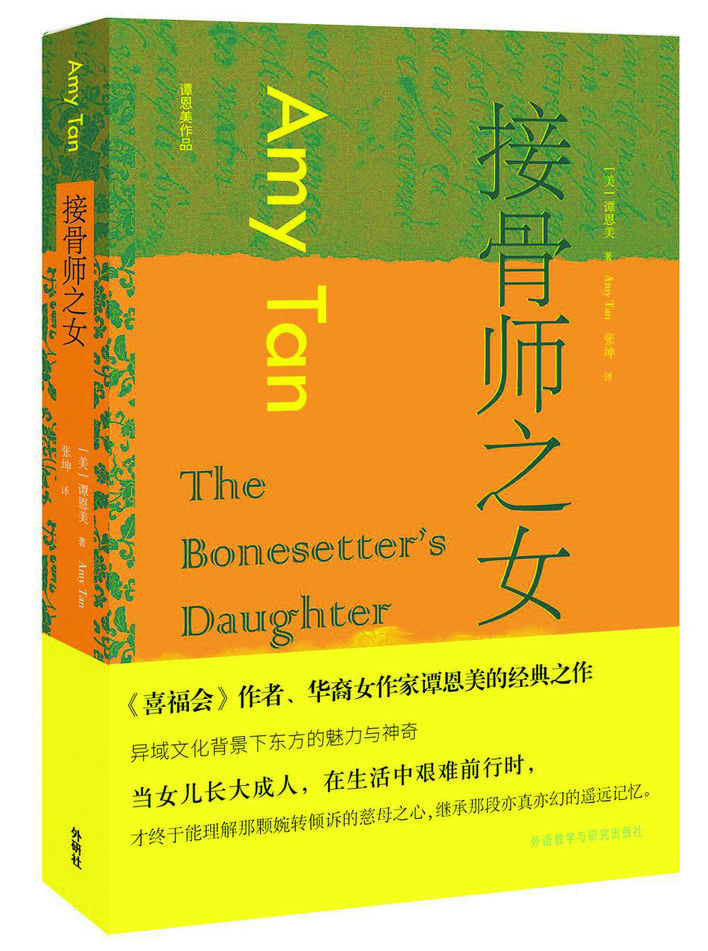王敬慧:在一次访谈中,你谈到库切的小说,你说在读完《耻》之后,你甚至想停止写作了。那本小说中的什么元素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和表述呢?
谭恩美:我钦佩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写作技巧。他可以毫无纰漏地讲述一个故事,叙述十分自然流畅。在这种清晰的叙述中,蕴涵的是他非常深刻的智慧和历史观,还有对社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理解。这些内容并不是被牵强地塞入故事之中。它们只是自然地出现在那里。故事的讲述也很直接,你会理解故事中这个人物和他的冲动。你可以看到人物的缺点如何指涉他所在国家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无法解决的局面会源源不断地带来更多可怕的后果。他无法阻止自己的不良行为。小说可以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让人们看清楚世界的危险是什么:种族主义,暴力,矛盾,歪曲的意图,挽救人们,同时摧毁他们的自我。拯救动物的人同时又是屠杀动物的刽子手。他把这些放进他的小说中,似乎毫不费力。我知道,这当然并非真正毫不费力。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就是这样的感觉。因此,当我读这样的小说时,我很烦恼,因为我没有写任何重要的东西。由于新的现实,我不得不写一本新书。我需要充分弄明白已发生的事情,还需要找到理解的方式,甚至还包括希望。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故事不能过于简单或陈腐——像什么美好战胜了邪恶、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了这类的故事。作品必须面对人类的黑暗,而不是说教,也不能嵌入结论或自成一体的哲学,因为那样的话,故事只会成为宣教。我想写一个关于人的私密的故事,这些人有缺陷和偏见,并生活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之中。
王敬慧:我最近刚翻译完库切最新的小说《耶稣之死》。他的小说不会用过多的情节,但是就如同你所说的,他轻松、自然地让你从小说中意识到一些事情。
谭恩美:我所读过的他的作品,没有一本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认为很多写宏大主题的作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写作起就带上了一种什么都知道的语调。他们似乎想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并且要用自己的认知来教化读者。我所欣赏的故事里,有一种声音对我说,故事自己也在探寻中,作者和读者将共同达到那个理解点。
王敬慧:说到小说创作,在《大师课》的预告片中,你讲的一句非常深刻:有些人认为小说是一堆谎言,但你认为小说是找出真相的最好方法之一。所以我在想,你自己是如何用这种“通过说谎讲真相”的艺术手段向读者表述你小说中的真相?
谭恩美: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谎言的目的是欺骗人,然后自己获利,谎言是在杜撰一个所发生事情的另外一个版本。小说是要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创造一个小说的世界,里面的人物是可信的,场景是可能的,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也是不可避免的。读者会自愿搁置自己的不信任,进入小说世界来获得消遣,同时找到小说中与他发生共鸣的真。所以小说中的真不是事实(facts),而是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作为一个作家,当你发现了个人的真,如果你将其变得具体化,并能够被感知,你也可以提供一种普世的真理。我想那就是读者对《喜福会》的感觉。我所写的内容,也是其他女人普遍感觉到的内容。
王敬慧:阅读中,我认为你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展现给读者大众,比如《奇幻山谷》这部小说,能帮助读者了解旧上海的妓女文化,这是非常新鲜有趣的阅读体验。
谭恩美: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写妓女的故事吗?
王敬慧:是因为你外婆的那张照片吗?
谭恩美:是的,从我外婆的那张照片看,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可能做过妓女。但是最初即便是那样想想都会感觉我在亵渎她,我其实曾抗拒把这个小说的背景设定为妓院。我自己就会第一个站出来质疑说用这样的异域趣闻是一个不好的套路。但是我不得不打破这种束缚。这是曾发生在我们家族的秘密,这个历史影响了我母亲和我的人生,所以我想要去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证明她的过去,而是对“她是谁”的思考。
王敬慧:记得在《大师课》的讲解中,你提到曾用放大镜来观察照片上的服饰细节,你的确观察得非常细致。
谭恩美:在我开始写《喜福会》的时候,我也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点紧张,我要写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而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直接经验,所以我怎么能写过去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呢?那么,我只能以我对母亲和家人的了解,从那个角度来写,写我对我长大的那个家庭的理解,他们所说过的话和所想的事情。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后,我也很感激,没有很多中国读者质疑说根本不是这样。反倒是,我记得有一位读者说我所描写过的某个城镇就像现实中一个城镇许多年前的样子。但实际上,那只是我想象的一个城镇,一个遭受洪灾的城镇。
王敬慧:是的,这是一种非凡的写作能力,你能够描述一些你并非亲身经历的事情,但其他人会证明你所描述的和他亲身经历的现实情况是一样的。这有着一种“毫不费力”的感觉,就像被你翻译成“道”的那种“毫不费力”。
谭恩美:我母亲读了我的第一本小说之后就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她觉得是外婆的幽灵告诉了我一切,并一直追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发生过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们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呢?我只能说这是想象基础上的创作。但是我不得不敞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得到某种帮助。某种意识让我以某种方式思考并沿着那个方向继续下去。为此,无论它来自哪里,我都心存感激。
王敬慧:在《奇幻山谷》这本书的准备和资料查找过程中,你有读过《海上花列传》吗?
谭恩美:是的,我读过。
王敬慧:那本书被改编成了电影。当我读完你的《奇幻山谷》,感觉它像是《海上花列传》的海外版续集,而且场面更宏大和异域风情化,所以感觉这本书可以很优美地展现在大银幕上。
谭恩美:我读过《海上花列传》,也看过电影《海上花》,真的很美。让我既惊讶又高兴的是,电影里的角色说上海话,那是我母亲所讲的方言。里面很多行为举止和语调都是典型的上海范儿,就像我母亲和我那些上海亲戚说话的样子。因此我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尤其当我知道里面很多演员都不是上海人的时候,因为要演上海人,他们就必须学说上海话,这一点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王敬慧:关于人物原型,我还想知道,之前我们谈论过的《接骨师之女》里的青年人开京,现实生活里有谁给了你创作这个人物的灵感吗?
谭恩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对我来说就像精神导师,他已经过世了,但我们曾一起到中国待过一段时间,他给我讲过很多东西,比如园林,它们的意义、构造过程、所代表的传统以及什么是中国精神。这些讲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让我明白了石头的选择和摆设,小径方向设计的意义等等。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精神层面上的中国文化。我们也会一起去逛园林和博物馆,看那些来自其他文化的绘画和建筑。但是,如果你剥开外壳,我是说比喻义的外壳,你会看到里面中国内涵的那个层面。中国的那个层面一直在那儿,它从一开始就在那儿,那些人试图在其上面涂抹将其变成另一种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依旧在那儿。我的这位朋友向我解释中国文化的坚韧,不论是谁用什么方法试图掩盖它,中国精神总会保持在那里。我觉得现在也是如此,在中国,有很多被人们称作是西式的东西,但事实上,中国早就走在前面了,远远超越了“西式”的那个标准。中国不是西方。中国是聚集发起,而不是改造。
我总是在思考中国对“道”的理解。我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区,我的一个朋友是那里的馆长,他的介绍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那些艺术品。看着这些画作,我在想为什么一些艺术家就能开某种艺术风格的先河并有创见。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先河之后,其他人都追随效仿:效仿者会尝试着去模仿或捕捉流派里的某种精髓,也许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甚至做到很相似;也许他们能够把它做得比较华丽,并带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特点;也可能很神乎其神,因为你从中感到的内容是如此广阔的,但是他们的创作却永远也不会像原创者那样毫不费力,自然流露。所以每当我看到中国艺术时,就会想到这一点,这种“毫不费力”与当时艺术家所拥有的某种精神有关。
王敬慧:你的《拯救溺水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里,画廊看展的章节也有这种对艺术感受的描写,现在我们来谈谈《拯救溺水之鱼》这本书的名字吧。这个书名有一种矛盾的内涵,一条鱼怎么会溺水?你是怎样想到这个书名的?
谭恩美:首先,我曾听别人在谈论从中国来美国的移民时说过,“如果要救这些移民,那就要照顾他们,安顿他们的余生”。说这话的人里,有些人是恶意的,像是把这事当成了负担,也有些人是好意的,认为多一些人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发现,这与人们开始做任何事之前的意图有关。当你说要救一些人的时候,你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看到有个人快淹死了、你知道救他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你生活的负担,你还会费劲儿去救他吗?我曾在某处看过关于“拯救溺水之鱼”的表述,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有关“意图”的故事,明明是想着“我要去做一件好事”, 结果却会很糟糕。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生活中对待事情的意图——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别人。意图或动机是什么?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如果结果出人意料的好,但这并不是你原本计划的,你是不是应该归功于自己?我看到很多人把日常生活中碰巧发生的事归功于自己,他们会说,是的,多亏了我。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你能说“我没想过会这么糟糕”吗?然后就不是你的错了吗?这就要提到“责任”这个问题了,后果是由经历这一切的人来承担吗?他们就该受到这些影响吗?如果你做了一件你没想过结果会很糟糕的事,但有人因此承担了后果,难道你就没有责任了吗?这也是我选择“拯救水中之鱼”这一意象的根本原因——把鱼从水里拿出来,让它们扑腾着、无法呼吸,最终因为离水缺氧而死去,而有人还在说他们的意图明明是在救那些水里的鱼。所以,对“意图”的本质思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王敬慧:是的,实际上当我读到小说中“救鱼”这个寓言故事时,我的感受是那个看起来最虔诚的人其实在惺惺作态,事实上,他是要从“救鱼”中获利的。
谭恩美:对,是这样的。在创作此书时,我看到太多的“意图”的被利用,不仅是世界层面上,在个体之间也是如此。当有人说: “我没想伤害你”,你要明白那个人是不想要承担责任,而事实上,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自己。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问,尤其是现在的美国。当你看着周遭发生的事情,你必须问,政府的这些政客在做什么?他们做这些事的意图是什么?其实他们是非常自私的。他们说起来像是做着一些好事,但实际是在做一些坏事。
我所关注的是意图、过程、责任以及结果这一整套问题,不仅仅是用来看整个世界,还有自己的生活。人们对我说,我为其他亚裔美籍作家开了先河,或者我成功地做了这个,那个。但这都不是我写书的本意,我是为自己而写作,是为了理解我的母亲而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写作,我从不会说我写作是为了给其他作家打破阻碍。所以人们说这些的时候,我试着跟他们解释那不是我的功劳。他们总是“不不不”。现在我只会说:“哦,谢谢,有这样的结果我很开心。”也有人对我说其他一些事,比如,“读了你的书,我离开了我的丈夫”。我心里想,好吧,我对此并不负责。我写此书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离婚。或许对那个女读者来说,离婚是件好事,但这并不归功于我,也不是我的错。
王敬慧:你在回忆录里认为,“写作是为自己而写,写关于自己生活的事……不论别人怎么谈论、解读你,那都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你还认为,“将一个人的档案送到图书馆并不意味着就此获得了象征性的不朽,这是一种永恒的误读”。你如何看待写作与误读的关系?
谭恩美:关于我在写什么,我的意图是什么,我看过的评论和听过的话还没有完全符合我的想法的。不了解我创作原因,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别人怎么能知道我创作的意图呢?他们又没有经历我曾经的生活。他们没有看到过我外婆的照片,感到那样的震惊。他们不会对忍辱负重有相同反应。我不是在批评人们所写的关于我作品的评论,只是他们并不明白我。而完全的明白是不可能的。
(王敬慧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