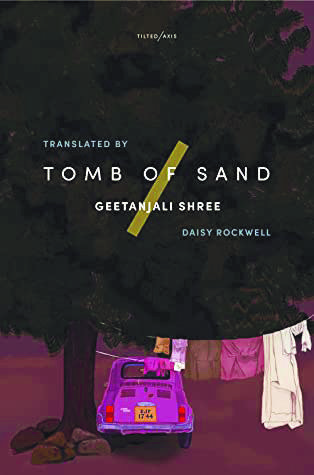2022年5月26日,印度印地语作家吉丹贾丽·斯里(Geetanjali Shree)凭长篇小说《沙墓》获得2022年国际布克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印度/南亚本土语种作家,英译者黛西·罗克韦尔共同获奖。《沙墓》的印地语原版于2018年问世,由印度知名印地语出版机构——国莲出版社(Rajkamal Prakashan)出版。其英译本由美国翻译家黛西·罗克韦尔从印地语直接译出,2021年由倾斜轴出版社(Tilted Axis)推出。颁奖词评价《沙墓》称:“这是一部迷人、有趣且极富原创性的小说,同时也是一声急切而及时的反抗,反抗那些横亘于宗教、国家、性别之间的界限和壁垒的破坏性影响。”
吉丹贾丽·斯里,1957年出生于印度北方邦曼尼普里(Mainpuri)的一个印度教婆罗门家庭。她一方面在英语学校接受精英教育,另一方面也深受印地语腹地文化氛围的影响,从小就对文学和写作展现出非凡的兴趣。她原名Geetanjali Pandey,Shree是母亲的姓氏,在开始文学创作后她就以母亲的名字作为笔名。吉丹贾丽·斯里在德里完成了大学学业,攻读的方向是印度现代史,随后取得了印度历史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她在新德里的国立伊斯兰大学和扎基尔·侯赛因学院用英语教授历史的同时,用印地语进行写作,后来成为全职作家。
吉丹贾丽·斯里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避罗叶》发表于著名印地语文学杂志《天鹅》。1991年,她凭借短篇小说集《回声》正式打入印地语文学界。在随后的30年中,她一共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分别是《母亲》《那年我们的城市》《隐匿者》《空地》和《沙墓》。其中,《母亲》讲述了印度北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故事,还被译为韩语、德语、法语等诸多语言版本。《那年我们的城市》讲述了巴布里清真寺被摧毁之后的北印度发生的故事。《空地》则从一所大学咖啡馆爆炸案入手,讲述了第19个受害者男孩的生平记忆和遗体被带回家后的故事,该书出版后被译为乌尔都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等版本。《沙墓》的英译本则是她的书第一次在英国出版。身为历史学博士,吉丹贾丽·斯里在文学创作之余也从事大量非虚构写作,她与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孙女是朋友,本人也进行了很多关于普列姆昌德的研究,著有《两个世界之间:普列姆昌德思想传记》。
小说《沙墓》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背》《阳光》和《前线》。三个部分的篇幅大致相当,每个部分又分为若干章节。该小说以北印度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因丈夫离世而深陷抑郁的80岁妇女改头换面、谋取新生的故事。她在与“离经叛道”的女性主义者女儿生活在一起后逐渐变得“现代化”,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还与一位“海吉拉”(跨性别者)罗希建立友谊,甚至在罗希死后于耄耋之年执意前往巴基斯坦,最终倒在边境的子弹之下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众多角色都没有确切的姓名,这样的安排使得书中的角色不仅仅是个体的代表,更是群体的象征。
文本中存在着多重话语、多条叙事线索并置的现象,从而使作家的创作思想得以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分隔”(partition)是《沙墓》关涉的根本议题,在书中不单指印巴两国的“分治”,也指任何其他形式的分离,包括性别的分离、种姓的分离、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分离、宗教的分离、文明的分离等。
男性与女性在性别上的分离是小说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母亲在80岁之前是奉献自我的传统印度女性角色,女儿则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女性主义者。她追求前卫的生活,离家后独自靠写作为生,甚至敢在公共场合公开谈论女性的意识、性、女性的独立等观点,出名后她住在豪华的公寓里,还经常去周游世界。社会上充满了对女儿的批评,觉得她的钱来路不明且过于肆意妄为。因此儿子告诫母亲不要跟女儿交谈,以免牵连到他们家人。母亲在内心同情女儿,悲哀地认为女性的一生都在被审视,女儿所有不符合传统印度女性的尝试和行为都被人们认为是“背离传统的”和“不可接受的”,其根源是印度文化语境下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女性和男性的性格和社会分工的分离。
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分离也是小说书写的重要内容。聚餐时儿子和儿媳因菜品争吵,儿子认为西式的餐点更显尊贵;女儿的白人朋友穿着昂贵的西装和领带参加聚餐,人们也认为她的身份和地位比穿纱丽的人更高。这样的认知生动再现了印度大众心中普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英国在印度百年的统治给印度留下了深刻的“英式”烙印,而印巴分治的一手操办者也是英国政府,殖民者在教派冲突中彰显了帝国主义的荣光,巩固了英印政府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将权力延伸至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即使在独立建国后仍有许多印度人依然以自己的国家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感到自豪,西方一切都优于东方的观点也成为印度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观念。
贯穿《沙墓》一书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是生与死的“分离”,如何面对生命中接二连三的生离死别以及治愈与亲人生死相隔的痛苦。书的开篇就介绍主人公母亲因为和丈夫的生离死别而痛不欲生,她缩在被窝,或躲进水泥墙里,借此躲避死亡的苦厄。“一个男人,即使在死亡时,人们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但不管他是否已经死了,他的遗孀似乎肯定已经死了。”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反思自己的一生,她已经厌倦了为他人而活,为此她绝食,不肯出门,甚至闹过失踪,想借此摆脱生活的桎梏。后来女儿将母亲带到自己的公寓居住,在公寓里二人的身份却发生了微妙的对调,母亲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女儿反倒扮演了照顾人的“母亲”角色。女儿允许母亲改变着装,交新朋友,母亲在女儿的照顾下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母亲的饮食起居和对外界的凝视,在互换的角色中,母亲愈发自由,她和“海吉拉”(跨性别者)罗希成为朋友。罗希是一名乐观向上的“海吉拉”,她勤恳工作,热心公益,心灵手巧,乐于助人,热爱生活。虽然她在社会中属于少数群体,饱遭歧视,但罗希对生活的不公敢于奋起反抗,活得灿烂自由。然而社会对她不曾有过丝毫宽宥,在罗希和租客发生纠纷被残忍杀害后,警察因其跨性别者的身份没有进行公正的处理。罗希生前遭受谩骂凌辱,横遭意外后也因“海吉拉”的身份无人为其伸张正义,杀人者也并未受到惩罚。作者在这里通过罗希被区别、冷漠对待,反映出性别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群体之间的分离和隔阂。虽然现代社会允许人们有权利选择第三性别,但性别之间的分离导致的歧视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罗希之死使母亲遭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她千辛万苦树立起的对生活的热爱和期许又一次被摧毁。
从根本上,小说指向更宏大、更具有野心的题旨:政治的分离、阶级的分离、宗教的分离,甚至也不单单局限于“印巴分治”这一个事件,而是人类由于战争造成文明文化的分离。作者在叙述中大量插入历史和政治事件,比如: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炸毁巴米扬大佛、2007年印巴友谊快线爆炸案……国际布克奖评委会称赞《沙墓》“针对横亘于宗教、国家、性别之间的破坏性壁垒提出了坚定而及时的抗议”。小说生动展现了作家对政治的极大关切,罗希死后,耄耋之年的母亲为了实现她的愿望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前往巴基斯坦,这是一种真实的“跨越边界”。她在印巴边境的紧张对峙中思考“边界”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最终死在印巴边境。书中提到杀死母亲的子弹时这样写到:“我感觉这颗子弹像是从另一个世纪发射的,但并没有停留在那个世纪。它一直袭击那些后来的人,让他们一直受到伤害。”这颗子弹象征着由印巴分治引发的痛苦战争记忆和难以磨灭的创伤。据统计,从1947年8月起至1948年春,共有60余万人于教派冲突中丧生。“从巴基斯坦逃往印度的锡克教徒、印度教徒与从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大约各有550万人,这还不包括从东孟加拉、信德逃往印度的难民,前者约为125万人,后者约为400万人”(林承节《印度史》397)。这场持续数月的人间惨剧给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抹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战争引发的苦难也成为数代人难以忘怀的痛苦记忆,而分治引发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一直延续至今。开伯尔的监狱中阿里·安瓦尔审讯母亲,他指责母亲没有签证越过边界是违法的行为,而母亲反问他到底什么是边界,怎么定义边界?母亲认为任何东西都有边界,但边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可以跨越的、是由爱组成的。边境应该是连接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的桥梁。是阿里·安瓦尔这样的人让印巴边境成了仇恨的源头,而血流成河的边境只会有一个后果,就是在血色弥漫中制造更多的杀戮和牺牲。作者在书中批判政治的分离和宗教的分离给民众造成的苦难,而这种苦难仍被有心人延续着、继续书写着,从未停止。作者呼吁人们跨越宗教的藩篱,重新以爱筑成沟通的桥梁。
这本小说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相当沉重的,例如分治、女性、宗教、屠杀、人权等等。然而,全书语言诙谐幽默,读起来轻松可爱,颇具趣味性。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却用简单的故事引发读者进行关于宏大主题的思考。作者对人类由于战争造成文明文化的分离的关切是这部作品的升华之处,也给予读者启迪和寻求文化共存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