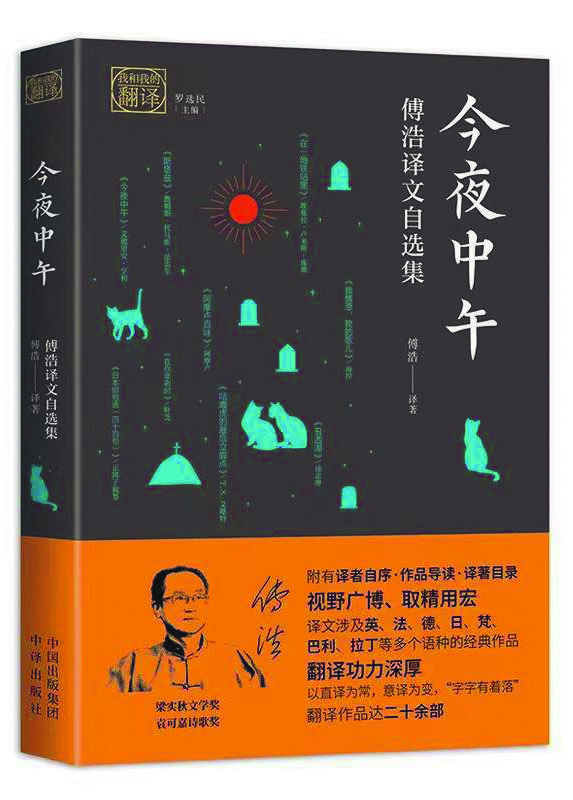我常说,我是翻译实践者,不是翻译研究者。犹如作者及其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译者及其译作则是翻译研究的对象。我对各种哲学性和文化性的抽象理论不感兴趣,而只重视翻译经验谈;对翻译批评持谨慎态度,因为我认为最好的批评者实践水平应高于被批评者,应有能力拿出更好的译文。除非必要,我不轻易批评同行,因为我是运动员,不是裁判员或评论员。诚如鲁迅所说,他不相信“小说法程”之类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相信“翻译技巧”之类的东西。我的技巧说来很简单,做到却不容易。我常对学生说:“汝果欲学译,功夫在译外。”翻译不用特意学,只要你能用两种语言的各种文体熟练写作,自然就会翻译了。再找已有的多种译本对比原文和自己的习作来揣摩,自会有得,即可入手。这就像学写作或学画画,与其研读理论,不如观摩范本来得便捷。一般理论是用来提高认识,开拓思路的,是后行的,不是先行的。真正有用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方法和方针,属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而非成果。
翻译犹如画画,初学往往崇尚意译,实际上是为功力不济找借口,这与文人画多写意是同样道理。随着功力增长,描摹愈来愈工细,自然就愈接近直译了。所谓直译,借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说,就是“以最佳语序排列的最佳词语”。具体来说,即以句子为单位,语序符合译入语习惯,同时较诸原文,字字有着落,不增不减,语气相似,文体相当。检测功力的一个指标是词典。初学用双语词典(或叫翻译词典),例如英汉词典,进而用双解词典,最后用单语词典,即英英词典。抱一本双语词典干活不能叫翻译,只能叫搬运,因为其中的单词是词典编纂者翻译的,所谓译者只是把词典的译文照搬到自己的译文中而已。这样的翻译,叫做词典翻译,功劳应该一半属于词典编纂者。能够全程用单语词典做翻译才算是真正的翻译。而具体能用什么词典也是一个指标。翻译20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应该用《牛津英语词典》,20世纪以来的则辅以《新牛津英语词典》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翻译美国文学应该用《第三国际韦氏英语词典》,辅以《牛津美语词典》。这些是顶级配置,其余等而下之,可以不论矣。词典选用不当,许多词义都查不到,怎么可能译得正确呢?养成用单语词典做翻译的习惯可以大幅度提高词义辨析能力,而词义辨析能力是译者功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其高低与选词正确率的高低成正比。至于母语,译者掌握的词汇量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足以不用查词典,词典只是用来印证不确定的措词的。仅用《现代汉语词典》不够,最好用《汉语大词典》,辅以《辞源》《辞海》。
翻译是一门手艺,凡手艺必有技术,也可以达到艺术的高度。技术未必是艺术,而艺术必然包含技术。技术的运用即艺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前所说,翻译与写作一样,如果能达到文体自觉,可以说就进入艺术境界了,只不过翻译需要达到两种语言的文体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其它地区付给译者的稿酬要倍于作者所得的原因。要熟悉各类文体,除了广泛阅读,多见多识,别无捷径。文体以雅俗论,不以古今论,尽管有些词语会因古旧而显得雅。所以,翻译中的文体对应应该是雅俗等级的相应,而非时代早晚的相应。用“诗经体”译《斯卡布罗集市》是不错的,因为二者文类皆属民歌;译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则未必对,尽管时代相近。有的译者所谓语感只不过仅指译文的语感而已,而非译文与原文间的文体对应。对两种语言中各类文体掌握不足,就会造成文体不相应。
译者是手艺人,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翻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永远是第二位的。他是站在发言者身后的那个人。如果他试图站到前面来,就是僭越;如果他试图说他自己的话,就是背叛。他可以用木雕或剪纸的形式逼肖《清明上河图》,但不可以把它临摹成泼墨大写意。他应该是个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而不应是个本色演员,演谁都像自己。有的诗人译者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译成自己惯写的自由诗体;有的学人译者把但丁的《神曲》译成散文体。这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最好的,因为文类不相应,说明译者力有未逮。译者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逼近,而非远离原文,在于创造贴切的妙译,而非所谓“超越原文”的蛇足,犹如画画写生或临摹,无论形似还是神似,总要以似为能事;不似,只能说明功力不到,再怎么利口逞辩,也无济于事。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原文为参照而后者没有。所谓意译一旦超出了可识别范围就不再是翻译,而是近乎剽窃的创作了。仿作和改作则是另一回事。埃玆拉·庞德的《震旦集》属于脱离原文对译文润色加工的产物,他所做的相当于古代译场中“润文”者,或现代出版界不懂原文的编辑所做的工作。若奉如此“译品”为圭臬,就会偏离译学正道,因为它不以原文为参照。
译者须另有专业,翻译应居于业余地位,否则会沦为无所不译的翻译匠。而正是这专业决定了译者的翻译领域,例如,法学译者须以法学为专业,医学译者须以医学为专业,文学译者当然须以文学为专业。而即便是以文学为专业的译者,也不是什么样式的文学作品都译得好的。仅以翻译为专业的翻译匠则无论译何种其他专业文献多半会让人觉得不可靠,而且其译作往往有一股说不出的“匠气”,犹如文人画家眼里的某些专业画家的作品那样。
翻译又是涉外文献研究的基本功,是细读的细读,若想换一种语言毫无遗漏地准确转述,非吃透原文原义不可。钱锺书有言:“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说句玩笑话,钱先生这说的是直译,若是意译,还是绕得过去的。我曾在一次讲座上说:“翻译应以直译为常。直译就像直道而行,遇到障碍,就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若障碍大,就再退一步,总之要贴着边绕,不能跑远了,这就是直译,意译是变。然后还要再回到直道上来,跑远了就不是翻译了。”翻译即换一种语言转述(英语“translate”的本义)。转述有两面:理解和表达。理解了,表达不好,是译入语能力有欠缺;未解或误解了,乱表达,是译出语能力有欠缺;既不解又表达不好,是两者都有欠缺。总之,译出语和译入语能力,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要大致相当,若过于悬殊,必然会失衡。尽可能均衡提高两种语言的词汇储备、词义辨析能力、文体意识、写作能力,是译者毕生都需要努力的,而这是无止境的。
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作品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好在原文永远在那儿,可以照着不断修改,但也不得不随时接受读者检验。自觉的译者往往能够自行发现自己的错误,欣喜于自我的长进,否则也会欢迎真实中肯的批评。闻过则喜,知过必改,修辞以立诚,这就近乎修行,由技而入道了。
一般来说,手艺人很少公开评论人家的作品,更少谈论自家的技术秘诀。以上所说,不过是些牢骚以及与同道共勉的话。作为手艺人,也许我说得已经太多了,不如还是让作品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