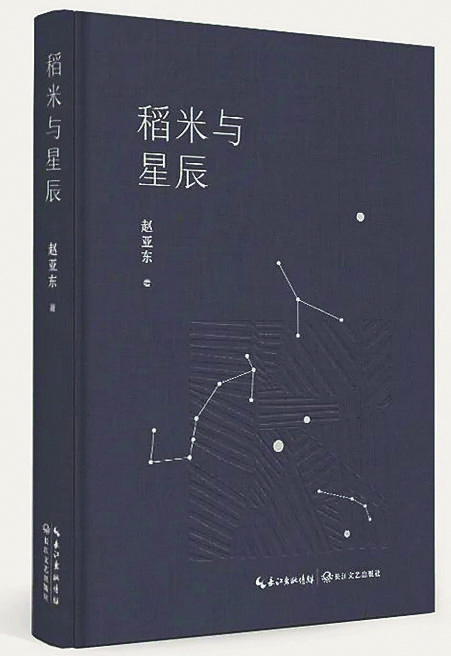让诗在内心世界记录生命的真实和丰收,这是赵亚东诗艺不断变化中的“恒常”;而寻找有价值的形式,书写有意义的生活,则是他孜孜以求的“新变”。新近出版的诗集《稻米与星辰》呈现了上述特质。
赵亚东诗歌的形象、视象、意象总是与乡土世界紧密纠缠。“土豆”“马厩”“村庄”等意象频繁出现,频繁梦见乡下的动植物,要多于梦见城市的人造景观。赵亚东将早年对乡土世界的情绪藏在深层的潜意识中,习惯从熟悉的乡土世界寻找客观对应物。他有大量表现乡村世界生死哀荣的作品,不但一腔热忱记述物事,还怀恋美好的人事。《在乌兰诺尔》《歇马滩》等诗作充满温馨温暖之气,美好的回忆炊烟般向上攀升,诗人在精神还乡中抵达自我救赎。
丰盈多姿的画面感,不凡的色彩表现与色调应用,是阅读亚东诗歌的强烈印象。亚东对乡村风物的热恋一如既往,他的诸多乡村静态摹写,画面感强烈。“真好啊,谷子一低头/小米就要被生下来”,从《野稻子》一诗可以窥见亚东诗歌的写作意义,他在迅捷之间让观察对象由“心入于境”而抵达“神会于物”,有时他给读者的是一幅淡淡忧伤的山水画,有时给读者的是满纸悲欣的大写意。
追问乡关何处,铭记渐渐稀释的乡愁,这些复杂的情愫统一于赵亚东的诗歌中。“夜幕缓缓合上,我追逐着最后一道光/寻找那双操纵时间的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却和那个黑夜中的陌生人撞在一起”。这些诗句由物及象,意象、幻象交织却朴素有力,个体的经验成为很多人接受的普遍经验。赵亚东诗歌创作中多次提及的“飘荡河”“乌兰诺尔”等精神乡土,是将他人的故乡视为自己的原乡。此种精神地域诗歌写作,已非乡愁与乡悲的简单表现了。
寻找有价值的形式,书写有意义的生活,一直是赵亚东孜孜以求的诗艺方向。赵亚东乐于使用幻象,生成的诗意颇似神话传说式的移梦造境。造境,是诗人开拓主观精神世界的艺术创造活动。亚东凭借自身对“生活幻象”的体验,融合了自我情感、道德判断、审美认知等,构筑了诗歌中不同的意象表达,艺术地实现了从现实之境向心灵世界的幻象之境的跨越。
赵亚东的诗作经常主客易位,“被显现的客体就是显现的主体”,他也将这些落实为诗歌创作中的虚实处理。《我在这世间两手空空》是虚实分写,情景互见;《地址不详》是实象涵虚,融情入景;《藏不住的影子》《札记》等是虚中有实、景藏情中。“笔着于纸有虚有实”才妙,虚实的和谐应用才会让诗艺飞升,正如范玑在《过云庐画论》所说,“人知无笔墨处为虚,不知实处亦不离虚”。
诗人总是难以割舍生活予他的苦难,更愿意视之为写作的富矿、诗意的缘起。赵亚东的疼痛时潜时隐,在皮里腠外如影随形,在灵魂里游荡。一方面,他希冀从苦难中炼金,于蚌壳里磨亮珍珠的光泽;另一方面,诗人渴盼让生活生出双翼,任凭心灵自由飞翔。亚东的诗更像是一个美的矛盾体。
跳出摹写生活、直诉现实的经验书写轨迹,将超验作为观照存在的视角,无疑是赵亚东近些年诗歌创作的重要探索。他早年的诗句还带着清晰的想象痕迹,如“白天的尘埃在夜里转身,一个人/全身的血也比不上那颗醒着的露珠/这个城市轻得可以被一只蜻蜓驮向远方”“那些干净的燕子,在高压线感受着远方的震颤”,这些诗句重视想象和节奏,对第一手经验的处理让诗歌有了动人的力量。《暮雨》等近作不断刷新既定的经验,前置主体的感受,从而获得全新的审美经验。“一滴清凉的泪水,从叶脉的深处滑落/刚好照亮了松针上的火焰”,这样的诗句化熟悉为新奇,通过陌生化激发诗人艺术上高妙的领悟。
在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赵亚东有自己的探索。《祭外婆帖》是一篇佳作,它深接地气,在简洁的叙事中传达出复杂的人生认知,显示了深邃而持久的力量。《二姑》《妈妈草》《刘晓静》等作品让人感受到草芽拱开硬土壳的微弱力量、花香弥漫世界的温柔力量、石头醒来的记忆力量。而那些回忆少年伙伴的系列诗章,带着朴素的情感和冷静的叙述,一种沉静内敛的中年味道跃然纸上。早年的《黑河信札》《和卓卓一起散步》等长诗尚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诗人还仅仅把叙事作为一种手段,作为抒情的有效补充。近年来,叙述在赵亚东诗歌里变为一种主观判断,说什么、怎么说等叙事因素带着深厚的阅历与理性认知。亚东遵从内心的需要,将青春的大赋改写为风霜雨雪的小令。他沉向生活的诗歌,开掘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后的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