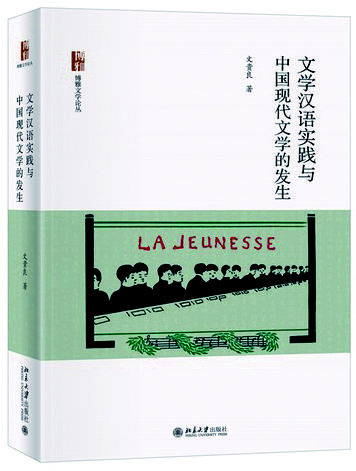文贵良新著《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中国现代文学创生期十位“核心作家”为例证,描述汉语实践的形态,揭示汉语造型的特质,呈现、总结文学形式的历史变迁和文学汉语的价值观念。从《话语与生存》《话语与文学》《以语言为核》到《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文贵良在语言变革领域内细作深耕,而由“话语生存论”发展到“文学汉语实践”也是一脉贯穿:话语以语言为基准,以晚清以来书面语的现代变化为历史坐标,总要回到语境中去清理语言形态的发展,总要重返现代书面汉语的个体创造的历史现场。
本书最富创获之处、也作为全书论述重点的是晚清至“五四”时期“轴心作家群”的文学汉语实践,他们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辉、胡适、鲁迅、周作人。这十位作家的思想与立场歧异,汉字汉语观和汉语造型千差万别,对白话文学也各有向背,但是他们的文学汉语实践,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形成和基本样貌。如果将文学汉语和现代文学理解为一条交汇的河流,那么这十位作家是矗立在源头的、齐格蒙·鲍曼意义上的现代立法者,他们对水质、流向与航道的疏浚与规定,迄今依然影响着我们。“文学汉语实践”成立的逻辑之一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理解为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寄生共存”(胡适所谓“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而这一命题逻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应并不是天然的,需要作者严密论证。在我看来,本书以黄遵宪开篇即为挑战。周作人说佩服黄遵宪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钱钟书批评黄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这两位对黄遵宪作品的“文学性”都颇有微词。文贵良则是将《日本杂事诗》的“本文”与“注释”既合而观之又分而论之。在书写形式上,作为本文的诗歌是主,自注居次,“但是在塑造新词和信息量的提供上,自注反而成为比本文更重要的部分,原因在于作为本文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巨大限制,而自注的散体形式则有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在对新理致的表达上,自注的散体形式也胜于诗歌”,经由这番独辟蹊径的阐述,文贵良指认“‘本文—注释’的表达方式是晚清以来汉语欧化的最初形式,是晚清以来文学汉语现代发展的起点”。
实践总是基于某个作家的具体实践,研究对象的确立,决定了本书主体以学案方式展开,回归语言本位,耐心研讨十位作家的汉语造型(“理”,即语言要素与语言造型)、主体意识(“情”,即情感取向与价值取向)与文学形式(“文”,即文类与风格)。六百余页的皇皇巨著,完全以细腻的语文学式学案来结撰,在今天的研究风气中实在不多见。中国古代,以文字训诂为主的小学无疑是人文研习的起点与基础,所以章太炎一再申明求学之次第与序进:“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今之学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记诵,能记诵者不皆能识字,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章太炎:《救学弊论》)在转型期,章太炎已敏感语言文字研究之于人文学科的根本意义和指导价值的式微,而近年来“无源之水”式的研究更是日渐风行,进入微观语言层面的赏辞析义,似乎是壮夫不为的小道;我们很轻易地跳过基础的语言文字与具体文本,上升到“宏大问题”的研究,《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示来者以轨辙之处,首先正在于“对言词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顺便说一句,上述文学汉语的“有情”一维,不妨视作对“话语生存论”的接续与呼应:“话语的分析必须回到当下的人,回到主体,回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展露”(文贵良:《话语与生存》),故而“话语生存论”打通语言形式特征与主体存在方式,强调主体置身特殊境遇(比如战争)中的言说与生存方式;文学汉语实践的研究同样关注汉语对汉语言说者自身生存体验的呈现与调理,文贵良在新著中解析王国维“我”与“人间”对立的主体意志,将林纾古文“抵制—开放”的结构视作对其生命意识内部“畏—狂”的人格结构的隐隐应和,都是旨趣相同的笔墨。
《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打通“晚清”和“五四”的努力也值得关注。很长时间以来,“五四文学革命”为代表的新文学实践如同发射炬火的灯塔一般为人瞩目,而此前以“文学界革命”为代表的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形象则如同前史一般轮廓模糊。而本书一半以上的研究对象以“五四”之前为主要历史舞台。即便是对于鲁迅,本书也以大量篇幅去考究其在晚清民初的汉语实践,鲁迅此期间在准白话译述、文言翻译及文言创作的三重汉语实践中“锤炼书面白话、吸收西方标点符号、怀疑语言的可信度、合理设置对话与场面、揭示隐秘的心理活动”,直到等来《狂人日记》的飞跃。更可贵的是,文贵良以“轴心作家群”为例,将“晚清”对语言异质性的容受联系到“五四”白话立场,“民国元年前有过白话实践的人,汉字汉语观往往趋于开放,汉语造型多新姿,往往喜欢改变旧有体式而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相反,没有或极少白话实践的人,汉字汉语观往往趋于保守,汉语造型少新变,不太喜欢改变传统文体样式”。上述对内在规律的尝试性总结,正是在摸索文学与语言变革的深层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方面在勾勒语言变革的阶段性中把握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又不为目的论与进化论所化约,而注重历史罅隙里一闪而过的可能性。当严复在以汉语字词翻译西方事理时,曾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的感慨,然而一个尴尬却又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严复如此苦心孤诣格义出来的现代学理新词,在民国之后大多被日语中的汉语借词所替代。在讨论小说传统时,昆德拉认为:“一种艺术的历史不光由这一艺术已经创造出的东西组成,而且也由它原本可以创造出的东西组成;既由它所有已完成的作品组成,又由它可能而未完成的作品组成。”(米兰·昆德拉:《帷幕》)严复的炼词实践闪烁在历史偶然的脉络中,却并未汇入未来发展的已然走向。面对这笔“可能而未完成”的资产,文贵良指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方式来否定严复“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的方案,“如果把严复的策略放在晚清汉字遭遇的现场,亲抚严复现代格义内面的摩擦,以此寻求‘汉字/汉语’通达西学的方式,不仅会刷新人们对晚清汉字出路的认识,而且对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推广也不无启发”。“亲抚”这个词真是让我心头一震,一个饱含生存论色彩的词汇,由此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勘查、激活每一历史阶段语言资源中潜含的能量,这一研究态度是如此深彻、郑重其事,恰是在回应前引萨义德的呼吁——“对言词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
最后,作为一本谈论语言的著作,《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自身不乏语言的魅力,不妨以比喻的遣用为例。讨论鲁迅文言书写中出现的内部摩擦,将小说《怀旧》中出现的白话形容为“从头颅骨钻出的青草,胀裂了文言的整体性”。出语奇警,让人过目不忘,这是瑞恰兹所言获利丰厚的比喻:“比喻如贸易,两造之间距离愈远,便愈易获得丰厚利润。”又借风景来比喻“五四”作家的语言:“鲁迅如尼亚加拉大瀑布,热烈,强劲,有气势;胡适如一川平原,河水汤汤;朱自清如苏州园林,明净透彻;吴稚辉如亚马孙丛林,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一同生机勃勃。”三言两语,而各作家的语言风貌已眉目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