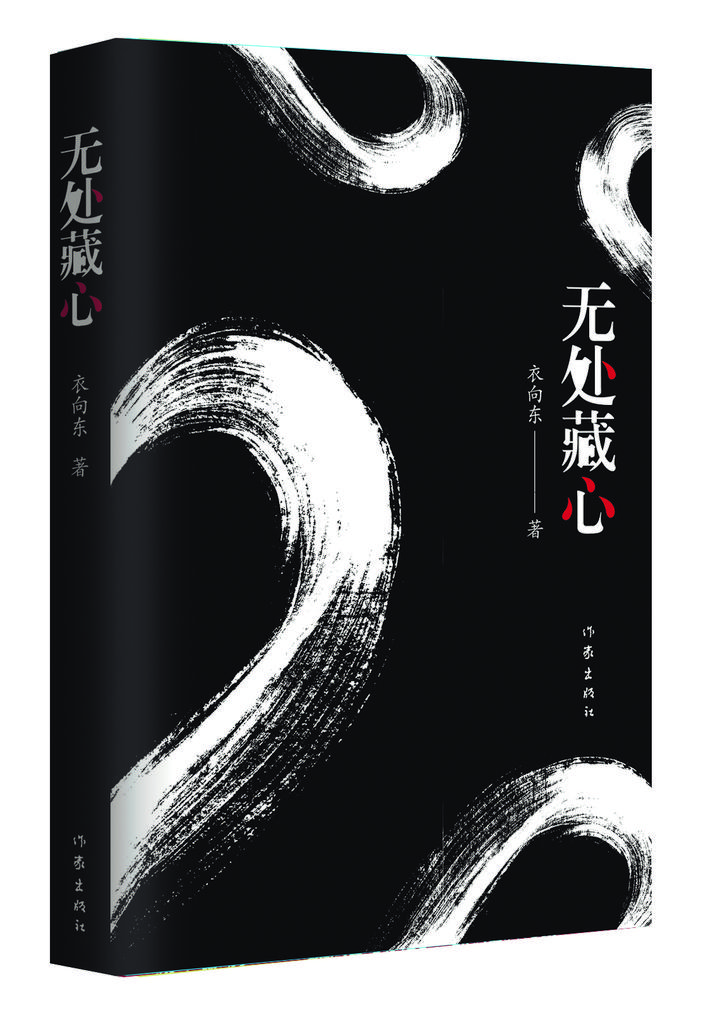柳一沙被执行死刑两年了,我答应为他写一本书,至今才迟迟动笔。这事挺折磨人的。20多年前他残忍地夺去了四条人命,毁掉了两个家庭,却请求我不要把他写成恶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
摆在案头的采访笔记,不知翻阅了多少遍,我似乎闻到了这堆文字里散发出的霉味,还有梅雨季节带来的不安与躁动。
我是2019年8月见到柳一沙的。当时为写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去菰城市公安局采访,在跟菰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晔聊天的时候,姜局长无意中提到由他挂帅破获了一起24年前的命案,案犯是个作家。我马上想到了两年前网上热炒的“著名作家”柳一沙杀人案,一问,果然,就关押在菰城看守所。
网传柳一沙是安徽的“著名作家”,有些夸大其词了,最多是在安徽小有名气。反正在他落网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是巧合,去菰城采访前两个月,我参加了一次作家采风活动,其中就有真正的安徽著名作家禾子。禾子曾担任安徽某文学刊物的主编,比较了解柳一沙,说在他印象中,柳一沙是个勤奋的人,想不到竟然是隐藏了20多年的杀人凶手,真是人心难测。这时,同行的一位上海作协老前辈爆料,柳一沙曾因女儿的医疗事故跟上海一家医院打官司,专门给他写过求助信。老前辈说:“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不过我还是跟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下。”
几位作家围绕柳一沙杀人案的话题扯了一些闲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上网查了柳一沙的资料。他跟我同岁,1985年就在安徽的一份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处女作。1995年底,他在菰城犯下惊天大案。2005年,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出版,获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这个奖项也被称为“安徽文学奖”,是安徽省最具权威的文学类奖项。
据说,柳一沙杀人潜逃后的这20多年,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如此心理重负之下,他居然能坚持文学创作,还能获奖,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跟姜局长提出要见柳一沙一面。姜局长有些为难,答应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其时距柳一沙死刑的二审判决已过去小半年了,按照时间推算,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书差不多该下来了,这时候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见面可能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
菰城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与看守所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要见柳一沙必须征得他本人同意,还要有检察机关的批准。我觉得挺难的,也就没抱什么希望。老实说,我想见他的动机很模糊,或许是作为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让我很好奇;或许因为我也是作家,对于身边发生的故事有一种本能的探知欲。
就在即将离开菰城的前一天晚上,市局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陶主任来电话,说柳一沙同意见我,并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批准。第二天上午,我在陶主任的陪同下,驱车赶往菰城看守所。
菰城的8月闷热多雨,看守所厚重的铁门在霏霏细雨中吱吱嘎嘎地打开了。所长和负责监管柳一沙的民警站在大门里侧,他们衣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
在所长的引领下,我穿过一道道关卡。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以前我也去过不少看守所,采访过不少死刑犯,但每次进出这类场所,依旧感觉有些忐忑。
按照程序,所长向我介绍了柳一沙的情况以及会见时的注意事项。他说柳一沙的情绪比较稳定,很配合监管民警的工作,这也是看守所同意让我见他的原因。
“柳一沙尤其在乎自己的作家身份,每当监舍来了新人,都会主动凑上去,转弯抹角地向对方介绍自己是作家。他甚至跟监管民警提出要求,希望看守所购买他的书,每个犯人发一本。”所长边说边摇头,“这个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
由此可见,柳一沙多么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其实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
对于执行的期限,柳一沙应该也有个估计。这些日子,每当监管民警喊他的编号,他都一个激灵,以为高法的核准书下来了。所长昨天去监室喊柳一沙的时候,见他神色紧张,赶紧解释不是“那事”,柳一沙的表情才松弛下来。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罪不可恕,曾表示只求速死,省得天天受煎熬,这种煎熬甚至比死还难受。尽管如此,求生是人之本性,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他也会紧紧抓住,甚至幻想有奇迹发生。
所长告诉他说有位作家在菰城采访,想跟他见一面。至于见不见,由他自己定。在所长的印象里,柳一沙比较抵触见记者,那些记者在报道中都把他说成是“杀人恶魔”,因此所长特意强调,这位作家不是来采访的,就是随便聊聊。
所长对我说:“柳一沙担心听错了名字,问了我好几遍,确定就是你,很痛快就答应了。看这样子,你名气很大哦?”
我只好说:“可能我这个姓少见,容易记住。”
“你这姓,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你见柳一沙,想问他些什么?最好不要问案子的情况,现在已经……”
我明白所长的意思,案子已经盖棺论定了,再问容易引起柳一沙的情绪波动。“真的就是随便聊聊,没什么具体的方向。”
见面安排在所长的办公室。所长解释,根据规定,会见时他必须在场,全程监控。“这个请你理解,我们必须照规矩来。”
这个我当然理解,同时注意到办公室上方的监控探头。所长的办公桌对着门口,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后,自己搬把椅子坐在一旁。我们的正前方摆放了一把讯问犯人的专用椅子,有点儿像饭店给孩子准备的“婴儿座”。
楼道里传来脚镣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不知是因为脚镣过于沉重,导致他行动缓慢,还是因为楼道太长,或者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总之脚镣声响了半天,柳一沙才出现在门口。
没想到他这么高的个子,接近一米九,进门时需要低下头。他站在门口打量我片刻,继而向我走来,同时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
我明白了,他要跟我握手。
“坐坐,柳一沙,快坐。”我想起所长的叮嘱,赶忙朝他招手,示意他坐在办公桌前的专用椅子上,变相拒绝了和他握手。
他的表情有点儿尴尬,刚刚伸出的双手又缩回去,手铐上的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衣老师,您跟照片一个样子。”
我知道他是没话找话,而我同样不擅长这种场合的开场白,干脆道明来意:“柳一沙,我到菰城采访,听说你在这儿,过来看看你。”
“谢谢衣老师,真没想到您能来看我,我很喜欢您的小说,《阳光漂白的河床》《吹满风的山谷》,还有《电影哦电影》,我都读过。”
他看一眼所长,接着开始背诵《阳光漂白的河床》中的段落。
“谢谢你能记住我的小说。”他竟然能整段落地背诵《阳光漂白的河床》,确实让我吃惊。
“听说您要来,我昨晚都没睡好,激动的……我喜欢的作家不多,但我是真心喜欢您的小说。”
我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窝深陷,有两个乌紫的大眼圈特别明显,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副黑框眼镜。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缘故,而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留下的印记。
我一时无话可说,满脑子寻找话题,突然想起所长说过柳一沙很在意自己的作家身份,于是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我听说你也写了不少作品……”
他一下子兴奋起来,谈自己的小说,谈他的创作经历,说他很想写影视剧本。落网之前,有一部电视剧本已经写完50集了。“我是瞎写,没经验。衣老师的电视剧我看过,特别喜欢。”
他向我请教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这个话题太大了,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而且他实在没必要知道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了。我只好打断他的话,站起身跟他道别:“所长他们都很忙,我就不打搅了。你这里有需要我帮忙的吗?我兜里现金不多,两三千块,都给所长,你想吃什么,就跟所长说。”我又转向所长,“所长您费心,多关照他一下。”
一瞬间,我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是因为伤感还是哀痛,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所长听出我情绪的变化,忙说:“放心吧,衣老师。”
柳一沙突然激动地站起来,弄得锁链哗啦啦响。“衣老师,我想请您帮我个忙。”他说完,觉得自己有些冲动了,忙又坐下,把两只手规矩地放在胸前椅子的托板上,像一个很乖的小学生。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让我帮什么忙。刚才我只是一句客套话,其实我能帮他什么呢?
“您给我写一本书吧,我一直想写本自传,我的事,可以写一本书。”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浮出难为情的样子,又说:“我希望衣老师不要把我写成恶魔,我其实不是恶魔,我像做梦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杀人犯,我、我其实很善良,有理想……”
他边说边挥动双手,忘记了自己戴着手铐。
我愣住了。说真话,这个要求太突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急切地说:“如果您答应,我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您,就现在!”
我不知道这合不合规矩,扭头看看所长,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所长微微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跟柳一沙聊了两个多小时。我询问他这2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到最后,我郑重地向他承诺:“我答应你,一定写这本书。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他坐在椅子上思索着,看上去很累很累。他说了很多话,尤其是那些痛苦的回忆,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的头微微垂着,仿佛脖子已经支撑不住。半晌,他才费劲儿地抬起头:“您要是有机会见到我儿子,告诉他,要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不容易。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定要上个好大学,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什么大学不重要,但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以后找到工作,要尽量帮助家里,帮助他妈妈……还有,不要仇恨这个社会,我是罪有应得,让他不要像我一样走极端,遇事要冷静……一定要有脑子,有自己的脑子。”
是啊,聪明人未必有自己的脑子。
我答应了他:“你放心,我一定专门去你家里,把你的话带给他。我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你妻子,有事需要我帮忙,就让她给我打电话。还有,我现在在大学教书,你儿子考大学,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谢谢衣老师。我老家南县很漂亮,您去看看就知道了。”他神色黯然,“只是,我再也不能回去了……”
“还有吗?”
他想了想:“我有个短篇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您看……”
可惜,我没记住那篇小说的名字。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监管民警站在门口,准备把柳一沙带回监室。柳一沙颇有些留恋:“衣老师,我真想跟您学写电视剧,原来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但跟你聊天后,我突然觉得,原来生活如此美好……”
我的心一揪,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是啊,生活如此美好,但他已走到尽头了。
他又想跟我握手,犹豫片刻,还是把手缩了回去,转身走向门口,脚镣拖在地板上哗啦啦作响。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身朝我走来,边走边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迎上去,握住了他的双手。
“衣老师,我总觉得应该跟您握握手。”
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
我问所长:“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所长点点头说:“采访工作照,可以的。”
我的手机不能带进监区,所长让民警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不过,按照规定,这张合影不能给我,只能留在看守所。
从看守所出来,外面依旧细雨蒙蒙。我从车窗看着宁静的街道,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有些憋闷。我决定推迟回北京的时间,留下来采访菰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晔,以及参与破案的民警们,拨开20多年来的重重迷雾,探寻1949年以来菰城第一大案的细枝末节。
半个月的采访结束后,我发现柳一沙在案情的细节上,还是遮遮掩掩没说实话,为自己开脱责任。再说了,如果他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善良,就不会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治病而残忍杀害别人的孩子。不过,无论柳一沙怎么粉饰自己,都不影响我还原案件的真相。
我离开菰城一个多月后,柳一沙被执行死刑,时间是2019年10月22日下午。
(摘自《无处藏心》,衣向东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