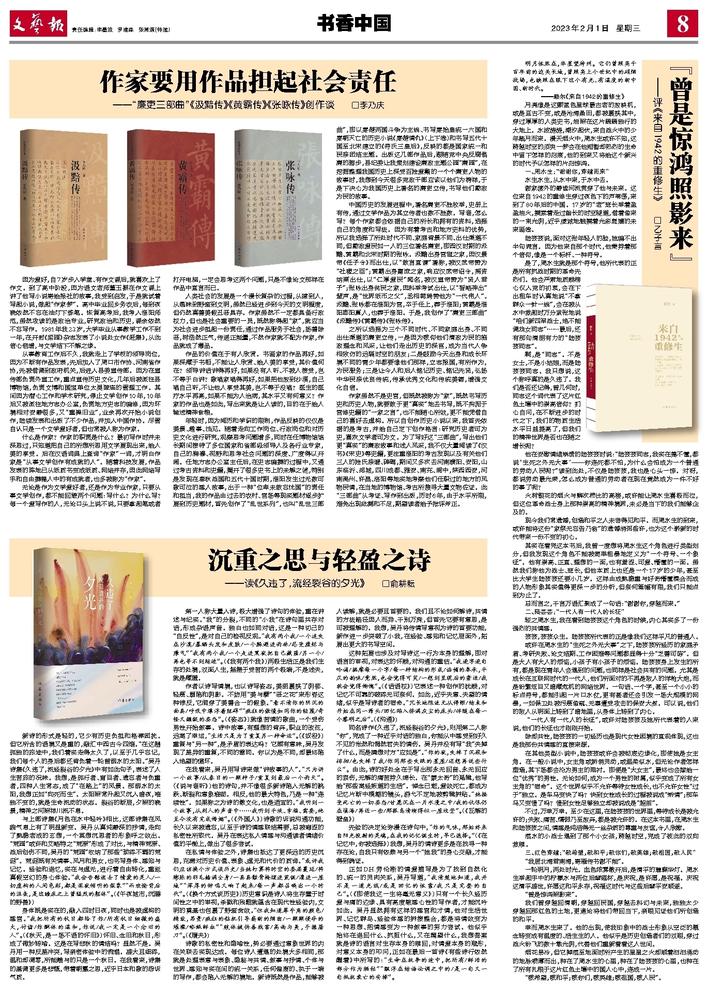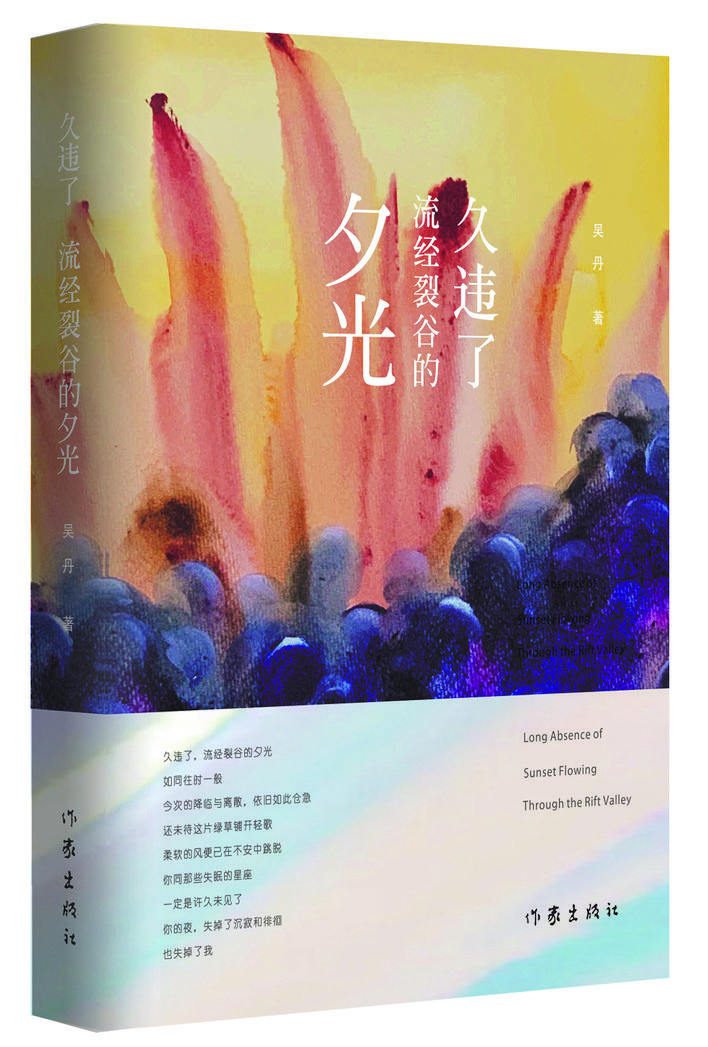新诗的形式是轻的,它少有历史负担和格律困扰。但它所含的语境又是重的,融汇中西古今四维。“在这趟孤独的旅途中,我们着实走得太久了,以至于几乎忘记,我们每个人的身后都还背负着一轮曾溺水的太阳。”吴丹诗集《久违了,流经裂谷的夕光》中有如此句子,表述了人生苦旅的况味。我想,是孤行者、盲目者、遗忘者与负重者,四种人生常态,成了“在路上”的风景。那溺水的太阳,我想正如“向死而生”。太阳照常升起又沉入暗夜,唯独不变的,就是生命流动的状态。裂谷的断层,夕照的晚景,精神之河照样川流不息。
与上部诗集《月色在水中轻吟》相比,这部诗集在风貌气息上有了明显新变。吴丹从真纯静深的抒情,走向了熟稳老成的玄想,一个冥想沉思者的形象呼之欲出。“荒园”或许和艾略特之“荒原”形成了对比,与精神荒原、战后创伤不同,吴丹的“荒园”收纳了那些“琐碎不羁的荒诞”。荒诞既有关情事、风月和男女,也书写身体、感知与记忆。经验和追忆,实在与虚无,进行着自由转化,重返真假空幻的身心体验。“我会告慰逝去了情爱的灵人/一切虚构的人间色彩,都是深夜倾听的假象”“而欢愉背后的沮丧,是这睡床之上曾猛烈的躯体”。(《午夜城市,沉睡的野兽》)
身体既是实在的,融入四时日夜,同时也是被虚构的感官。“我把所有的秋日都给了你/所有秋日细微的盛大,付诸/你酮体的温和,你说/我一定是一个念旧的人”。(《秋天,是一场不语的怀旧》)怀旧、念旧和秋日,形成了微妙转喻。这是在写悲秋的情结吗?显然不是。吴丹用一种反差冲突,写亲密体验中的惋惜。盛大且细碎,温和却凋零,所能赠与的只是一个秋日。在我看来,诗集的基调更多是悲慨,带着朝露之思,近乎日本和歌的怨诉气质。
第一人称大量入诗,极大增强了诗句的体验,重在讲述与纪实。“我”的分裂,不同的“小我”在诗句里共存对话,形成杂语声音。独白也如同对话,这是一种切己的“自反性”,是对自己的检视反观。“我有两个我/一个迷失在沙漠/暴晒头发和皮肤/一个躲避进雨林/忍受糜烂与瘴气”“我有两个我/一个走进黑夜把自己藏匿/另一个/再也寻不到踪迹”。(《我有两个我》)两极生活正是我们生存的处境,双面人生,摇摆于受苦的两个极端,不是迷失,就是藏匿。
作者以诗写情境,也以诗写姿态,美丽裹挟了阴郁、轻蔑、塌陷和阴影。不妨用“美与孽”“恶之花”来形容这种悖反,它洞穿了美善合一的假象。“看不清你的阴沉的面具/呼吸中漂浮着阻碍”“疯狂的傲慢如同你的轻蔑/奇怪又龌龊的姿态”。(《姿态》)就像苦情的歌曲,一个受伤男性开始叙事。诗中故事,有理想的背弃,职业的改弦,远离了幸运,“生活只是为了重复另一种命运”。(《奴役》)重复与“另一种”,是矛盾的表达吗?它颇有意味,吴丹发现了差异的重复,不同的雷同。你以为是不同,却最终陷入绝望的循环。
在我看来,吴丹用写诗来做“讲故事的人”。“只为讲一个故事/从春日的一颗种子/重复到最后一个雨天”。(《说与谁听》)他的诗句,并不像很多新诗陷入无解的跳跃、断裂和意象堆砌。相反,他的最大特色,乃是一种“连续性”。如果称之为诗的散文化,也是适宜的。“我听到一个故事,从别人的声音中……我听到平淡、幸福、需要,他至今没有完成婚姻”。(《外国人》)诗歌的诉说沟通功能,长久以来被遗忘,以至于诗的情感联结需要,总被晦涩的私密性所取代。吴丹在表达私人情感与沟通读者情绪价值的平衡上,做出了很多尝试。
在私情与体验之外,诗集也抵达了更深远的历史沉思,充满对历史价值、表象、虚无和代价的质询。“或许我们应该换个方式谈历史/当她打算将时空的委屈蔓延/将膨胀的羽毛插满全身/一具具骸骨掩埋进荒诞/灌进一座城”“浑厚的钟鸣又响了起来/每一声都召唤出一个时代”。(《换个方式谈历史》)历史意识是诗人将生存置于时间性之中的审视,杀戮和残酷就蕴含在现代性经验内,文明的奠基也包裹了野蛮贪欲。“但我知道犀牛角的颜色/精致,昂贵/疯狂的钻机引导崭新的烟囱/一颗颗侵夺的璀璨/舔舐鲜血”“肢体被伪善戕害/高尚与美,手握屠刀”。(《屠夫》)
诗歌的私密性和隐喻性,势必要通过意象世界的内在关联去实现达成。每位诗人遭遇的处境大多相同,那就是处理表意与表象、隐秘与共情、叙事与抒情、个体与世界、感知与实在间的统一关系,任何偏废的、执于一端的写作,都会陷入无解的境地。新诗既然是作品,能够被人读解,就是必要且首要的。我们且不论如何解诗,共情的方法路径因人而异、千别万殊,但首先它要有意思,是可被理解的。我想,吴丹将传情写意视为诗的首要功能,新作进一步突破了小我,在经验、感知和记忆层面外,拓展出更大的书写空间。
这种拓展也涉及对写诗这一行为本身的理解,即对语言的审视,对表达的怀疑,对沟通的重估。“我逐字逐句吟诵/揣摩每一个字/每一种结构的形成/谄媚的奉承,平仄的韵味/竟然,也会觉得可笑/一想到呈现后的窘迫/我就会觉得惭愧”。(《话语权》)它表述一种创作的犹疑,对记忆不可靠的破碎无可奈何。如此,近乎失意、失望的情绪,似乎是写诗者的宿命。“冗长地陈述无从停顿/结束和开始在同一源头/回忆陷入挤满灰尘的床头/伴随在每一个黎明之后”。(《沟通》)
同名诗作《久违了,流经裂谷的夕光》,则用第二人称“你”,完成了一种近乎对话的独白,你能从中感受到好久不见的怅然和惘然若失的情伤。吴丹并没有写“我”失掉了什么,而是猜想对方“应如是”。“你的夜,失掉了沉寂和徘徊/也失掉了我/你同那些失眠的星座/还想再说些什么”。由此,诗的好处全在于写出那永无回音、永无回应的哀伤,无解的痛苦持久绵长。在“蒙太奇”的尾辑,他写给“那些离经叛道的生活”。悼念已逝,爱欲死亡,都成为记忆片断中模糊的镜头,游弋不定地被剪辑拼贴。“她接受死亡的一切姿态/甘愿沉在一片水漫之中/我的仇恨仍在填海/再近一些/那孤岛清晰得似一座坟茔”。(《瓦解的壁垒》)
先验的决定论弥漫在诗句中,“你的气味,那始终来自阳光投射的灵魂,在我的记忆诞生时,早已选择。”(《在记忆中,你被选择》)我想,吴丹的情诗更多是在找寻一种存在论,自我只有依赖与另一个“她我”的身心交融,才能得到确证。
正如D.H.劳伦斯的情爱描写是为了找到自然化的、统一的灵肉关系,吴丹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是一道光线/或是回忆的依靠/我只是完整的自己”。(《即使我这一生将毫无意义》)只有一个长久经历爱与痛的边缘、具有高度敏感心性的写作者,才能沉吟如此。吴丹显然拥有这样的感官和才情,他对生活世界、记忆群岛、经验体感的拼接整合,都是将情欲变为一种思想、把情感变为一种叙事的努力尝试。他似乎始终在追回什么、抗拒什么,又在渴望什么,我想答案就是诗的语言对生存本身的赎回,对情爱本身的赋形,对意义本身的叩问,正如在最后一首诗《有些诗行依然醒着》中所写的:“生命在抗争的途中,把所有/鲜活的部分作为牺牲”“飘浮在结语论调之中的/是一句又一句抵抗衰亡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