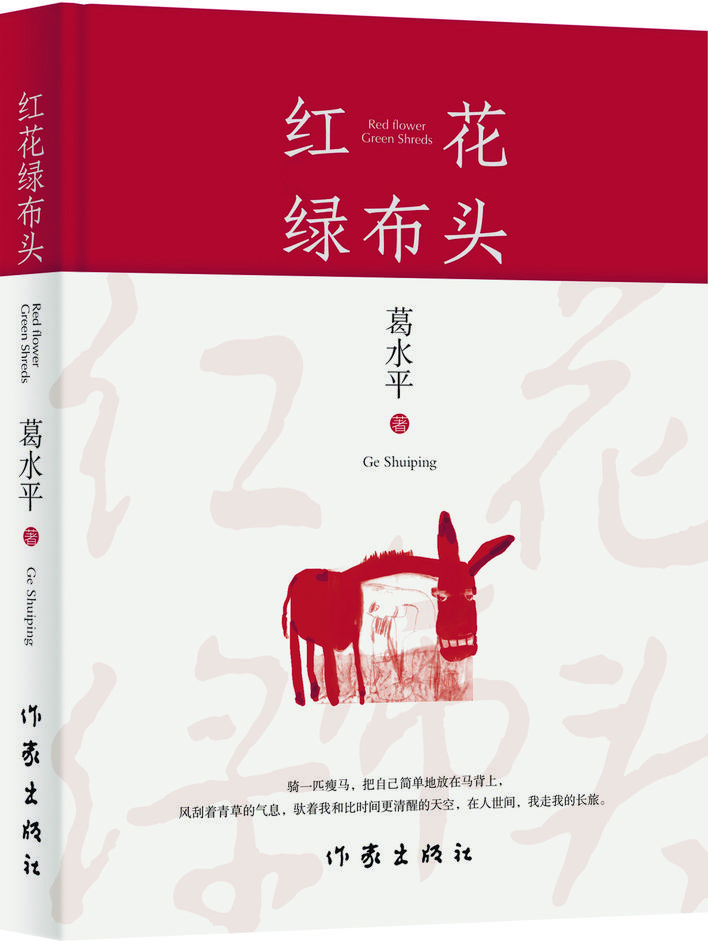文字斑驳地记录着老时光。
来自北方的桑皮麻头纸,再生环保。我还记得童年,植物的纤维,每次被平筛托起,即成一张纸。纸,有厚、有薄、有舒散、有凝聚。手工的纸,粗放里蕴含细腻,细腻里潜藏豁达,和风丽日中晾干,融入了阳光的色调,乡人叫:黄草纸。
冬天的黄草纸糊在窗户上,整个村庄都很怀旧,镰刀似的月亮挑在树梢,猜不透。窗外雪地上一长串狐狸脚窝,它的三寸金莲盛满了各种故事,与生活有关,与风霜有关,与情感有关。糊窗纸没有捅破之前,我听到一个女人喊:“雪啊,凉啊,屁股蛋子挂了霜啊。”
空空荡荡的,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结点上,需要和黄草纸一样悠远沉静的心境,才好去抚慰岁月。
从前的黄草纸糊在窗户上,透过阳光能够照见那些浮动的桑皮经络,亲切得让你觉得如体内的血液在流动。我似乎又想起了从前,从前的心爱之物,阳光裹起密集的尘土,慢慢涌动着,我的亲人们穿梭在中间,有一点儿生存的荒凉味道。风吹动他们的衣襟,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股扩散开来的牲畜味儿。那一瞬间被惶惑了,最好的命运被篡改了,是什么样的魔术手破坏了原有的秩序?
奇怪的是,时隔多年我站在乡村的山脊上,村庄里的一些人和事,或是经由各种关系将我的从前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彼此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却还记得他们在黄草纸张满窗格的天光下的身姿。
这些记忆是扎了根的,在心里,有时候做什么事情,也不知为什么,就感觉到那种从前非常熟悉地来了,绽开来,仿佛颓败的美好越来越大地洞开去。我把他们框在脑子里,并在很久之后想把他们一一画出来。可惜我没有那么天赋异禀,我想,就随性而画吧。
想象一种情景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不是出自自己的视角,而是像灵魂出窍一般,因为我真切感受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动笔之前,他们是视觉上一种强烈的刺激,带来心尖上的一阵颤抖,墨落下时,黄昏跟随寂寞爬满了我的小屋。一件事情开始之后,我总是怀揣着一个很大的抱负,但看着纸上的他们,突然明白,我还是一个写作者。天边光线穿过云层,诚实地映射到我的脸上,我还是我,我的画只是内心的一份不舍。不管怎么说,只要写作,只要画画,都可以洗涤我脑海中的一些烦恼。
想起童年,乡下的岁月弥漫着戏曲故事,炕围子上画着的“三娘教子”“苏武牧羊”“水漫金山”,寺庙墙壁上的“草船借箭”“游龙戏凤”“钟馗嫁妹”,八步床脸上更是挂着一座舞台,人人都是描了金的彩面妆,秀气的眉与眼,水蛇腰,风摆柳,或者水袖,或者髯口,骨骼间飘逸着秋水、浓艳般的气息。
伴随着日子成长,后来又学了戏剧,可惜没有当过舞台上的主角。
庆幸的是,更多的日子里是站在台子下看戏。风云变幻的历史,折射的却是社会的风情变迁,人生前无论怎样显赫辉煌,尘埃落定后都将成为过眼云烟。
“饿肚皮包容古今,生傲骨支撑天地。”
正值好年华,那时候,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台子,有台子就有戏唱,有戏就唱才子佳人。舞台上的人生命运错落纷纭,连小脚老太都坐着小椅子、拿着茶壶,在场地上激动呢。我看台子上,也看台子下,台子下就像捅了一扁担的马蜂窝,戏没有开场时,人与人相见真是要出尽了风头。台子上,一把杨柳腰,纤纤身段款款而行,出场的演员一代一代,永远倾诉不完人间的一腔幽怨。
人这一辈子真是做不了几件事,一件事都做不到头,哪里有头呀!我实在不想轻易忘记从前,它们看似不存在了,等回忆起来的时候却像拉开了的舞台幕布,我好像进入了一段历史,一段民间演绎的历史,长时间地徜徉在里面。
尘世间形形色色的诱惑真多,好在尘世里没有多少东西总是吸引我,唯有唱戏的人和看戏的人。沉入其间时,我并没有感觉到缺失了什么,这些都是缘分,值得感恩。
乡下浮游的尘土罩着山里的生灵。春天,河开的日子里,觉得春风并不都是诗情画意,亦有风势渐紧的日子,活着的和曾经活着的,横晃着影子走进我的文字。岁月滴滴答答的水声,消歇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些走老了的倦怠的脚步,推着山水蠕蠕而动。那些风口前的树,那些树下聊家常的人,说过去就过去了,人是要知道节气,是不是?
记忆如果会流泪,该是怎样的绵长!
亲人们让我懂得什么是善良、仁慈和坚忍。我庆幸我出生在贫民家里,繁华的一切成为旧日的过眼云烟之后,身后无数的山河岁月,心目所及,我的乡民,只要还想得起他们明澈的眼睛,不久就会是丰收的秋天了。
对于乡下人,收获的秋天就是一场戏剧“秋报”的开始。台上台下生动的脸,无疑让我有了想要绘画的感觉。岁月如发黄的黑白片,想画时感觉并不沉重,它是清清淡淡、丝丝缕缕地由心底生起,像一声轻轻的叹息,虽然单色调,却更像是彩色作品的底子,或者说是逝去日子的旁白。那些清新的、人间柴烟味道的生活,让我再一次回到尚不算遥远的青春时代,回到那些已经在记忆中经过无数次过滤留存下来的明月当空的日子,那些日子里有我们共同的卑微。是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我总得抓住光阴做点儿什么,以便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交代。
时间的距离使追忆成为对现实感受的提炼,只想对他们深切地关注。他们都是我曾经认识的熟人熟事,入文入画都不如入心来得疼痛。在画案前、在书桌前,我们一起坐着,天就黑了。
写作和画画都是怀恋从前,都是玩儿的生活。人生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长路,一个人停留在一件事上,事与人成了彼此的目的,互相以依恋的方式存在着,既神妙莫测,又难以抗拒,其使命就是介入你、改变你、重塑你,将不可理解的事情变成天经地义,如此就有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成长,其实也是寻找自我、不断靠近或远离自己的过程。
现在我手上握着一支羊毫,尽管我只是一个初学者,很难控制我对好的绘画的向往,很害怕自己喜欢上了别人的东西,很怕被人影响,但喜欢的同时又觉得,别人那么画是挺好,我喜欢,但是不是我心里的东西。技艺难以操控我的心力,或者说心力难以操控我的技艺,唯一的是想到我经历过的生活,就感觉到自己不那么贫乏了,甚至可以说是难过。有些时候难过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我活不回从前了,可从前还活在我的心里。
文人学画,其实是走一条捷径。即便是诚心画,许多难度大的地方也永远过不了关,简单的地方又容易流于油滑,所以画来画去,依旧是文学的声名,始终不能臻于画中妙境。我始终不敢丢掉我的写作,画为余事。
想起张守仁写汪曾祺,题目叫“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说汪曾祺的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汪曾祺之后,谁还是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我自称“文人画”,有些时候也会脸红。其实我只是觉得,还有那么多从前的牵挂,在精力的游移不定中,文学和画都是我埋设在廉价快乐下面的陷阱。我为之寻找到了一种貌合神离的辩解,随着日子往前走,有如河床里的淤泥层层加厚,我厚着脸选择了我的生活,而你们给了我一个最高的褒奖“文人画”。我只能说,落入任何陷阱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相信任何一门艺术都是有灵之物,它会报答那些懂它的人。它在夜与昼的交替之间控制了未知,并一次次浇灭体内因欲望而生的焦火。人到中年,再一次靠近自己的兴趣,我才发现写作和画画于劳力的人确实有份实在的功效,天气、物、光线,都是无法复制的,尤其是入画时的那一刻的静,风的节奏,就连性格也比平常内敛。一辈子的好时光都留在了从前,那些我认识的故人,还有他们的恩情,我怎么好一个人执意往前走呢?在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寂寞过的世界里,夜与昼之余,一种很幽深的精神勾连,让我感到犹如见到菜籽花般的喜悦。信不?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这样,相互依存。
春天了,风吹着宣纸,飞花凌空掠过,一层景色,一番诗情画意。浪漫而不无虚荣的记忆中,与生活有关,与风霜有关,与情感有关,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结点上,需要有和宣纸一样悠远沉静的内敛,我才好去抚慰岁月。
(摘自《红花绿布头》,葛水平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