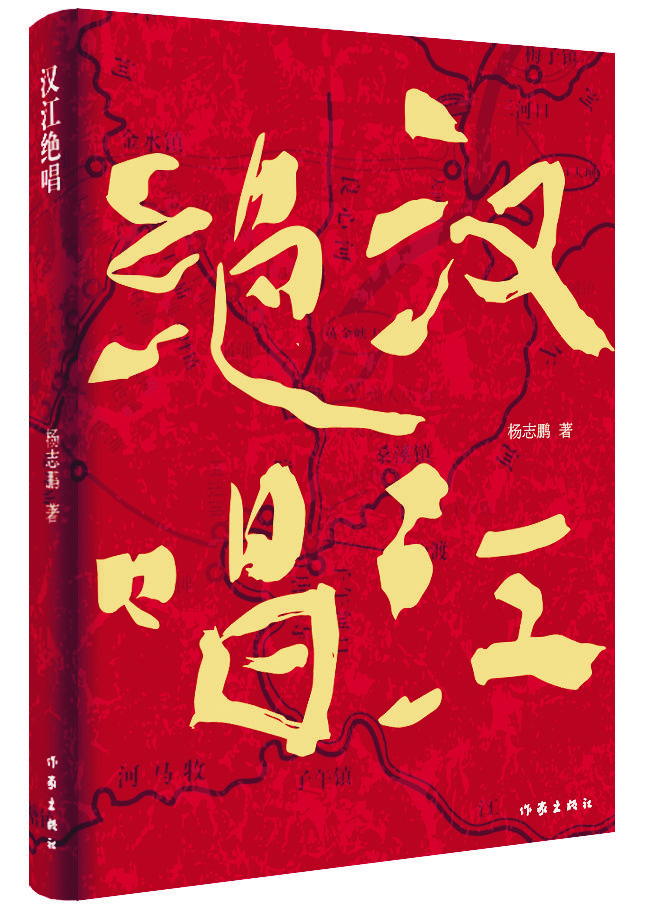汉江在流经陕西汉中洋县时,冲破秦岭巴山的夹峙,形成波涛汹涌的百里黄金峡。如果把三千里汉江称为母亲河,那么,黄金峡无疑是风华正茂、青春四射的少女。起初,汉江像一个顽皮的幼童,从宁强嶓冢山弹跳飞跃,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冲出山地,终于汇聚褒河之水,在欢声笑语中进入汉中盆地,成长为一个天真烂漫的美丽女子。她睁着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天汉大地,在短暂凝视这片土地上曾经辉煌苦难的历史,倾听无数次金戈铁马所引发的战鼓雷鸣,领略了平坦富饶又水患不断的土地后,带着野性,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冲入大山,在高山峡谷中体验青春激荡,迎接未知的爱情和生命的艰辛。因而,黄金峡无疑是三千里汉江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我有幸出生和成长于此,黄金峡与我有生命的渊源。
汉江留给我儿时的印象,更多的是苦难和贫穷,使我羡慕的则是拉船的纤夫。我和同伴们隔三岔五地会在江边遇到航船通过的情境,在早晨的朝阳中或太阳落山的夕照中,浪花中逆行的船和岸上行走的纤夫,在秦巴大山的峡谷中,构成一幅动感十足的画卷。更多的时候,我的眼光并不注视水中的船,因为船在水中的行走并不好看,上水船走得缓慢,老远看到江中泛起的浪花,如同展开的白布带,在船头和船体两边摆动,并不如汉江发大水时狂风巨浪惊心动魄,而走在悬崖峭壁上的纤夫,几十人排成一行,在高低不平的山崖上攀爬,虽然个头高低不同,身材胖瘦不一,但他们共同的姿势是弯腰弓背,如同放大了的壁虎在山崖上运动,一声又一声连绵不断的号子声,更增加了画面的生动。
我之所以迷恋纤夫拉船的画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三叔在洋县航运队做纤夫。我曾在黄金峡入口不远的沙坝上目睹了我三叔拉船的场景,他和工友们弓着腰,正在将船拉过一条险滩。我向他招招手喊了一声,他只是仰头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埋下头用力向前。三叔三个月或半年时间会回一趟家,带来城里的水果糖,偶尔还有牛奶糖。三叔说这糖来自大城市汉口或者上海,所以统统叫洋糖。可不要小看了当年的水果糖或牛奶糖,那是轰动小小山村的一件大事,人们会不断传颂,谁家在外工作的谁,回家拿回一包水果糖或牛奶糖,味道是神仙享用的人参果才有的。人们谈论如何把水果或者牛奶做成糖的过程,认为那是一项伟大的发明。那个年代没有保鲜技术,红薯只能装入地窖过冬,而苹果、杏子、橘子、枇杷等无法保鲜的水果,大多数时候只能现摘现吃,保存也不过几天时间。即使柿子做成柿饼、葡萄做成葡萄干,可以贮存一段时间,但哪有水果糖奇妙的味道!水果糖不但保持了水果的原味,还比原来的水果更甜蜜,牛奶更不用说,本来就是一种水质(山里人不说液体),如何将它熬干?又如何加入了糖,使它比鲜奶更香醇?在农人的眼中,这种城里的洋货,是山里人永远难以理解的。不理解的洋货一定是稀缺的宝贝。享用这种稀缺宝贝的,一定是在外工作的人!整天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一个全劳力一天才挣九分钱,几毛钱一斤的水果糖,对他们而言,是与自己无缘的天边的事。
三叔带来的水果糖,无疑增加了我的自豪感。那时的航运队是名副其实的国有单位,无论拉什么船,船上装的什么货,把货物送到哪儿,都与拉船者无关,纤夫每月可领到固定工资。那时纤夫一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三四十块钱,可比岸上工作单位的人拿得多,何况纤夫出船还有伙食补助。工厂里的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正式工人也就30多块。综合算下来,纤夫的工资就高出许多。所以我的自豪不仅来自洋糖,更重要的是来自我有一个当纤夫、吃国家饭的三叔。
由于对纤夫的向往,在我十几岁时,终于有了一次当纤夫的经历。我跟随父亲和生产队的大人们,一起将在汉江边黄家营真符村割的柴草,装船运回我的家乡——黄金峡小峡入口处的尖角村。几十里逆水行舟,我在岸上当了两天纤夫,实际上在大人们的照顾下,我只是觉得好玩,用不用力并不影响船的前进速度,加之秋后的汉江水流平缓,又在小峡段行走,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纤夫生活的艰苦。
长大后才知道,纤夫是世间第一艰苦的体力劳动,而汉江航运的主力则是纤夫,如果没有无数纤夫的生死之旅,根本就不存在航运的发生与发展。久远年代以来,黄金峡两岸的大山上,长年住着一些靠卖力气吃饭的壮实农人,有船经过黄金峡时,他们就会应招成为临时纤夫,将船拉出峡口,领了工钱再返回到山上,等待下一次招聘。走过黄金峡的纤夫们,不但要承受在悬崖峭壁上攀登的危险,还要时刻遭遇险滩巨浪的威胁,如有闪失,死亡很可能会接踵而来。即使航船进入平缓的河流,拉纤仍然是一件很伤身体的力气活。他们常常因为水流引起路程变化的缘故,无法准点按时吃饭,许多时候只能在航船容易停泊的地点,上岸吃几口干粮充饥,即使停船做饭,吃完饭也得立即赶路。无规律的生活方式,极大伤害了他们的胃,崎岖的道路、泥水以及过度用力,同样伤害了他们的身体。年纪稍大一些后,他们十有八九不但患有严重的胃病,而且百分之百会患腰痛和脚腿病,有些纤夫的腰很早就弯了。汉江航运衰落后,三叔改行在陆路运输做装卸工,他在父辈四个兄弟中最早去世,严重的胃病发作时,他会用一根棍子或扁担顶住胸口以缓解病痛。他最后在胃癌的折磨中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我从部队回去参加他的葬礼,他最小的女儿给我讲了三叔离世前被胃痛折磨的惨状。他的容貌在离世前的痛苦中彻底变形,当我看到他遗容的一瞬间,不由得泪如雨下。
因此,我在《汉江绝唱》中,用不少的文字描写纤夫拉纤的场景,既是向我的父辈致敬,也是替航运中无数纤夫不屈的灵魂发声: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的演进,固然有英雄豪杰的激扬文字,但更有无数普通生命的前赴后继。那些留在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人物,值得后代子孙敬仰,而更多的凡夫小卒的生命消耗,则奠定了时代前行之路的基石。记住平凡,就留住了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三千里汉江第一大峡谷——黄金峡,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尽管少年时期我曾在黄金峡拉过纤,还经常去黄金峡两岸的山上砍柴,但只是对尖角村镇江寺至还珠庙小峡段有所认识,对整个黄金峡并没有完整的印象。实际上黄金峡小峡和大峡两岸的山势并没有多少差别,一样的陡峭,一样的密林,只是因为大峡段河床更加逼仄,水流更加湍急,险滩更加密集,于是说起黄金峡,人们一般指大峡。古人咏汉江的诗中,或者人们平时说黄金峡,更多的时候也是指大峡。所谓九十余里黄金峡,是古人形成的一种印象,因为说的人多了,又写在许多诗文里,就成了一种共识。从龙亭镇尖角村(也称镇江村)镇江寺小峡入口处,至渭门关沟口大峡出口处,整个黄金峡陆路距离71.8公里,因为它绕道了新铺街,除去拐弯的距离,黄金峡全程应该超过了50公里,所以我在《汉江绝唱》中,说成百里黄金峡,取一个大概数。两年多前,《唱河渡》完稿,我产生了全面了解黄金峡的想法,这也是几十年来的一个愿望。于是,在故乡洋县作协主席、诗人李雪如的组织下,在黄建中、雍建军、郭秋梅、高原胜、周志峰、申万华、任俊峰、苏洁、张玮、司红等朋友的陪同下,分别乘车、坐船、步行,多次分段走完了黄金峡全程。
黄金峡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渭门村土生土长的楚勇,他是地道的农民,在汉江航运红火的年代,他曾是黄金峡一流的太公,驾驶航船无数次穿越黄金峡。百里黄金峡的每一个渡口、每一条险滩,他都如数家珍,能说出它的历史传说,道出无尽的故事。航运衰落后,他走进了庄稼地里,上世纪90年代又搞起山货贸易,一度做得很大,成了周边十里八乡的能人。他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凭借一个普通农民的努力,把一对儿女供到大学毕业、上了研究生,这在秦巴大山的深处创造了一段佳话。他对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散文和诗歌,为山河大地而歌唱,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文字和诗句,本来就写在山河大地上。他给我讲了许多黄金峡的故事,使我找到了长久以来寻找的山河魂魄,这是促成我决定创作长篇小说《汉江绝唱》的最初起因。
学者、作家余世存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唱河渡》后对我说:“你应该写一部汉江传。”余世存的故乡在随州,那里属于长江流域,汉水从武当山下流过。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汉水武当的太极猜想》的文章,对汉江有很深的了解与研究,他的提议和文字,是我下决心创作《汉江绝唱》的重要因素。在读完《汉江绝唱》后,他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文明及其个性的完成》,其中评价说:“包括‘陕军’在内的当代汉语小说,多半在如实记录个人和文明在现代的溃败,在哀挽人在现代的迷茫、抽换,在‘现眼’自己和笔下人物的‘变形记’。《汉江绝唱》有了重要的突破,甚至在志鹏的其他作品中,这种突破也都显而易见。”数代人百年变迁的历史如同江水中的浪花,如同江水百年的荣枯。这是一部独特的《汉江传》。
在穿越黄金峡的过程中,我多次深入重要河段走访,包括采访老船工,听他们唱当年的船工号子和山歌,感受他们对汉江的炽热情感和对已经流逝岁月的深切怀念之情。这些亲临现场的感受,强化了小说中关于地理环境细节描写的想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
作品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汉中历史和民俗,这与我的好友、文史专家、作家黄建中的帮助密不可分。他校正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使这部作品可以面对历史的逼问。作品中涉及的大量贸易细节,则请教了翻译家、金融学者于杰,他提供了民国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境内贸易交换的货币史实,使我受益匪浅。小说中关于南水北调和黄金峡引汉济渭工程引发黄金峡文化旅游开发的有关情节,则受益于陕西省政府决策委的专家胡煜,在以他为主的多位有心人的不断努力下,黄金峡的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已列入省级规划。这些情节丰富了作品的内容。
2014年9月,我去台湾参加长篇小说《世事天机》繁体版的首发式和研讨会,在台湾诗人古月的陪同下,拜访了诗坛巨擘余光中先生,他不但给我的《世事天机》写了一篇独到深刻的评论文字,而且答应了我的邀请,撰写了一篇有关秦岭、汉江气韵的雄浑、磅礴、淋漓的文字。《汉江绝唱》完稿后,我翻出余老的文章一看,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数,余老精湛的文字与我想要表达的主旨不谋而合,于是将余老这篇难得的文字作了代序。令人痛惜的是,余老已于2017年12月驾鹤西去了。在此表达我对余老深切的怀念之情!
《汉江绝唱》的创作,同样离不开清扬、刘鲡丽、段纪刚、王军、刘淑玲、张洁冰等朋友的帮助。作家、评论家兴安在听了《汉江绝唱》的构思后说:“这很可能是一部凝聚了你一生文学生涯的重要作品。”他的话使我为之一振,使我在下笔前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还要感谢雕塑家、画家贾维克,他研读了《汉江绝唱》,查阅参考了有关资料,用了近半年时间,精心创作了36幅插图,同时还要感谢书法家尤全生题写书名。作品中的山歌、船工号子、孝歌以及孟云朵所唱的校歌等文字,除采访尖角村、黄金峡多位老船工外,还引用参考了相关书籍和网络资料,对原作者和资料整理者表示敬意,正是这些众缘综合的因素,促使这部寄托了笔者无限深情的作品,如愿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关于二十四滩的名称,在历代船工的口传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叫法,定稿时我与楚勇商讨,他不但分析了二十四滩的特点,而且还专门请教了健在的老太公,最终校正了几个险滩的名称。如其中的“太阳滩”,是因为这条险滩,在上午九至十点之间,太阳的光线从崖头上直射到江心,严重影响太公辨别准确的航道,技艺再高超的太公也无法通行,因此应该叫“太阳滩”;“稍气坑滩”正对着南岸山谷“蒿溪沟”,由于“稍气”和“蒿溪”在洋县口语里很接近,后来被人们误称,所以更正为“蒿溪坑滩”;“长兴滩”很多人叫它“唐兴滩”,出于南岸建于唐代寺院唐兴寺,这个险滩虽不算太险,但确实比较长,又因为汉代这里的航运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长兴滩”更符合这条滩的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汉江绝唱》中涉及的地名,除重要情节发生地卫门,避开了实际存在的“渭门”外,其他地名基本采取实名,这样可以更为真实地描写黄金峡本来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这样做的风险是很难排除读者对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号入座的可能,所以我强调:《汉江绝唱》和《唱河渡》一样,展现的是一条文学的汉江,不是对历史资料和当下现实的整理与记录,而是对民族精神的历史追索与回放,作者所追求的艺术真实,希望与汉江汹涌澎湃的内在魂魄一致。
(摘自《汉江绝唱》,杨志鹏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