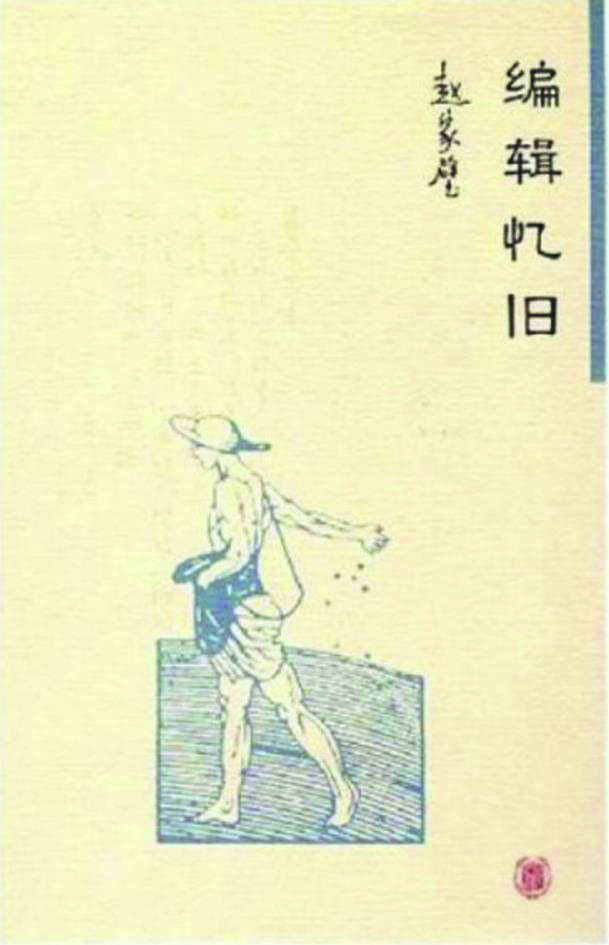《编辑忆旧》是编辑出版家赵家璧的个人回忆录,作者对其编辑生涯的回顾,向读者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历史现场。这些回忆关联着中国现代出版的点点滴滴,又关联着中国现代作家读书生活的多个侧面,其史料价值自然不必言说,书中文字更是饱含着作者深刻的个人与历史体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可以在此书找到丰富的佐证材料,一般读者可以借此领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界一些独特的风景,编辑、作家与书籍的故事既有趣味性又具可读性。此书虽然是2007年出版的,但书中所忆并没有过时,仍然值得品读。
编辑这个工作,处于文化生产流通的中间环节,常常被一般读者所遗忘,没有太多人会关注书籍是如何编辑出版的,读者感兴趣的是作家以及书的内容,这当然是偏见与盲视。编辑出版家起着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作用,作家的手稿通过编辑的编排变成铅字的印刷品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过程其实也十分曲折和艰难,充满故事性。赵家璧的回忆文章让读者看到,一个真正的编辑在此过程并非是简单的文字搬运工,而是充满创造性的建构者。有些书的产生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是编辑先有一个设想再组织作家编选或写作一套丛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曾在为《萝轩变古笺谱》作序时谈到,“学有二:有个人专攻之学,有社会通力之学。治专攻之学易,治通力之学难。专攻之学重在个人之钻研,凡好学深思者类能为之。通力之学则非通才达识关心社会文化者不能知之。知且不易,况其能结合社会力量,锲而不舍以治之乎?”私以为,恰好可以用来佐证编辑工作的难度。编辑是一个杂家,既要有个人专攻之学,又有社会通力之学,其素养要求之高,远在读者的想象之上。
《编辑忆旧》由20多篇回忆文章构成,目录的编排并不是随意的,前几篇《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从爱读书到爱编书》《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等文章,就是回忆自己与书籍如何结缘,如何从一个热爱读书的读者转变成一位编辑出版家的过程,以及第一次对成套书的编辑实践。
一个好的编辑必定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或者,起码应该是一个喜爱书籍的人。赵家璧是一位图书编辑,他对于编辑成套图书的兴趣来源于学生时代的读书兴趣。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打开了他的想象力,王尔德的《陶林格莱肖像画》读书札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也增加了他的阅读兴趣。赵家璧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受到徐志摩的影响,开始关注欧美文学作品,对国外出版的成套文学丛书更是爱不释手,后来他也因此专攻美国现代文学。五四时期,《新青年》《新潮》等定期出版的文学刊物在学校中广为传播,学生也热衷编辑文学刊物。赵家璧所在的光华大学附中出版了《晨曦》校刊,他就是四个编辑之一,后因参加《光华年刊》的编辑印刷工作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总经理伍联德结识,真正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编辑,赵家璧渴望出版对读者有益的图书,而不是被动地替他人做嫁衣,或者一味地迁就读者的趣味。我们知道,《良友画报》是该社最知名的品牌,销量4万,在当时可谓十分畅销。一开始赵家璧沿着画报重趣味的方向走,但后来受到开明、北新等进步新书业出版文艺书籍的启发,决定开始编辑文艺书,于是就有了《一角丛书》的诞生。
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编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向受读者欢迎的作者组稿,编辑和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编辑忆旧》里的大部分回忆文章都是在讲他如何同作家打交道,如何共同完成书籍的出版工作。这些书籍的出版背后,往往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耐人寻味。最初编辑《一角丛书》的赵家璧,联系到的作家面仅限于同乡、师友和同事。当时很多“新月派”代表作家都在光华教书,赵家璧最为熟悉的老师就是徐志摩,因而向他组稿,徐志摩便给了他一篇散文《秋》。不久以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罹难,赵家璧编辑出版了他三部遗作:《秋》《爱眉小札》和《志摩日记》。最让赵家璧遗憾的是,1935年协助陆小曼编辑的《志摩全集》十卷本未能出版。赵家璧在诗人50周年逝世纪念之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徐志摩和〈志摩全集〉》,文字感人至深,讲述了自己在光华读书时期对徐志摩的印象以及编辑这几部遗作的经过。徐志摩的课堂别开生面,重在启发学生的性灵,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赵家璧对他的印象是“真像是一团火”“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活泼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说话那样娓娓动听”。后来因为光华闹学潮徐志摩离沪到京教书,赵家璧对徐志摩最后几年的生活情状和心境都有详细的勾勒,对于《志摩全集》未能出版的原因也作出了解释。
赵家璧的编辑理想和创造性工作体现在他编辑的文学丛书上,例如《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和《晨光文学丛书》,这些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已经被写入文学史,有些书甚至是作者的代表作。当然最富创造性和知名度的,当属《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和出版。《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篇回忆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讲述了这套大系的成书过程,以及丛书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收获了怎样的社会反响。在翻印古书热的年头,《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展望了新文学的未来,确实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得到文坛高度的关注与推崇,这与赵家璧的宣传推广也有很大的关系,良友图书公司更是在其所办的刊物,如《人间世》,刊载关于大系的各种书评,把各报刊和知名人士的评价网罗在一起,让读者更系统直观地看到书系的价值。
《编辑忆旧》中还有多篇回忆文章与鲁迅有关。鲁迅对书籍的情感十分深厚,对于新文学事业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赵家璧刚开始担任文艺编辑时,计划编辑一套以新创作为主的《良友文学丛书》,准备请第一流作家执笔,第一个想到的组稿对象就是鲁迅,又担忧鲁迅过于严峻,会拒绝他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编辑,但是鲁迅得知其意图后爽快地把手头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交给了良友,这个书稿就是丛书中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部书。赵家璧在《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一文中回忆了鲁迅如何在重病中全力以赴地编选大系中的小说集,工作态度之认真,读之令人感动。
当时新书业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左翼作家作品的出版更是困难重重。丁玲的大部分书籍因为革命色彩过浓,被当局查禁,却依然十分热销,《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一文回忆了这部书的出版过程。《母亲》是一部未完成稿,赵家璧计划将此书列入《良友文学丛书》,丁玲的被捕,让这部计划中的书差一点流产,没想到此次事件反而触成了《母亲》的提前出版,并带来巨大的销量,共印了四版近万册。这种印数,在当时无疑是个出版奇迹。读者也许会以现在的出版标准去衡量当时的出版状况,那肯定会造成谬误。据赵家璧回忆,丁玲被捕后三天,郑伯奇就替鲁迅传话,“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对于左翼人士而言,这种出版宣传策略,也是对国民党文艺统制的一种对抗性方式。
总之,爱书的读者会在这个回忆录里获得意外的收获,了解到当年的出版状况和图书信息,编辑出版人与作家对于文化事业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令人感慨,他们与书的故事读者掩卷之余仍会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