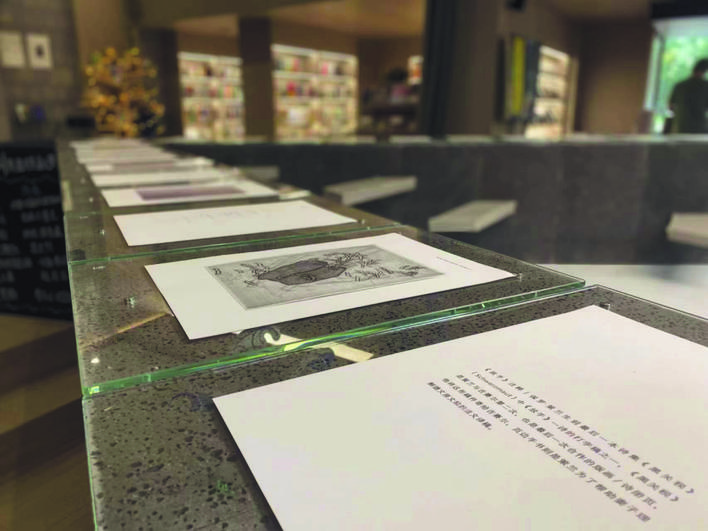已经发生的事,即为“事件”,它们无所不在,亦不能被替代和简化。
对于诗人保罗·策兰,“已经发生的事”是出生于切尔诺维茨一个说德语的犹太家庭;是二战爆发,不得不终止在法国图尔医学院的学业返回罗马尼亚,转而攻读罗曼语文学;是双亲被纳粹抓进集中营不幸罹难;是背井离乡,漂泊至终生的流亡之地——巴黎;是与一位出生于法国贵族天主教家庭的女艺术家吉赛尔·莱特朗奇登记结婚;是被诬告抄袭的“高尔事件”;是精神崩溃导致的“疯病”……它们横亘在诗人的生命里,如假包换,却不是诗歌直接的对象,因诗人从来拒绝不假思索和批判地接受现成的图景,而呈现“处心积虑”的晦涩、浓浓的寂静与谨慎的呼吸……那些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所重建的内涵和词语”引领我们,不断敞开阅读的经验,在自身记忆中植入一段“策兰密码”。
7月1日,“已经发生的事无所不在:策兰主题放映讲座暨手迹展”在北京刺鱼书店举行。活动以纪录片放映、主题讲座、手稿展等形式为抵达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创作提供了更多维的视角。
正如展览前言所说,保罗·策兰的诗走在其时代的最前面,他孤身闯入一片未有人迹踏足的语言荒地。他的德语是断裂的、多意的、暗蚀的,其灰色、无调性的书写与同时代德语抒情诗的咏叹调完全不同。因为在那场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后,曾经的一切写作变得不再可能,语言线上的风景变了,正如现实的风景……
面对语言土壤下那一片人类的灰烬,诗人在一张泛黄的纸片上写下:
我承担 J’assume
我抵抗 Je résiste
我拒绝 Je refuse
这个写于1961年6月8日的句子,字迹几乎是轻盈的,书写优美的倾斜角度、字母与字母之间疏离的间隙,与它所表露的心曲形成微妙的反差——假如在心底默念,读出它们的节奏,一定是缓慢、沉稳而坚定的。
已经发生的事无所不在
《狼豆——从切尔诺维茨到米哈依洛夫卡》,这部制作完成于2020年的纪录片,题自策兰的诗歌《狼豆》,其源起是策兰文学遗产执行人贝特朗为写《策兰图传》,邀策兰之子埃略克一道重走策兰故里切尔诺维茨。这个逐渐壮大至六人的队伍足迹从劳改农场、校舍、集中营遗址,延伸至崎岖的边境公路、林中池塘,这一场亦步亦趋的行旅并非策兰早年生活的图解,影片的轻叙事性,对不十分了解策兰生平的观众来说,甚至可能“语焉不详”。
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如实记录的意义恐怕远远大于叙事性表达。首先它记录了“重走”的这一趟旅程,其次,它素描了经历历史性灾难后,一些地缘意义上的面貌。跟随镜头,我们得以看见那些曾湮灭无辜生命的集中营遗址外野草丛生的荒芜景象……于是影片引发了一个思考,当一切可见、可感的物质不复存在,甚至灾难本身被很多人遗忘之后,我们要如何去叙述、记录、思考灾难?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所记录的“重走”,以朴素的姿态在行动和思想上接通了策兰的诗与思。
伴随由画面中心向屏幕四周不断漾开的水波,画外响起策兰诵读诗句的声音,眼前之物与思绪也逐渐涌向未曾抵达之处:
母亲,你叫它
狼豆,不:
羽扇豆。
昨天
他们中间又有人到来
杀死了你
再一次
在我的诗中。
……
母亲,我
输了。
母亲,我们
输了。
母亲,我的孩子,他
看起来像你。
(截自策兰《狼豆》,孟明译)
策兰曾说过诗是“母亲唯一的墓碑”。在历史的星空,他的诗,那些“对抗精神暗夜的自我疗愈”,也是死去的犹太人的墓碑,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战场”,一个“线太阳”(语出策兰诗名)。
“它们的经过,是为了重新在场”
无论在生活上、创作上,还是精神上,策兰与妻子吉赛尔之间的联结都密不可分,不同于以往谈及策兰多有提及的女性巴赫曼,这种联结和影响终其一生,也更为深刻和隐秘,在阅读策兰作品本身之外,为深入诗人的领地开辟了另一条路径。
通常人们只在谈论策兰时谈及吉赛尔,作为一位出色诗人的妻子,她艺术家的身份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蔽。事实上,吉赛尔的创作生涯自20世纪50年代始伴随一生,涉及水彩、综合材料拼贴、素描、铜版画等,其中,用腐蚀性溶液腐蚀或直接雕刻在金属版上作画的铜版画占绝大多数,是其造型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
展映的另一段实验短片名为《满目时间》,前半部分是吉赛尔几乎大部分代表作的集合。尽管影像作者将其做了一些颜色的处理和动态上的变形,但“阅读”这些影像的过程中,我们仍能明显地感到,作为艺术家的吉赛尔所使用的抽象语言与作为诗人的策兰在语言气质上的相通——试图赋予不可言之物、之思以形体……“文学不断滋养激发她(吉赛尔)的创作,但她也无时无刻不警惕着文字,尤其是诗歌对图像语言的侵蚀”(张何之画论《灵魂的骨骼》)。这些抽象的图像语言,用类似矿物结晶的图形作为基本的图式单元,并通过控制图形群落之间的空间关系表现某一主题,是吉赛尔在相当长的创作阶段里热衷使用的。即使时空相隔,也能直抵读者感官,它们是“非常浓密的、存在一些断裂的结晶体”。值得注意且令人唏嘘的是,以策兰的逝去为分水岭,这种语言在1970年策兰过世后就消失了,转而呈现为一种更接近传统版画的,更为放松、也更为具象的语言。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显著信息是,策兰对吉赛尔版画的命名几乎贯穿艺术家整个50-60年代的创作,策兰去世后,吉赛尔的大部分作品都标为“无题”。
“在你的版画中我认出了自己的诗,它们的经过,是为了重新在场。”1965年3月29日,策兰走进妻子的工作室,在一张包铜版的纸上写道。而吉赛尔也在1966年1月4日的通信中对这句话作出回应:“你曾对我说,你在我的画中重识你的诗歌,对我来说,没有比这句更美、意义更大的话了。”
策兰用“呼吸结晶”命名了两人出版于1965年的第一部作品集。《呼吸结晶》的最后一首诗《擦锈》这样结尾,冥冥中呼应了这种文学语言与图像语言间的往返流连:
时间裂痕的
最深处,
临近
冰的蜂巢,
等待,
呼吸结晶,
你坚定不移的
见证。
(孟明译)
将语言交还给生活
策兰研究者张何之在题为“歌的传统:人类之外,依然有歌要唱”的专题分享中,不无遗憾地谈到当下策兰研究面临的一种境遇,即今天至少存在两种面貌的策兰,一种诉诸策兰本人的声音,另一种则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对他个人或诗歌的阐释。奇怪的是,诠释策兰的声音在很多时候都淹没了策兰本人的声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而这几乎是每一个晦涩、复杂的写作者不得不遭受的共同命运。尽管近些年为了调整这种声音上的偏差,德、法等国的研究者做了相当多的考据工作,丰富了关于策兰的学术研究资料,但其与更广泛的读者接受之间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保罗·策兰生前非常反对就自己的诗歌作出任何诠释,《保罗·策兰1934-1970通信集》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路径,即通过阅读策兰的书信来理解某些他关于诗的观点。此外比较重要的工具书还包括《保罗·策兰诗全集》,这一著作几乎考据了策兰每一首诗的起源与变化,考据了诗中词语的出处,厘清了其中哪些属于策兰独有的“发明”。
反观目前策兰研究中存在的遗憾,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手稿展陈。既往阐释为阅读策兰打开了一条道路,由批评阐释回到诗歌的阅读顺序本身是否意味着一种遮蔽尚待商榷。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当我们与策兰不同类型的手稿面对面,亲身对照译文加以解读,这其中包含策兰笔记、阅读批注、信件、格言、诗稿,以及唯一一本日记,追随诗人的目光和手写,“见证他如何从日常提取语言”,如何“使摘得的字句脱离开原本的语境”化为诗。策兰说“诗是浓缩了我们所有期年记忆的聚合体”,因此,不厌其烦地将语言交给生活,由细部和深层去改造它,几乎可以确定是诗人赋予诗的独特角度,是策兰的诗学。
缓步于展陈区之间,策兰在阅读某本书时,对一些句子着重划线的情形俯拾即是,他甚至直接将诗写在某一本书边缘的空白处。当观察到日常之物中的表达性,也会立刻在笔记上生成一些句子或小稿。仿佛仍然携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无声诉说:诗不仅仅是灵感式的、突发式的,对于策兰来说,诗是一种异常辛勤的劳作。
“陈列的目的,并不是窥探策兰的生平跟八卦,也不是我们阅读策兰所必须的辅助和参照,它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关于爱的付出与劳作。”张何之与读者交流时说,“如果我们读策兰的诗,想听一听策兰自己的声音,就不妨回到他的诗,回到他写过的信、他的日记、他的摘抄。相信在虔诚的阅读中,将产生纯粹的对自我的让渡和付出,我们会静下来倾听诗人究竟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以及在文本背后,他究竟抱有怎样的观点和立场。”
一个文本的完结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完结,它等待的是更多阅读的目光,这种等待跨越时空,被赋予无限多的可能性。借助阅读这一“反垄断”的动作,我们得以一次又一次重返初次阅读策兰时遭遇的那种受创般的无言与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