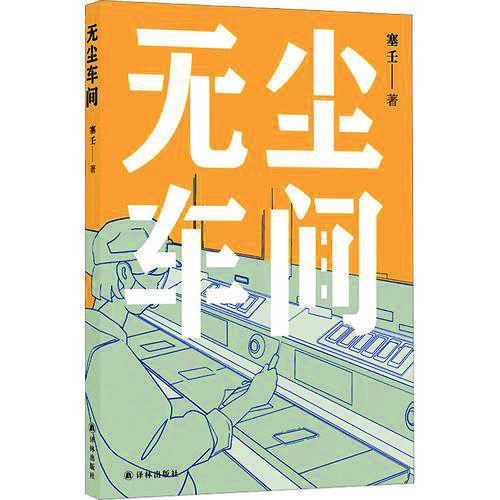2020年秋天,我联系塞壬,她很久才回复,说自己正在工厂,只有短暂的休息时间,马上就要进车间干活。这条信息发来之后,对话框陷入了沉寂。这个湖北女人,在2000年辞掉了老家的记者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广东深圳,从事媒体工作,做过企宣、广告杂志经理人等。2009年,她结束九年“深漂”,正式成为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直到今日。
2004年,塞壬开始散文创作,出版了《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镜中颜尚朱》等散文集,并多次获得文学奖。她的文章可以看见生活、看见故土,看见辗转人间的浮沉际遇。如她所言,在写作中摆脱困境,在无边无际的孤独中警醒,奔向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疑虑,一个文学之路趋近成熟的作家,一个在多年前恨不能将“我写的不是打工文学”贴脑门上的人,为何在年纪渐长后又跑去工厂?6年前,我与塞壬有过一次深度访谈,基于对她的了解,直觉告诉我事情不是作家体验生活这般简单。果不其然,《无尘车间》出版了。
2020至2021年间,塞壬走进东莞工厂,前后耗时80余天,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等与工人同吃同住,记录下打工者的一线生活。她的文字真实而锋利,将自我剖开,与外部世界坦诚相对。我在好奇的同时也保有最大程度的期待——塞壬会如何书写这些打工者?聚焦何种主题?她又如何面对并处理身处其中的自己?
流水线不需要同情
周 茉:进入工厂前,你对即将面对的生活是否有过预设,心情是怎样的?成为真正的打工人之后又有何不同?
塞 壬:我并非对工厂的打工生活一无所知。在东莞生活多年,身边随处可见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同他们都有过深度交流,而且我有很多打过工的作家朋友。虽然如此,但我还是对即将面对的工厂生活充满了期待,这个期待来自一个作家的心理,我有一个不属于传统打工作家的外部眼光。真正成为打工人之后,我所看所想都与之前的认知有巨大不同。它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现场感。只有人在那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捆绑”进工厂的制度与逻辑,那种肉体与精神的消耗是实在的,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我身上。
周 茉:在作品中,你毫无保留地呈现出自己在遇到不同人事、面对不同环境时的情感波动与心理变化,可以说将自我作为一种方法甚至观察对象。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创作方式?是前期有意识的准备,还是写作过程中无意识地情感代入?
塞 壬:《无尘车间》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它不完全呈现他者,更重要的是,它呈现我这个人。我感兴趣的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什么样的“我”会呈现出来,一个在熟悉的环境中被遮蔽的“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创作该书本意是为了解决我自身的灵魂异变问题——心灵的钝感、麻木,无法共情的危机,而非主动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作家的社会担当之类的。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崇高。但是,一旦进入那种环境,“我看”成为了写作的全部,并带给我心灵的冲击。这是一个散文作家进入非虚构最难摆脱的一个点,因为散文写的是“我”。当然,好像也无需摆脱。我思,同样也是真实。
周 茉:经过80余天深入打工现场,对照自己几十年的漂泊生涯,你对打工者的世界或者打工者群体有了什么不同的理解?
塞 壬:我不认为我的漂泊生涯比流水线工作更安逸、更高级,或者更有保障。两者只是不同的生存现场。我对流水线上的工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原来他们并不是像以前打工文学所描述的那样活在苦难中,活在无望的绝望中。他们跟社会其他群体一样,生活在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生存环境导致的种种命运中。他们掌握的命运已经是可以选择的种种命运中最好的一种。我不认为他们应该被同情,或者说要予以他们格外的爱心与关注,后者才是变相的傲慢与歧视。大家都凭劳动的价值拿报酬,平等、公正,都值得被尊重。
周 茉:这本书是否足够丰富地呈现了你想表达的主题,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塞 壬:有非常多的不足。因为时间短,我还没来得及深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一个人如果能够跟你说起情感,涉及私密的事情,那可不是两个月就能达到的。我听说,他们的情感世界已经达到了某种自洽的高度,世俗的婚姻枷锁已然无效。在那样的环境中,夫妻和子女异地生活,为了更好地活着,人们自觉地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情感生态。当你以正常的价值观予以指责他们,得到的回答竟是:我们只是相伴活着。这些只是听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验证。
用散文审视自我
周 茉:6年前采访时,你说“我时常在不同时期去审视自己”,书中也毫不掩饰你时刻对自己行为、动机的思索与质疑,这几十天的工厂生活是否让你对“打工者黄红艳”有了从未有过的发现?
塞 壬:打工者黄红艳显然要弱势得多。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打工者黄红艳,按照正常的逻辑,她不会也不敢跟组长当众翻脸。为了生存,她会顺从工厂的一切规则,可是黄红艳的内心住着塞壬,她就会蹦出来反抗和维权,因为塞壬不属于那里。我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因而有不同的命运。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般体验,既令人悲伤,也令人欣慰。
周 茉:我注意到你非常重视细节,环境摆设、人物穿着,甚至说话时脸部五官动作等等,观察入微并且会事无巨细地写出来,这是你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吗?
塞 壬:我在写人、写环境的时候,会先在脑中有一个画面,我是按这个画面照实还原出来的。颜色、声音、气味、表情……都还原出来。这需要观察与描摹的功底,需要对决定性瞬间的准确捕捉,文字的表现力用在细处,即使是碎片,最终也会形成一个面目清晰的整体面貌,通过词语内部的共谋关系自然呈现出来。
周 茉:你曾说自己的写作是“自杀式”写作,高度依赖生活经验,在文字中完全释放后自我有如“药渣”一般的存在。也有评论谈到你的文字足够真实,尖锐而不乏冒犯性,这种深度的自我审视与剖析,你在文学创作时心理状态如何?有痛感吗?
塞 壬:我是极度依赖个人经验的作家。这样的写作当然会有心力耗尽的一天,以“自杀式”予以定义并不错。至于冒犯性,可能是指,我说出了别人会极力掩藏的话与事。但这样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当你把它写出来,实际上是与自己和解、与过往和解。散文写作是回忆性的、自传性的,本身就是自我审视的文本,一旦绕开,把“我”隐藏起来,那读者就无法进入你的世界,也无法共情。
人性中蕴含着不变的东西
周 茉:对非虚构写作尤其以第三视角记录的文学作品来说,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身份差异和交往关系尤其值得思考。对身份的不同理解会形成不同心理活动,写作者如何定义自我与他者,如何进入话语系统并建构人物关系将直接产生融合、矛盾甚至冲突等结果。从此角度出发,你怎么看待非虚构写作者对二者关系的把握与处理?
塞 壬:在我看来,以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体验写出我看、我思,这才是最诚实的写作。不需要刻意转换,对身份的不同理解,本身也是一种真实,无须掩盖与规避。至于说,非虚构是第三者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不是定论也不是标准答案。作家对文本的理解,本来就包含着创造与个性化。以真实的人、真实的自我进入陌生环境,自始至终保持人的基本认知,保有人性的光亮与温暖,任何文学外部的概念都不是事先预设就能如愿的。一切的未知、不确实性都是在不变的人性中。
周 茉:你的散文属于在场的、当下的、身在其中的写作,你也曾说“我的写作,将与一切正在发生的同步”“只要作家存在情感续航能力,瓶颈与安定的生活无关”。时隔多年,在新书序言中,你写道:“这些年,我的灵魂已经干枯了,已荡不起一丝血性的风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遇到写作瓶颈了吗?
塞 壬:参与社会实践,走出安全区,一直是我解决写作焦虑的方法之一。这本《无尘车间》即是。人是惰性的,安于现状的,也是极容易躺平的,人的一生都是在跟自己的惰性对抗,那些写着写着就消失的人,就是在这个对抗中败下去的人。当然,也可以说是解脱上岸的人。只要你还跟自己较着这个真儿,你就会一次次闯进不熟悉的领域探险,收获新鲜的历练,即使不为写作,也是丰富人生、精彩人生的选择。
周 茉:未来计划有哪些创作方向?
塞 壬:关于以后的创作,打工题材我还会坚持写下去。这是一个时代题材,我目前所触的不过九牛一毛,需要深耕。我希望关于这个题材的写作能由远及近,让我最后“成为”他们。传统文化和文化传承类的散文也是我想尝试的题材之一。此外,由阅读经验开启的写作也吸引着我,在我看来,它可以唤醒个体经验,开掘全新的自我。我相信所有写作最终都会回归阅读经验,支撑点依然是每个作家自身的命运与人生际遇。当我阅读涩泽龙彦的作品,那种恣意汪洋和打通纸上与现实、梦境与想象、即刻与逝去的种种表达,让我看到了未来写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