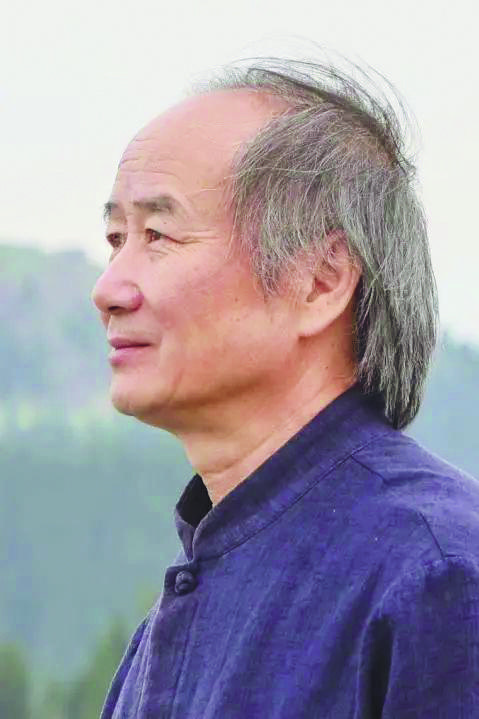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本巴》与其他几部似乎略有参差,即便置入到整个茅奖的历史中,它在题材与风格上都堪称一个独特的存在。一般对于茅奖作品的想象,多少会与广阔的现实、厚重的历史、复杂的生活等联系在一起,而《本巴》则是幻想的题材、轻盈的叙述。它的获奖,打破了那种关于茅奖的题材、主题的刻板印象,显示出茅盾文学奖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乃至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小说”这一文体的生长空间,以及文学在今日民众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
这一切都源于《本巴》的文本特质:它当然是小说,但也可以称为童话或者寓言;它充满飞翔的气质,却包裹着关于梦幻、游戏、时间的深邃内核;它将深沉的历史化为飘逸的思辨,让文学呈现出其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表述。
《本巴》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抽取元素进行当代创编,但他并非简单地还原式重述,或者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是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历史与史诗的吟唱进行了联动,从而营造出一个似真似幻的文学空间。一般还原式的重述往往只是将口头文学进行书面文学的转写,这种转写往往经过记录者的修订润饰,如在前现代时期不同年代转写者层累式完成的《荷马史诗》,或者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年代伦洛特独立搜集整理的《卡勒瓦拉》。但在世俗化的“散文时代”,现代性“祛魅”的史诗已经被“现代史诗”小说所代替。小说作者深处现代性语境,即便试图进行迷狂的书写,也依然笼罩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巴》是原初史诗的否定之否定,抛却史诗的外壳,而采用史诗的元素和思维进行文学的创新。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兴起的小说规制的突破。
《本巴》的突破性体现在,激活古老史诗的活力因子,让诗性智慧在理性时代重获生机,具有思想上的启示意义。《本巴》淡化了原史诗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在字里行间却蕴含着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作为重新锻造出的可译性文本,它既是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又是普遍共情浩瀚的世界文学,返璞归真,举重若轻。这使得《本巴》的文本兼具卡尔维诺的灵巧气质和乔伊斯的象征品格,同时又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于此敞开,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所谓“当代性”显然包含了几重内涵,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年代分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以及躬身入局意义上的情感与态度。在文学饱受新媒体冲击的当下,它在民众生活中的出路与位置究竟何在?我想,《本巴》也许提供了一种路径:前现代史诗原本是根植于民众日常的集体欢腾形式,现代以来则分化为一种艺术门类,并向着日益细致的分支拓展,由于不同媒介与载体形式的迭代更新,小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小众化。但形式的小众化,并不意味着史诗精神或者普泛的文学性的式微,它可能转化为其他形态。
如今《江格尔》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遗产如果仅仅是标本化的、博物馆化的,就失去了其活力。“文化”与“传统”如果要鸢飞鱼跃般生生不息,那么就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就显示出认识、弘扬、再造传统的当代路径:传统即创新,它并不是复古与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将其重新置于当代文化生产与生活之中。唯其如此,传统的魅力与活力才能绽放出璀璨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