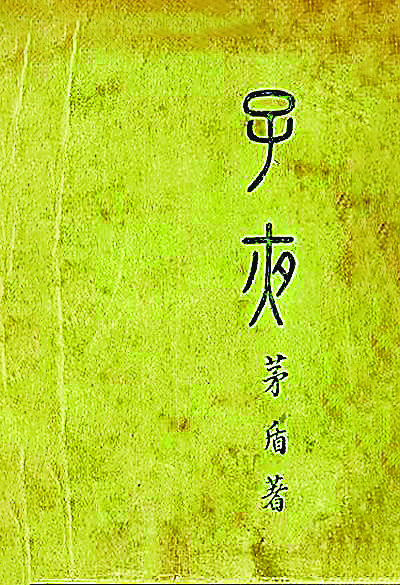□王卫平
1933年1月,茅盾的《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今已90年,《子夜》多方面的成就,值得我们不断纪念。其中,史诗性长篇白话小说的创立及其之于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意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
《子夜》的史诗性追求
史诗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过经典论述。它以诗叙史,书写民族的重大事件,充满英雄色彩,因而也叫英雄史诗。由于史诗的结构宏大,气势雄伟,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高度评价。因此,这种风格遂向音乐、舞蹈、朗诵、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等领域渗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史诗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由于具有宏阔的视野,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包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因此成为众多小说家的创作追求,甚至是最高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时期,长篇小说寥若晨星,更谈不上史诗性的作品。那是一个抒情的时代,而非叙事的时代。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批评:“伟大的‘五四’”,“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鲁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了。”“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叶绍钧的《倪焕之》问世,茅盾欣喜地评价:“《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可见,茅盾所赞美的是《倪焕之》的史诗意味。同时,茅盾也不满足于《倪焕之》对时代性、社会性的描写,认为书中对“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正面描写得还不够。同时,《倪焕之》毕竟还是单线叙事,仅仅写一个人的成长和蜕变,缺乏总体性的宏观视野。到1935年,茅盾、鲁迅、郑伯奇分别为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三集小说作序,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弱点:缺乏宏观把握生活的气势。
茅盾写《读〈倪焕之〉》,也正是他写《虹》的时候,从《虹》可以看出某些史诗性的苗头,但真正的史诗性的长篇是《子夜》。《子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诞生,它超越了“五四”文学的“主情主义”“感伤的情调”“情绪的传达”“即兴小说”等“青年文学性质”,第一次使小说具有了整体性、全景性以及宏大叙事。它具有笔力雄健、浓墨重彩、汪洋恣肆等史诗性的品格。《子夜》题材的广阔性、结构的宏大性、主题的多义性、人物的众多性、线索的繁复性,形成了气势阔大的“史诗传统”。茅盾曾说:“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史诗性的作品。他以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驾驭纷纭复杂的时代风云,完成民族国家叙事,回答时代命题。《子夜》以人物为中心,把人物及其命运放在时代的浪潮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吴荪甫具有英雄气质,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茅盾写吴荪甫,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他放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同时,《子夜》属于“浓缩型”史诗性长篇,篇幅并不很长,时间跨度比较小,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但空间幅度大,展现的是时代、社会和生活的横断面,具有概括力,多层次、多线索、全景式,充分显示了茅盾驾驭全局、分析社会的能力,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素质。
对史诗性品格的继承和发展
《子夜》作为史诗性的长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现当代史诗性作品的先河。严家炎认为:“《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相当宏大的规模描绘了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第一次以相当可观的深度刻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子夜》是‘五四’以来第一部真正具有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的长篇小说。”严家炎在研究中发现,《子夜》的出现,影响了吴组缃、沙汀、艾芜等人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
除此之外,《子夜》与中国当代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的关系到底怎样?哪些是“影响关系”?哪些是“共性关系”?正如学者杨扬所说,“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问题”。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部作品是否受到前辈作品的影响,要有确凿的证据,这证据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作家的自述提到或承认这种影响。二是两个作品中存在着可靠的影响的例证,留下了借鉴的痕迹,不能仅凭题材和风格的相似。从这两点出发,我们看到,中国当代具有史诗意味的长篇小说虽然不在少数,但真正受到《子夜》“影响”的要数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姚雪垠的《李自成》和柳青的《创业史》。姚雪垠的《李自成》得到茅盾的阅读、指导、点评和帮助,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两人频繁有书信往来,后结成《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茅盾对史诗性作品的看法以及创作《子夜》的经验不能不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产生影响。周而复在怀念茅盾的文章《永不陨落的巨星》中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读到《子夜》,像彗星一般出现在中国文坛,震动了中国文坛,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柳青的《创业史》力图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显然是和《子夜》要回答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及其性质是一脉相承的。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设有“对历史的叙述”一章,列有“‘史诗性’的追求”一节,其中说到“‘史诗性’是当代不少长篇小说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作品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三十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目标后来得到继续。”接着他列举了许多的红色经典作为例证。当然,我们要注意:洪子诚在这里所说的是对《子夜》的“继续”,不一定受到《子夜》的直接“影响”。我们看到,史诗性的作品多从纵向上展现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而《子夜》则展现生活的横断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两个月(1930年5月至7月)。当然,红色经典中也有类似作品。而浩然的《艳阳天》作为百万字的巨著,也展现生活的横断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20多天(麦收时节),这种横断面的结构与《子夜》类似。这说明浩然与茅盾有相同的追求,两者存在共性关系。
当下文学创作尤其需要史诗性
茅盾不仅是史诗性现代长篇小说的创立者,而且还是积极推动者。他在临终前决定将自己的稿费无偿捐给中国作协,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这就是后来的“茅盾文学奖”。从历届获奖作品来看,具有史诗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占相当的比重。这说明“史诗性”对于今天的创作同样重要,尤其是面对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殷切希望作家、艺术家“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全景展现生活”。《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文艺的新要求,也是人民对“全景展现生活”的新期待。《子夜》已经为我们开创了史诗性作品的良好的传统。《子夜》作为史诗性的巨著,它的宏伟的构思、宏大的结构、磅礴的气势、雄健的笔力,以及善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家庭、伦理熔为一炉,体现出“全景小说”的追求,在中国具有开创的意义,且被后代作家所承传。
联系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巨著还不够多。有一段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显出小家子气。新时代以来,长篇小说包括网络小说的创作在全景展现时代、展现生活、展现历史的巨变方面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力图呈现这个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史诗性,这些都是对《子夜》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超越。总之,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作家、艺术家的企慕和创作追求。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