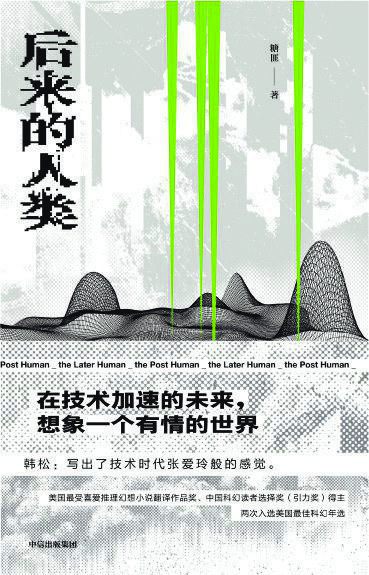@谢诗豪:《后来的人类》中的“新”空间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看云宝地》中的“房间”——一个需要密钥才能进入的云上空间,以及《快活天》里的“公寓”。克拉考尔在《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中细析了教堂和酒店大堂的区别。在教堂中,个体的“匿名”是为了汇入祈祷的共同体,“站在上帝面前的人们彼此唯有足够陌生才能互认为兄弟”,这让他们确认了存在;而酒店大堂截然不同,其中的相聚是真的“不具意义”,“人们发现自己与‘无’面对面”。他的分析或能帮助我们理解《后来的人类》中的空间。比如《快活天》中的“公寓”。公寓中的主脑出厂名叫小壹,小说中也被称作“家神”。“它拥有权威,照顾家中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在它的控制中。”实际上,如果将公寓理解为某种生活场景或方式,《快活天》里的公寓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后来的”公寓代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这个场景真正的核心是“家神”。以小说中的四名女性为例,她们的生活被割裂,和朋友只偶尔在线上或线下聚会。但是在她们头顶存在一张巨大的网络:有“神”在看且“调度”着他们的生活,维持一种宏观也貌似“客观”的平衡。公寓是“神”实施力量的空间,在这里,“个体”走向无名,“后来的”世界里,“神”以服务的样式重新出现。然而颇具意味的是,面对监控所有、无所不知的“家神”,欣敏好奇地想:家神能看到鬼魂吗?这有对技术的反思,用鬼魂这一“过去的存在”反问“后来的”世界里的“神”,用“信仰”的存在提问技术的“神”。
@战玉冰:我想进一步讨论在“公寓”空间中所发生的日常行为实践——家务劳动,《快活天》中对于家务劳动的书写特别精彩。小说中,家庭主脑的普及表面上看似乎减轻了很多日常家务劳动的负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中的结构性困境。家庭主脑的出现不仅没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女性,反而施加更多的束缚,并更清楚地暴露出日常生活中的不对等。比如想把烹饪模式改为烧烤模式这一简单的生活需求,就需要调整房间安全参数;想要调整参数,就需要获得相应的权限;而权限则只掌握在丈夫手中。又比如想在朋友家中试做一顿碳烤鸡肉,连接炭烤箱却需要征得全部住户的同意。德·塞托曾将烹饪视为抵抗社会规训、获得个体自由的重要日常生活实践方式之一,在他看来,烹饪过程中劳动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自由时刻,就是主体性解放的瞬间。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更是颇为浪漫地认为家务料理具有某种诗意,它“在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之间编织起统一古老的过去和崭新的日子的连线”,“家务使沉睡的家具苏醒”。但家庭主脑的出现却破坏了这种家务劳动中所可能包蕴的自由与诗意,一切家务劳动都有其固定的程序,必须被严格遵守,主体性在这种彻底的可计算性逻辑支配下遭受进一步压抑。
小说中的双重反抗在一开始便打下伏笔。面对失败的料理、烧焦的鸡肉与一场没有火焰的大火,欣敏感受到并记住的却是鸡肉被炙烤后所释放出的气味——“真是香”。借用朗西埃的说法,欣敏的身体、感受与动作,在其作为家务劳动主体与技术规训对象的过程中,不得不服从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秩序,而嗅觉感知则意味着一种感官政治的重新分配,这是一种对于秩序规训的逃逸和反抗、一种审美的断裂、一个主体性解放的时刻。进一步来说,这种逃逸规训与寻求解放的方式甚至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基本结构:面对“便捷”“健康”的速成餐,她想要进行一次亲手烹饪;面对时时被监控、计算的住宅与家庭,她精心策划一场“意外”……小说中的反抗从家务劳动中的一次偶然“失控”,最终发展为一场“谋杀”。
@史建文:糖匪的写作旨趣并非以令人目眩神迷的未来科技产物刺激读者的感官神经,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时代中另一部分人群,考察“后来的人类”在不同维度空间的科技伦理下所受到的多重重压。《看云宝地》中以新型科技构建的云上世界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以至于云上的消失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失踪”。短短数十年间,因为云上空间的出现,现实世界的社交伦理及婚恋伦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新的伦理道德法则随着新科技的诞生运用而渐趋稳定。《快活天》则将考察的视角聚焦于未来家庭,新型科技的投入使用反而加剧了人际关系中的固有矛盾。所谓为人类“孵化梦想”的集约化智能住宅本质上是为“双系抚育”提供便利,而家庭主脑的一切运行法则即为最大化、最优化地维持家庭的正常秩序以抚育后代、繁衍族群。欣敏所在的密友圈正代表了女性的四种生存样态,拒绝进入婚姻的阿璨最终因社会的“放逐”而走向死亡。与其将欣敏的行为定义为精心策划的谋杀行动,毋宁称之为捍卫生育权、生命权与个人主体性的殊死搏斗,是普通个体面对庞大的科技系统与其伴生的社会伦理法则的消极对抗。
@梁钺皓:我关注是主体人物与客体装置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关联。“科幻”对于糖匪仿佛一套陌生化装置,与其说她的小说关乎未来,倒不如说在试图逼近当下生活的真相。在书的后记中,她说自己更愿意在路边就地坐下,然后看向世界。这个描述让人想起小津安二郎的低机位,这是一种漠不关心地将目光投射至未来的视角,因为它必将被拥挤的人群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阻隔。所以,在这本小说集中我们看到的所有“后来的人类”几乎都能在今天的世界里找到身影,小说中出现的种种未来科技装置,也成为了这种现实隐喻的组成部分。
《快活天》中“家神”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在家庭内部全知全能一般地掌管一切装置,完成一切家务劳动,并且监视整个家庭。这样的职责让人想起女性在家庭中古老的职责。这一点在欣敏父亲的家庭变化中显得尤为突出。一个中风瘫痪的老男人,顽固地排斥一切新科技,坚持由欣敏的母亲来全权照料自己,但是当欣敏母亲突然去世之后,他却近乎基因突变般接受了躯体的赛博格改造,还有主脑的引入。这正说明了主脑是“母亲”这个女性职责在家庭中的替身。由此,最诡异的一幕在家庭生活中出现了,当欣敏试图修改参数来使用新锅时,主脑告诉她只有她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男性拥有修改权。也就是说,这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受限于那个漠不关心的男性。至此,“家神”这个称呼几乎变成了一种诅咒般的命名,在要求无所不能的同时也要求顺从臣服。尤其是作者告诉我们,主脑的根本逻辑是维护这个家庭,它会选择欺骗来保持家庭的稳定,就像是小说中母亲的灵魂劝告欣敏不要离开丈夫。先进与古老于此交汇了。
主脑将家庭主妇从“母亲”的幻觉中解放出来,欣敏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虽然矛盾重重,但并非对立,她们是共生的,如小说中一再强调的,其实没有什么小零,那只是小壹的幻影。如同欣敏和主脑最后那场充满了伤感的告别,就像在说,“我选择不同,但我来自她们。”
@曹禹杰:虽然披着科幻的外衣,但是在琳琅满目的技术语词背后,小说传递的依旧是对记忆、情感、性别等主题生生不息的观照。值得追问的是,当科技、幻想与人类耦合的时候,人类或者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糖匪提醒我们“后来的人类”可以从相互纠缠的两个维度解读,表面上,这是指向未来社会与后人类的时态语法,但它又可以指称那些“被技术抛下落后于时代的人,那些不知不觉就从视野里消失的人”。糖匪把二者扭结在一起,在科幻语境中生成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反讽视角:那些看似一往无前,奔向未来的后人类,转瞬之间就有可能成为被技术淘汰、被时代抛弃的“后”“人类”。
从后人类旋灭为“后”“人类”的成因撬动了我们对科幻文学中科技与人类关系的惯常思考,挑战了我们对于“新人”的认识。小说最后,糖匪借助鹤来提出了另一种她所期许的“新人”形象:鹤来有着种种现实的欲望、顾虑与羁绊,他无法像成音那样彻底舍弃过去,让曾经熟悉的人事都“向他背转身去”。尽管他可以带着不变的记忆、无数过去的形象,假装仍然活在现在,但是鹤来并不愿意成为这样的“新人”,因为他对“关于生命的走向,时代的噪音,进化道路上一些被抛弃的和留下来的”还有眷恋与困惑。情感、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互通有无,最终促使鹤来以失踪的方式退场,离开云上/云下这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体系,虽然糖匪并没有明确交代鹤来最终的结局,但是无论如何,他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创造了既定道路之外另一种可能性,“屋子里没有人,却有不少人生活过的细小痕迹,就像那种主人暂时出门的屋子……清丑顽拙的神秘空间。似乎在前一秒刚刚成新。开天辟地般的新。”失踪的鹤来最终成为了一个似新实旧,似旧实新的“新人”。
赵园曾这样定义她心目中的“新人”:“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准确意义上的‘新人’,应当指人群中的那一部分,即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对于‘使命’更为自觉,依历史要求而行动的先觉者和实践的改革者。”无论是在科幻文学的脉络中,还是在19世纪中叶以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争鸣的“新人”谱系中,抑或是糖匪自身的创作流变中,《看云宝地》所提出的对于“新人”的思考都有难能可贵的意义。何为“依历史要求而行动”?何为对“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的自觉?何为真正的“新”?借助科幻书写,糖匪将这些在技术浪潮中逐渐被淡忘,但又值得我们时时反顾的命题重新问题化。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可以看到,糖匪在过往作品中反复触及的命题,如代际关系、技术伦理在《后来的人类》中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人性、生活与现实的感受、探索与追问,这是真正的贴地飞翔。糖匪未来的创作值得期待,这并不是在翘首等待一个典型“新人”的出场,而是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与无远弗届的未来中,守望永远自觉、先觉且永不定型的人性与人类。